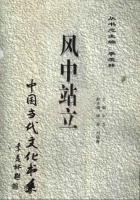我在我妈教书的学校门口站着,看到坡下走来一个人,瘦高的个子,推着一辆加重飞鸽牌自行车,暗红的天光下,进入我眼帘的是那双趿拉板的人字拖鞋。八十年代的北方没有见过那样的拖鞋,感觉很洋气。他支下自行车说:“你是张老师的闺女?”我点点头。他说:“讨口水喝。”我始终没动,细小的骚动也相当微小。他一直看着我,听见妈妈和他讲话,知道是岸山坪考上中山大学的那个人。一碗水喝下,我们算是认识了。他离开时留下地址,说:“给我写信。”莫名其妙突如其来的心跳,似乎有什么与我的内心相连,我点了点头把那张纸条收下。
那一年,我虚岁18。
我上晋东南戏校,是暑假,我的心因他的到来随着升腾起灼热无边的思念,我恋爱了。心事莫名其妙的多起来,比如听别人讲到岸山坪,我就想多听两句。对季节有了敏感,雨天或者黄昏,心里一直想那个人,想那双趿拉板拖鞋,心里满是他离开的足迹。暑假返校后,我突然很想让别人知道我有对象了,是名牌大学生。我说不清楚为什么当时会有那样的心情,后来我明白了。其实是,我一直没有演过主演,一直被认为不是唱主演的料,在专业过硬的同学面前,我只能是跑龙套的,我有这样一个大学生对象,显然我就有了几分高出他们的出息。我毕竟是个女人。
我一定要对得起这个上中山大学的对象。我开始读书,背唐诗,写日记,写诗歌,写信。最长的时候他给我写过十九页信。那封信让我泪流满面了很长时间。
结婚时,我骑着马,从山神凹走向山头,再走向山头,我进了岸山坪他的家。我的婆婆和公公都是平实的农民。记得我怀孕,公公到市里来看我,买了香蕉放到我面前说:“不知道咋吃,你有身子,嘴馋,吃了好。”我告诉他怎么吃香蕉,他看着不动,不舍得吃,一定叫我吃。这是一个情节。还有一个,当时我们回岸山坪住了几天,要离开了,公公看到班车从远处的山洼里要往岸山坪的山头上过,他跑上岭头到大路上拦下车叫车等我们上来。公公怕我赶着坐车吃不消快跑,先跑着往山头上等车,叫我们消停走。等我和他儿慢慢走上山顶的路上时,我看到他给班车司机发纸烟,一脸讨好人家的笑容。那样的情景,我一辈子不会忘掉。
婚姻对家庭从来都是拭目以待的。我们会如何?结局又是这样?
结婚四年,明亮的心很快就暗淡下来了。其实,一直到离婚,我们彼此从来没有把心伤透,因为太年轻,结婚、离婚,我们都牵着手。记得当时从民政局出来,我们坐了三轮车一路说笑,碰见了他单位的人,人家问:“小两口去哪了?”我们异口同声说:“离婚去了。”人家笑我们和他开玩笑。那天中午我们一起在饭店吃了饭,他送我到公共汽车站,我坐上车,车还没有发动,我们坐在一起说话。车要开了,司机撵他下车,他下了车,我们又隔着玻璃挤眉弄眼,车要开了,隔着玻璃我们互相挥手,突然的手搁在玻璃上不动了,我看到他眼睛中的泪流下来,我也流下来。车徐徐的开动了,我从他的口型知道他在喊:“下来,不走了。”车还是把我带走了。
没有做过爱情去后的失衡之举,我们是一方土地上长大的,我不否定曾经的爱情,也不想在人性失落中变得狭隘。我也不是超出一般人的人,我只是怀恋有一段时间我们爱得很深,爱退隐了,回忆还在。
我祝福他,他和他的家人都是我距离中的远方亲人,在未来,我笃信他幸福,笃信他快乐。只是因为,他是我婚姻的过去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