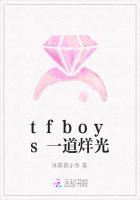我的家族本不姓“葛”,从祖坟的墓碑上刻的姓氏看是姓“盖”。姓氏的过程得怨南下干部葛起顺。葛起顺是我爸葛成土的爸,我叫“爷爷”。当时大字不识一斗的爷爷被扩军扩走时,有军人问,你们家姓甚?爷爷很光荣地喊:“盖”(姓氏里盖姓念葛)。那军人说,知道,姓“葛”。用毛笔工整写下要爷爷看,爷爷不敢看,只说:“是。”战争过后,部队比较守规矩,往来信件一定要统一姓名,爷爷不能改档案就一定要山神凹的“盖”姓改“葛”。一个“知道”断了“盖”姓家族的香火,从此“葛”姓在山西十里公社山神凹广延。
我对爷爷的认识一直是一张相片。我17岁那年,爷爷回乡了。先是在长治市里住了一段时间。爸爸当时在长治市中医院烧锅炉,我上晋东南戏剧学校。记得是夏天,我在戏校的排练场化了妆排练《断桥》一折,我演白蛇。等待锣鼓家伙响的空档,我看到排练场的窗户上有两个脑袋,一个是我爸,一个是一张老汉的脸。排练结束后,我走到院子里,我爸说:“你爷爷。”早知道爷爷要回来,真回来了。我看着爷爷还有点不大好意思。我爷爷夸我说:“我孙女长得比世上的花好看。”我一直认为爷爷是在说瞎话,夸人太出格了叫人别扭。爷爷在市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正好我放暑假,我爸决定一起回乡下。回家的头一天晚上,我爸的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汽油味儿。半夜醒来,只见地上的他们把塑料壶里的汽油装在葡萄糖输液瓶子里,大约地上放了有十几个瓶子。
莫名其妙,我又缩回脑袋睡了。
第二天,要往车站走,我看见爷爷和我爸脱了上衣,我爸用纱布把装了汽油的葡萄糖瓶缠在爷爷的腰上,自己也缠了一圈,像一排子弹似地。爷爷穿不上自己的衣裳,捡了一件我爸秋天的半大风衣穿上,看上去有一点滑稽。去长途站的途中,我问爷爷,才知道我爸是想带汽油回乡下卖大价钱,乡下的汽油比较紧缺。班车上不让携带易燃易爆品,只能偷缠在腰上。
黄昏,眼乱的时候回到山神凹,卸了汽油,已经有人来买了。我爸手里捏着票票合不拢嘴,大约赚了有两倍还多。送走来窑洞里看爷爷的人们,爷爷脱衣睡时发现躺不下,身上奇痒难忍,腰间出了许多水泡,密密麻麻的水泡看上去叫人头皮发麻。油灯下爷爷焦急地问我爸有没有?我爸抬头纹都没皱说:“光光的。”没有比我妈了解我爸了,我妈悄声儿和我说:“要光光的才叫日了怪。”
我琢磨这些话包含的意义——我大约知道;但我并没有准确找到含义,有多种猜想,每一种都让我不能准确找出其中况味,就像身体内部的血液,它的循环和输送、感应和嬗变,有着初生婴儿一样的灵敏。我爸和我爷爷让我知道了什么是血缘。我妈则告诉了我,有些真话不能讲,不讲真话叫:善意的谎言。
如今爸爸和爷爷都去了另一个地方。他们会在当空明月下远远地望着尘世中生活的我,望着尘土中劳碌的妈妈,那些来自天上的声音,那些来自天上的温暖,我爱他们,但是,我看不见他们的脸,只能在梦里,挡不住的念,又怎堪消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