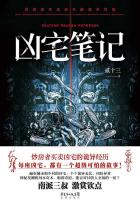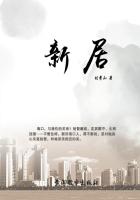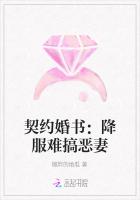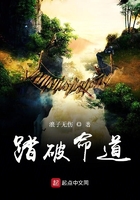等待的日子又延续了不多的几日。其实用等待这个词也是不对的,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其实谁都不知道自己究竟在等待什么。
天一日日的亮得晚了,有一天是晴天,看得见慢慢探出头来的太阳;有一天到了中午前后雾还没有散;还有一天阴云密布,断断续续地下了两场暴雨。而每天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头发一天比一天少的季先生就站在桂花树下,等待手里提着小包裹的柳春风下楼。
但这样的等待其实等不等都是一样的。几回书很快就会说完,即便还没说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是已经有人听着听着就在茶馆店里睡着了吗,人生烦恼的事情太多了;而一个女人偶尔向你抛几个眼风,这更是又有什么呢?当然了,当然,或许在荒凉广阔的人生的荒原上,这还是有点意义的。
季先生等来了柳春风,两个人就一起去河对岸的茶馆。大部分时间他们从木桥上过去,但有一次,小河涨水了,他们就站在岸边等船。就在不远的河面上飘着一只小船,一个船夫靠在船舷上睡着了。他一定是等累了,等了很长的时间,希望有个摆渡客远远地走过来,上了他的船。但人来的时候他却睡着了,什么都没有看到,你说这样的等待又算是什么呢?
倒是两个女人间的亲谑、以及天性中的防备、忌妒、小心眼……倒是这些有根有据或者莫名其妙的东西在慢慢延伸,渐渐微妙。还有那个小丫头柳小妹,因为等待的东西万分清晰,所以每天都显得兴高采烈。她甚至在河对岸的茶馆店里学到了一套简单有效的魔术表演--怎样让纸花在放进帽子后变成一朵怒放的玫瑰。孩子总是天底下运气最好的人,至少在她真正懂事以前是这样,甚至不用乞求,不用做梦,只要等待--闭着眼睛、抿上嘴巴、竖起耳朵--天底下的美事就乖乖地来了,就连白纸都要变成红花。
有那么几天,晚饭过后,季先生、童有源、童莉莉、柳春风、还有坐立不安、老是跑来跑去的柳小妹就坐在楼下的客堂里。每个人看上去都有点心神不宁的样子。窗外传来风声,还有风刮过树叶以及树梢的声响,童莉莉面无表情地在看一封信,看过前面一页翻到后面一页,信纸也会发出沙沙的响声。
童有源问了问信的来源,童莉莉仍然面无表情地回答了他。当然了,有些事情问与不问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问的人没有往下延续,而回答的人也不再加以补充。倒是老季、季古季先生流露出一种难以掩饰的焦虑。他先是动作夸张地开了窗,并且探出大半个身子去,然后又楼上楼下地跑了好几个来回,直到本来就光亮的额头沁出一排细密有光的汗珠。
“这可怎么是好呵--”季先生摊手摊脚地往椅子上一坐。
“什么好不好?”这种奇怪的情形,大家当然忍不住要问上一问。
原来这季先生在河对岸茶馆店里说书的时候,遇到了一位老听客。有时季先生他们去早了,就先泡上一杯茶,和他聊聊天。有时季先生书说完了茶还没淡,就又边喝茶边和他聊聊天。这样聊着聊着,不知怎么就聊到了季先生的头发。有一天那听客突然哎哟哟地叫起来了。说哎哟哟,季先生你这年纪和你头发的数量可不成比例呵。季先生脸腾的就红了。那听客又说,其实我以前的头发和你一模一样,还没你多呢。季先生惊讶万分,说你现在的头发多好呵,又浓又密,春天田野里的新草也只不过这样。听客自然很得意,在太阳光底下,他又仔细观察了一下季先生头发的现状,说,喏,有个偏方,专门就是治疗你这样的脱发的。季先生一拍大腿,说好呵,你也是用了这个偏方吗?听客点点头。季先生很是有点急不可耐的样子,说,那你还不早点告诉我--
那听客就掰着手指头说了起来。说,“喏,是这样的,槐树,你知道槐树吧,就是那种大家都知道的槐树,十月份的时候,你去采一些槐树子,二十一颗,记住了吗,一颗也不能多,一颗也不能少,不多不少就是二十一颗,连着皮把它吃下去……”
“槐树子,二十一颗,连皮吃下,就这么简单?”
“当然不是。当然不会那么简单。”
“那还有什么讲究呢?”
“得在月圆的晚上、身上又恰好出了汗以后,这个时候把槐树子吃下去,效果最好了。”
“那也不难呵。十月份,二十一颗槐树子,月圆之夜……”
且慢,且慢--
接下来才是让季先生真正烦心的事情呢。因为那听客把最重要、最棘手、最为性命攸关的交代放在了最后面。是呵,就按着那偏方去做吧,很多人都做成功了。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长出了又浓又密的头发,春天野草般旺盛蓬勃的头发,即便是山里荒凉的野百合,但野百合也会有春天呵--但是,但是--
“也有很少一部分人会失败的。”那听客的声音变得凝重起来。
“失败?那也没什么,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早已经习惯了。”
“那可要比现在还不如呵。有很少一部分人用了这个方子后,头发会全部掉光的,直到变成一个真正的秃子。”
“哦?有这样的事情?”
“是的,事情就是这样的。”
“那什么样的人会长出好头发,什么样的人会变成秃子呢?”
“不知道。没人知道。只有天知道。”
这是金秋十月的一个月圆的晚上。只要推开院门,走上那条通往河边木桥的曲折小路,走到大约一半路程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路边站着一棵高大的槐树。旁边还有一棵略微矮小些,但也是槐树。就着月光远远地望过去,槐树的树冠就如同一团墨绿色的浓云。你盯着那一团浓烈不散的云团,看它,死死地看它,目不转睛地看它,看着看着免不了就会恍惚起来。有时你会觉得,它就只是一大团树叶和树枝嘛,从树根那里伸展开来,在碧蓝的夜空里成为凝固的、静止不动的树的形象。风吹过来的时候,有沙沙的声响,还有不易察觉的细微的清香。但还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它突然动了起来。它不再是一棵树了,也不再是一棵树的所谓组成部分了。它更像暴风雨到来前天空中不断聚集的雨云。它们在天空中神秘而诡异地集结,随时都会移动,随时都会飘走,随时都会消失……但也随时都会被天空中飞流而下的闪电击中,周围的一切被通通照亮,坦荡,通透,无耻,曲折幽深的南方景致隐遁不见了。
但现在,它看起来还只是一大团晦暗的阴影。因为白昼和夜晚交替而出现的幻觉。如果月色明净如水,湖面风平浪静,那么墨绿的色泽则还是清晰可辨的。当然了,其实墨绿是一种相当晦暗的色彩。浓云同样带来晦暗。所以不管怎样,这月色下的槐树看起来还是晦暗的,让人感到有不可知的事物藏匿其中。
是呵,又有谁能够声音宏亮、不加思索地表达--表达对于未见之物的完全信任?
季先生的头发尚且还是小事,季先生看了农历看月亮,看了月亮看槐树……季先生楼上楼下地不断奔跑,直到把自己弄出一身臭汗,但是季先生还是不敢把已经在手上揉得潮腻腻的二十一颗槐子吞下肚子--坦然地接受命运,就连这也是很难很难的呀,谁知道命运到底会给你什么呢?一头乌黑浓密的新发,还是寸草不生的不毛之地?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但月亮很快就会落下去的,月落星沉。当然月亮也很快就会升起来,月明星稀。然而明天的月亮和今天的月亮是不同的,明天的月亮与那二十一颗槐树子已经没有因果关系。所以季先生才会如此焦灼地抬头望望月亮,低头看看槐子。
季先生在看完月亮和槐子以后,又曾经求助般地望着大家。只可惜没人应他。这事情就自己拿主意吧。他们说。除了命运的信息有时确实让人担惊受怕,也因为每个人也都有着心神不宁的原因或者隐情。
童莉莉手里的信是吴光荣写来的。
莉莉:
你究竟哪天回来?
我单位里的事情很忙。你四弟的眼疾好像又犯了。你母亲前几天来过一次,也不说话,坐了会儿就走了。
你不在,家里的一切都乱糟糟的……
莉莉,你究竟哪天回来呢?
吴光荣的信总是这样,冷静,简短,克制。永远不会说得比别人多、比心里的多,比该说的多,就像他手上永远比别人少的那两根手指--然而吴光荣无疑是坚定的,斩钉截铁的,像燃烧的火种一样热烈的,所以童莉莉明显地觉得就在信纸的背面,就在那雪白的纸片上,沉默的、一言不发的吴光荣其实还写着另外一段文字:
你疯了。你真是疯了。你们这一家全是疯子。你到底在想什么?你到底要干什么呢?!
你快回来!听到了吗,你赶快给我回来!!我是那么爱你……你回来吧,你随时都可以回来的。我等你。
当然了,这样炽烈而又直接的话其实在信纸上并没有出现。拿在童莉莉手里的这封信简简单单、明明白白,信纸的正面写着不多不少的几句话,而信纸的背面则是空白的……
现在,我们这位秀气的姑娘,我们的童莉莉,正在把信上的另外一些事情告诉父亲童有源。这些事情自然是可说可不说的,因为即便不说也是可以从报纸广播里知道的。而每个人隐秘广阔的生活道路就不是这样了。好几年以前,在我们的女主人公还没有认识潘菊民的时候,有一天下午报社开小组会,因为有几个新来的职员,大家就开始一个个的自己介绍自己--
我叫李小翠,二十二年前出生在浙江奉化的一个小山村里,父亲替地主做长工,母亲在家里纺线做饭,哥哥帮爸爸种田,姐姐比我大一岁,和我一起玩,所以叫我小翠;我五岁就开始干活了,什么都会,八岁的时候,家里子女多,地主剥削重,先是我姐姐被人带去做了童养媳,接下来就轮到了我,我在做童养媳的那家人家里也是什么都做,但做了也没用,婆婆照样打我;十四岁的时候我们来了苏州,婆婆让我去里弄的袜厂摇袜,但摇了袜深夜回到家里,还是什么都要做;十七岁的时候,我的丈夫病重快要死了,婆婆逼着我和他成婚,一星期后丈夫真死了,测字先生却说是我的八字太硬,把他克死了,说我必须一辈子守寡才能为他在阴间赎罪;后来终于天亮了呵,苏州解放了,我加入了家庭妇联,加入了学习班,新婚姻法颁布后我还离婚得到了自由,现在又来报社看管仓库,我高兴得几个晚上都从睡梦里哭醒了呀!
我叫刘毛毛,我从小就住在沧浪亭后面的小巷子里,我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全都是工人阶级,全都是老实人,所以我也是工人阶级,也是老实人;上学的时候我就是个好学生,上课我用心听讲,不做小动作,下课我也不和人打架,不给别人起外号,虽然我体育成绩不太好,但那是因为谁也不肯将球传给我,怕我个子矮守不住;我虽然个子矮,但是在没人的时候我可以唱很好听的歌,我站在树林里唱,树林里的鸟就跟我一起唱,我站在沧浪亭外面的河岸上唱,沧浪亭里面的鸟也跟我一起唱;这次能够加入报社的合唱团,我一定要好好地唱,和大家一起唱,好好地歌唱党、歌唱人民、歌唱我们的新中国。
我叫潘子林,是这个报社的副社长,报社的同志大多都认识我了,有些新来的同志可能对我还不是很熟悉,这没关系,因为熟悉起来也是很快的;现在报社的所有同志都说我忙,所以不能对我多要求;同志们对我原谅,在同志们说来当然是好意,我非常感谢,有的同志恐怕还会原谅我岁数大了一些,因而对我不作苛求;但是,原谅对我没有好处,况且岁数一大很容易倚老卖老,所以我在这里要先向全报社同志表示一下决心,我一定坚决地做一个真正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
……
大家发言到中间的时候,童莉莉就悄悄溜出去了。后来,当童莉莉认识了潘小倩、继而又认识了潘菊民以后,有一天晚上,潘菊民约她出来散步。街上人倒是不多,不时有断断续续的爆竹的声响,还有隐隐约约的歌声……但那天晚上夜莺倒是悄无声息了,不再歌唱。童莉莉竖起耳朵听了很久,有一个静谧的瞬间,她甚至听到了一只漂亮的小夜莺发出的鼾声。大多数夜莺都睡觉去了。大多数睡着了,睡不着的也埋着头开始想心事。童莉莉发现那天晚上潘菊民也在想心事。
潘菊民说其实今天他才刚刚回家,回去了一会儿就又出来了,出来找她;潘菊民说其实今天特别累,刚从父亲那家“潘记中庸银行”下班回来,原本想听听昆曲唱片、在院子里紫藤树下看看月亮就睡觉去了;潘菊民说他回家以后稍稍吃了些点心,他是坐在餐桌旁吃的,所以就留意到桌上放着的一张报纸;潘菊民说那张报纸给翻看得有了好多折痕,但又被小心压平了规规整整地放在了桌上,这说明已经有好几个人看过了这张报纸,这也同时说明--看过的人希望没看过的也仔细地看上那么一看;潘菊民说他们家一直就是这样的,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不完全是好事的、好好坏坏、或者干脆就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他们家的人就会用这种比较曲折委婉的方式来告诉大家,特别是他的父亲和母亲;潘菊民说他母亲是个古典的人,他父亲也是个古典的人,他父亲爱着他母亲,他母亲更爱他父亲,就像一种最美好最古老的传统;潘菊民说他们走路的时候也是轻轻的,慢慢的,怕吓着了自己,更怕吓着了别人……
潘菊民说他看完那张报纸后就出门了,想找她,找她童莉莉说说话,哪怕只是简单地走一走,哪怕只是一句话都不说。潘菊民说,报纸上说的那些他都懂,都明白,他绝不是漠不关心、无动于衷的,绝不是这样。有些消息有些事情他看着看着也会热血澎湃,甚至还差点流下泪来。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完全不在这儿……
“你不用说了,”童莉莉打断了他的话,“我知道,你只是感到孤独。”
是的。我只是感到孤独。难以名状的一种孤独。
两个人在街上走着,同样的月光照在别人身上,也照在他们身上,同样的柳荫遮在别人头上,也遮在他们头上……但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人却就是让人觉得态度暧昧,形迹可疑。他们走着走着就走得近了些,更近了些,几乎靠在一起了,其实也是为了反抗以及淡化那种暧昧、可疑与孤独--他们聊了会儿天,有些是可以聊的,现在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聊的人,于是心曲尽吐;还有一些不是那么可以聊,但想了想,因为孤独终于还是说出来了,说出来心里于是就会好受很多,于是就不管是不是非常合适非常得体;再有一些,总会有那样一些事情的,埋也要埋在心里,烂也要烂在心里,那就把它埋起来了,那就干脆让它烂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