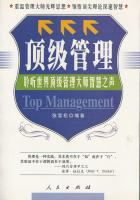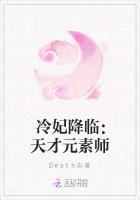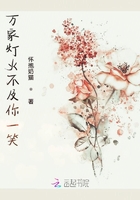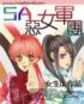赫伯特·胡佛同志其实是个工作狂。他坚持“早到迟退”,每天早晨八点半就准时坐在办公桌前,经常加班到深夜,中间只给自己15分钟的时间来吃午饭。大萧条期间,这位“勤政爱民”的好总统更是精神抖擞,全力以赴。不过,一个人如果最初选错了方向,那么他越是拼命赶路,就会背离最初的目的地越远。胡佛就是这么个悲情人物。在企图挽救小麦和棉花价格的努力惨败之后(众所周知,《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后果是天怒人怨),胡佛又本着屡败屡战的原则开始了挽救银行、铁路等大公司的努力。1932年,他组建了复兴金融公司,这也谱就了他和摩根财团之间最后的甜蜜恋曲。自从20年代以来就负债累累的铁路公司,是复兴金融公司计划的重点救助对象。与此同时,摩根银行正为了范·斯韦林根兄弟这个冤家的违约贷款大伤脑筋。突然之间,政府表示愿意拉阿利甘尼铁路这家劣迹斑斑的企业一把,这真是“馅饼天天掉,今天到我家”啊。拉蒙特等人心里乐开了花,对此自然是全力逢迎。臭名昭著的斯韦林根兄弟俩不久就欢天喜地地贷到了7500万美元,不过,让胡佛没有想到的是,复兴金融公司也就此落下了“富人福利院”的坏名声。
他的宏伟计划从第一桩贷款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复兴金融公司可算是胡佛最大胆的一项举动,后来证明,也是他跟自己开的最大的一个玩笑。这个计划矛盾重重,他想让复兴金融公司推进投资,但又限制它的中介功能,并且对资助项目严格设限,强调项目必须是“稳健的”和“可由银行担保的项目”。也正是因为如此,斯韦林根兄弟俩才有可能凭借自己跟摩根银行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从这里拿走了第一笔贷款。只能说,胡佛又选错了方向。复兴金融公司1932年发放的贷款有2/3流进了银行。然而,就在这年秋天,全国范围内的银行倒闭以摧枯拉朽之势发生了,这无疑挥了胡佛一记重拳。复兴金融计划宣告破产,胡佛落得个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仅联邦政府20亿美元救助贷款几乎打了水漂,更重要的是,他失去了美国老百姓的信任。“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胡佛很郁闷。作为传统经济理论顽固而悲情的代言人,事态的发展已经完全超越了他的掌控能力。可以说,赫伯特·胡佛本身也是个受害者,连带遭殃的,还有他拼命捍卫的那些理论。与此同时,胡佛和摩根的关系也开始走向了决裂。先是欧洲的贷款问题又出了岔子。
到1932年,被经济危机折磨得憔悴不堪的欧洲首脑们终于看清了一件事,那就是用战争赔款把德国逼上绝路不是个明智的选择。那一年,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在德国大选中获胜,这个一脸神经质的小个子愤青让人们嗅到了危险的味道,连一向不依不饶的法国也终于决定偃旗息鼓,不再闹了。于是,1932年,各国首脑在瑞士洛桑达成了“君子协定”:如果美国同意他们停止支付战争债务,那他们就同意不再向德国索要战争赔偿。球被踢回了美国人脚下。欧洲人的态度是明白无误的,你美国人别逼我还钱,我也不去逼德国。大家各退一步,喊声“一二三”,一起结束这要命的三角债。拉蒙特为此欢天喜地。欧洲的债务对于摩根银行来说,早就不是什么赚钱的香饽饽,而是烫手的山芋,世界经济眼看着被这些陈年滥账一步步地拖进了泥潭。同时,日本国内一系列残忍的暗杀活动也搅了摩根合伙人们的清梦,拉蒙特当然更不愿意看到他在欧洲的客户也落入极端分子手里。结束这场噩梦的机会终于来了。拉蒙特快马加鞭地把这个好消息传递给了华盛顿——正如你我所知,巅峰时期的摩根银行与白宫亲近得有时只隔着一部电话机的距离。胡佛的回应同样激动得不可抑制。
可惜的是,支持这份激动的不是喜悦,而是愤怒和沮丧。这一回胡佛选择了跟当时保守而缺乏远见的美国老百姓们站在同一个立场上,共同责骂这些天杀的、欠钱不还的欧洲佬儿。他嘲笑拉蒙特,说他大错特错,居然没有认清洛桑会议就是一个反美大联盟,“他们是在联合起来反对我们……也许他们已经解决了德国赔款问题,但他们是以最糟糕的该死方式来解决的”。老虎不发威,当我是病猫?胡佛同志这次发了狠,表示欧洲的债不仅要还,还得马上还(他不再延长为期1年的债务缓期,拒绝英国和法国推迟归还即将到期的付款的请求)。这就有点奇怪了。
国际债务延期偿付明明是胡佛本人在1931年6月一手促成的,如今事情总算有了起色,他怎么倒玩起了翻脸不认人的把戏?窃以为,胡佛同志当时也实在是顾不得这许多了——国内经济政策的几番失手搞得民怨沸腾,人心涣散,如今眼见大选在即,胡佛为了保住总统宝座,当然也只有先“顺应民意”。别忘了,每到关键时刻就把民众的矛盾焦点向外转移,这原本就是美国政客们最擅长玩的把戏之一。无论如何,对于摩根的合伙人们来说,煮熟的鸭子就这么飞了。拉蒙特等人对胡佛的失望可想而知。不过,与胡佛在空头投机问题上捅摩根的那一刀相比,这点小摩擦基本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