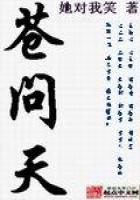一晃半月,丝毫不见女子的消息,赵枢心下明白,自己多半被人耍了。可那女子倒也不算太下作,不仅没将他盗版纳兰性德的那首诗占为己有,还散播了出去。没多久,这首诗便红透了汴京城,连带着他也红了,使他立时明白了许多当红明星的烦恼。
得知汴京城还有赵枢这么号才子,许多文人士子都跑到庄园来拜访,弄得他不胜其烦,只得在门口挂上牌子,非应聘先生者,不予接待,可一块牌子怎挡得住文人们的脚步?便是赵桓、赵佶也知道了此事,一番刨根问底之后,他终于待不下去了,直接跑出了庄园,让人寻不着。唯有熟悉他的人,方才知道他的去向。
马行街街尾有家食肆,如今已被改建成酒楼,赵枢离了庄园,便躲在这里。这里本是当年史文恭盘下,用以养活家小,眼下史文恭成了赵枢的人,又进了太子六率,实是没空打理,他老娘年岁又大,也打理不动,便将这里送给了赵枢。
赵枢欲开车马行,汴京城里自是得有个据点,有家食肆总比甚么都没有强,他便出钱将此食肆改建成了酒楼。最重要的是,将这食肆加高,他坐在阁楼里,正可看见当年的周宅。看着宅院里面的一景一物,他的心会变得平静。
“师父,你还好么?徒儿敬你…”赵枢凭栏而立,端着酒杯朝周宅方向举了举,便一饮而尽。
突地有个声音在他背后说道:“公子好雅兴,却在这里独酌,不知在下可否有幸搭个桌?”
赵枢闻言眉头一皱,便转过身来,却见一个三十余岁,学士模样的人站在他那里。这学士身高八尺,紫膛阔面,皮肤略微发黑,若非身着青色宽袍博带,头戴高统尖顶学士帽,倒似个武士。此人含笑叉手而立,脸上正气凛然,端的是气度不凡。
看着这人,便有种好感,赵枢放平眉头,伸手道:“兄台请坐,不知如何称呼?”
“在下陈东,丹阳人,以贡士入太学,眼下正在太学读书!”学士作了个揖,又笑问道:“不知公子又如何称呼?”
“在下姓赵名枢,在家行五…”赵枢也还了一揖,并招呼跑堂的另外拿了副碗筷来。
“原来是赵五哥,久仰久仰!”听得赵枢姓名,陈东又拱了拱手,可他突地觉得此姓名甚是耳熟,不由疑惑道:“似是在哪里听说过五哥,却是记不起来了!”
“汴京城里有数百万人,同名同姓者甚多,陈兄何必纠结,相聚便是有缘,且饮一杯罢!”赵枢是来躲清静的,可不想做大猩猩,再惹人来围观,连忙撇清并转移话题。
“此言甚是!”陈东倒也豪爽,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赞道:“好酒!有些日子不曾饮得这般好酒了!”
其实看见陈东便知道他囊中羞涩,须知太学在御街,若是太学生想要饮酒,放着近的樊楼不去,偏生跑到马行街来,若非情有独钟,便是嫌樊楼东西贵。陈东虽是博袍高帽,却浆洗的有些发白。
赵枢不由笑道:“陈兄今日便可尽兴,这顿我请!”
“如此便谢过公子了!”陈东笑着摇了摇头道:“过犹不及,酒之方物,多了却也误事。陈东身为太学学子,自不能滥饮无度…”
“陈兄所言甚是!”赵枢点了点头,端起酒杯呷了口,才笑问道:“陈兄既是太学生,怎地看似颇为拮据?”
陈东笑道:“奸不厮欺,俏不厮瞒。在下时常指责蔡京、王黼施政不当,故而被朝中官员所排斥,常常被拖欠薪俸。家中又是以儒嗣其业,自是没甚么进项。若非尚有三五个好友,与太学司正的照顾,或许早已饿死。公子听了此话,是否后悔请我吃酒?”
“吃些酒罢了,下次若想吃,遮莫来此讨要,由我会帐!”赵枢慷慨的拍了拍胸膛道:“朝中须得有陈兄这般正直之人,方能抑制那些奸臣。我尚有些势力,却是不惧蔡京、王黼。陈兄听了我家势力堪比二人,可曾后悔与我同桌吃酒?”
陈东闻言大笑一声,端起酒杯一干而尽道:“公子,在下敬你。即便你是蔡京、王黼家人,若不曾为恶,在下亦可与你为友。在下结交的是公子,又不是公子的家世!”
“好好好!”赵枢抚掌笑道:“好个对事不对人,兄台此言,当浮一大白!请!”
“请!”陈东也端起酒杯与赵枢碰了下,二人同时饮尽,又同时开怀大笑。陈东放下酒杯,却是笑道:“公子,刚才进来之时,在下见你脸上似有忧虑。在下既是吃了你的酒,自当与你排忧解难!”
“嗯?”赵枢闻言一愣,脸上立时露出几分喜色,他笑道:“若得陈兄相助,倒也是一桩美事。只是不知,陈兄对文武之争有何看法?”
“文武之争?”陈东道:“在下有个好友曾言,大宋崇文抑武过甚,早晚自食恶果。文武当携手共济,大宋方能强盛无忧…”
“说的好!”赵枢叹道:“真不知是哪位先生有此见地,恨不能与之一见…”
“公子想见他,却是难了!”陈东摇了摇头道:“此人前些日子因上书要求朝廷注意内忧外患,被官家认为不合时宜,已谪监南剑州沙县税务…”
“可惜了!”赵枢道:“不瞒陈兄说,在下却是个武人。前些日子收养了些孤儿,准备做家中亲卫。本想为孤儿寻些先生,却不想那些个文人听得孩子们要做军卒,竟不肯入馆相授,直愁煞个人…”
“我当公子为何事烦忧,却不曾想是这等小事…”陈东指了指自己笑道:“公子看我可能为师?”
“陈兄乃太学生,自是可以,难道陈兄愿意帮我?”赵枢激动的站了起来,可看见陈东点头,他又坐了下去,摇头叹道:“虽说有陈兄相助,却还是不够?”
“不够?”陈东端起酒杯问道:“公子到底收养了多少孤儿?”
赵枢不语,伸出五个手指。
“五十?”陈东疑惑的问了句,却将杯中酒倒进了嘴里。
“五百!”赵枢吐出个数字,陈东愣了下,竟是被呛住了。
“咳咳咳…五…五百?!”陈东咳了半晌,脸都涨红了,才喘着粗气道:“我说公子姓名怎地这般耳熟,原来你就是那个为了孤儿延师,而作‘人生若只如初见’的赵五郎!眼下人人都在找你,你却在这儿躲清静,还让我遇见。不行不行,我怎能这般轻易助你…”
“呃…”赵枢愣了下道:“陈兄,难不成在下大名竟已传遍了东京城?”
“何止,我听闻官家都已知晓!”陈东笑道:“既是被我遇见,也算你我有缘。你招不到先生,我却可以助你。若能作首好诗,我便去太学请些同窗来,若你作不得…嘿嘿…”
“不行不行!”赵枢连连摇头道:“且不说我诗才有限,便说当日那女子也如陈兄这般说。可后来我连人都寻不着,还被追得躲到这儿。若再来首诗,我真不知该躲到哪里去了!”
“由此可见,公子乃仁厚之人!”陈东笑道:“公子曾言,家世不弱于蔡京、王黼,却不肯做仗势欺人之事,汴京城中似公子这般的世家子弟已然不多,想来公子若能多多扬名,结交些清客文士,再招人给孤儿做老师,却也容易些…”
“陈兄,此事甚是不妥!”赵枢道:“结交自是得意气相投,今日见了陈兄,我一见如故。可若陈兄是那做作之人,我又岂能与你同桌而饮?我可不希望找些虚伪文人,污染家中清白孩童。”
陈东闻言不由问道:“你到底要教些甚么?”
“读书识字,却不学四书五经,只学些忠义爱国之道,以及兵法战策,保境安民之术!”赵枢自豪的说道:“这些孩子,将来可为官,可为将。虽不说出将入相,却也不会是只知吟诗作赋,不知民生的废物。”
“公子此言却是有些偏颇!”陈东道:“眼下只是朝廷大权尽在奸臣之手,那些忠臣无用武之地,方才这般…”
“忠臣奸臣?”赵枢冷笑道:“陈兄,你说如今的官员,真正懂得民生的有多少?便是你,若让你为一县之宰,你又当如何?”
“平讼狱,理民生,说教化!”陈东自豪的说道:“在下不才,若为一县之宰,虽不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却也能…”
“屁…”没等陈东说完,赵枢却打断了他道:“讼狱如何平?民生如何理?教化如何说?仓禀足而知礼仪,你可知如何使仓禀足?”
“这…”陈东愣住了,赵枢说的这些,他从不曾想过。一时间,竟是无言以对。
赵枢摇了摇头道:“陈兄,若是为了诗词而来的人,又有几分心思在教学上?诗词小道于国家何益?这些孤儿若学成,他日便是种田,也能带动周围的人多打些粮食,而不是成为那种整日里只会吟诗作赋,不通民生的蠢官…”
听完赵枢的话,陈东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今日赵枢给他的震撼,是他人生中不曾有过的。他放下酒杯一拍桌子道:“公子既有这般志向,我陈东若不助你,岂非枉读圣贤之书?我这便回太学,且等我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