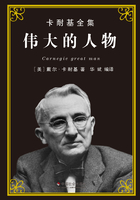陈桐生撒娇......准确的说是撒泼打滚,但小孩子无论做是多么都有股子娇憨气,她在殿里又嚷嚷口渴,又叫着这个不行那个不要,很是胡闹了一番,终于将桌子上摆满了各色小饮。
要在宫中搜集东西,光靠一个姜利言打着她的名号,恐怕不能收全,于是陈桐生出门前又打起了这个皇帝的主意,既然说他对她自己格外纵然关照些,那么胡闹想必也是行得通的。
尽管陈桐生后来知道了自己被陈辛澜卖出去给人家当媳妇的事实,但仍能,面色不改色的在地上乱滚。
皇帝对她越看不上越好。
陈恪看上去也没有那个心思,但也不为着她母亲的要求而对她区别对待,从前对她不太在意的惯着,如今还是不太在意的惯着,言语间便吩咐着宫人把桌面摆满了,陈桐生哗地扑上去,也不忙着喝,一个一个地拿来闻,终于闻到了一个她熟悉的,含有异香的液体。
陈桐生便望了宋川白一眼,因着飞光对她一直以来的阴影,她也没敢喝,抬起头问:“这是什么?”
陈恪意外道:“这不就是你成天喝着的散汤么?”
原来她一直都喝着的,这么一说陈桐生也不犹豫了,北朝人长期服用飞光,但却并未出现任何上瘾与身体衰退的迹象,可见北朝人所饮用的飞光,也就是陈恪口中说的散汤,与大周流行的飞光想必是不一样的。
陈桐生舔了舔嘴唇,在宋川白异样的注视下扬起昂起脖子咕嘟咕嘟灌完了,“哈”地长叹一口气。
散汤说不上什么滋味,但却与茶水一般有回甘,并且入口后极为爽利,简直是微甜醇香,又带着清爽。既不想茶水一样有不得不尝的涩苦,也没有酒喝下去后返上来的那个冲劲儿,果真还是男女老少都适宜的饮品。
陈桐生咂摸了会儿滋味,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问陈恪:“这散汤都是怎么做的?”
陈恪笑道:“感兴趣教人带你去膳房,亲眼看见了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这倒是个好主意,陈桐生还挺想知道北朝的散汤与大周的飞光,到底有什么不同。
这额外的想法了结了,陈桐生就准备问起正事来,她神神秘秘地拉着陈恪,让他遣散了所有的宫人,顺便把宋川白也赶了出去。
宋川白出门前微皱着眉,似乎并不认同陈桐生的做法,但他现在的地位委实也没有发言权,便只好老老实实地出门去,出门前,回过头来特地在嘴唇上抵了一指,意思教她谨言慎行。陈桐生还眨眼应下。
大门一关,陈桐生转过头来就问:“你为什么要杀她?”
陈恪还有些莫名其妙地:“什么?”
“陛下曾经娶了一个莫姓的皇后,然后将她杀了,”陈桐生问:“为什么?”
陈恪表情的变化几乎是在瞬息之间。憎恨,痛苦,恶毒,悲伤,与面对陈桐生的愕然。
然而这些表情又很快地从他脸上消失了,也不过是短短几息的功夫,他又恢复了原来不咸不淡的表情,笑了一声,很有些长辈对孩童言语漫不经心的意思:“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
他还觉得与辛澜有关:“你娘又与你说些什么?”
好,看来辛澜平日里看上去虽然不待见陈桐生,但估计也不愿意看女儿跟别的亲,少不得在背后还跟陈桐生说了什么能惹得陈恪头疼的话。
陈桐生装模作样地叹气:“还能说什么。”就把这句揭过去了,继续盯着陈恪问:“你为什么要杀她?”
“大人的事小娃娃就莫要参与了,”陈恪摆摆手:“回去跟你那几个玩伴侍从玩过家家去。”
陈桐生就知道是这么回事,开口就说:“是不是她表现的与你以往认识的不同?是不是即便到了你杀她的时候,她也好似完全意识不到危险似的,你刺她一刀,她也能爬起来接着走,再刺第二刀,还是如常的走。你接连地挥刀,她接连的受伤,鲜血淋漓,可还是向你走过去,脸色带着与平日里一样的笑容,甚至说......”
“够了!”陈恪猛然站起,胸口剧烈起伏几下,厉声道:“留着你的命不是让你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秘法来窃阴窥私的,陈辛澜身为祭司无能无德,其罪当诛,为着赎罪才生了你,莫要走你娘的后路!”
陈桐生原本紧紧抠在掌心的手指缓缓松开,几不可闻地呼了口气。
有反应就好,有反应就说明她猜对了。
陈恪的话不仅从侧面证明了她的猜想,坐实了莫皇后就是因为被变成了偶,才会被深爱自己的男人亲手杀害,更透露了另一件事。
“窃阴窥私”是个什么意思?秘法又为何有这么个功能?
陈恪是让她住口,而非反驳她荒谬的推论,也就是说她方才根据自己经验所假意描绘的场景,与现实很有可能是高度重合的。
但陈恪却没有去质疑陈桐生为什么能够得知这些,只是喝令她适可而止,也即是说......通过秘法,陈桐生是可以看见,或者说了解到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那么陈桐生如今深陷此境,是不是就与所谓的“窃阴窥私”的秘法有关?
这些念头迅速地从她脑海中掠过,面上也不过眨眨眼的事情,陈恪讲完便沉默了一阵,又开口道:“我知你天生早熟聪慧,也格外有股邪性,但这总归都不算什么。莫要太看得起自己的小聪明,秘法你学得了一时,你能用多久?你想跟以往的祭司一般,因为秘法而七窍流血暴毙么?那个祭司也才多大,不过二八少女而已。”
陈桐生现在也没法儿问这秘法是怎么一回事,只好板着脸保持着合理的沉默,看沉默的差不多了,她接着厚着脸皮问:“为什么要点紫烟香?”
陈恪的目光直钉在她脸上,简直跟刀子似的直接就从她脸上要刮下一层皮来。
“我说过了,不要走你娘的路。”陈恪加重语气警告道:“回去吧。”
“因为要防止其他人也变成这样,对不对?”陈桐生道:“还是陛下发现已经有人变成了这样,只是人数过多而无法一个一个杀干净,便只好用了这个法子。”
陈桐生也反过去盯陈恪的眼睛,观察着他任何一个细微的表情和动作。
这是一个不会掩饰,也可能是不屑于演示自己情绪的皇帝,他还年轻,但是不知道为何,想起那梦境中在宫墙上的陈恪,陈桐生却突然觉得他或许并不想当这个皇帝。
梦中除去那癫狂的情绪,还有那么一丝浓烈的,连陈桐生都能感觉到的愤怒的解脱感。
望着痛苦挣扎的臣民,他甚至会在内心涌出报复般的快意。
“想多了吧,”陈恪却在这时眼睛一瞥:“你娘告诉你那不是什么好东西?你殿里不点就是了!”
陈桐生想了想,觉得要问的也问的差不多了,不能光逮着一只羊薅毛,免得给人激着了,要给他反应的时间,便施施然的站起来,临推门前,她双手按在门上,突然道:“我母亲有何罪?”
“她不敬伽拉。”
“我又为什么要死?”
陈恪似乎反应了一秒才意识到陈桐生在说他的那句“留你一命”,便道:“你是伽拉之子,按理应回伽拉的故土,没人教你这些么?”
“回伽拉的故土就会死?”
“活人不进。”
伽拉的故土活人不进。
陈桐生就推门出去了。
宋川白看她主动把手交过来,对她方才做了什么好事,心里竟然就有底了,问:“你方才说什么了?”
“陈恪现在就开始怀疑我,接下来就应当去找辛澜来问一些关于我的事情了。”陈桐生道:“不过我们之前猜测的是对的,那个莫皇后确实是因为变成了偶才被陈恪亲手杀害的,而紫烟也确实就是为了这件事才点上的。”
宋川白抓重点问:“他怀疑你什么?”
怀疑她什么,本来陈桐生也不太能清楚,但在得到了陈恪对于紫烟的反应后,她心里也有了猜测。
陈恪所担忧的,也还是於菟。
“等我确认一件事以后就告诉你。”陈桐生眨眨眼,这回不故意累着自己了,两手向他一伸:“抱。”
宋川白先是一愣,随即笑道:“怎么这回不自己走了?”
“又不要跟皇帝讨水喝,还演什么苦肉计。”陈桐生嘴巴一撇:“走过来真是太累了,你不抱我就哭。”
宋川白嗤地一乐,弯腰把这个短腿短手的小东西抱起来,道:“别人不知道,怎么你自己也不知羞?都多大的人了,桐生原来也不爱叫人抱。”
“嘴上说着不愿意,身体还是很诚实的嘛。”陈桐生回嘴道:“我就是桐生,桐生就是我,我说要抱就要抱。”她还故意蹬了两下腿,差点把自己从宋川白怀里蹬出去。
宋川白无奈地把人抱好了,陈桐生靠在他的温热厚实的胸膛上,突然咕嘟咕嘟往外冒念头:如果我小时候遇见的不是什么清临,而是宋川白,会怎么样呢?
郑棠遇见了宋川白,受他的祸又借他的力,阴差阳错间成为了一朝之君,那陈桐生会怎么样呢?
她是否还会被千里迢迢地被带到大周去,记忆全无,像一个灵智未开的怪物一样茫然地活了许多年,把大周与北朝都活成了异国他乡呢?
她是否还会在这么多年后,依然接受的伽拉的诅咒和折磨?
陈桐生一开始是为了追根溯源,才想要进入北朝遗址,然而如今回到了北朝,却依然陌生的犹如路人。
在这个生她养她的土地上,在这个曾被她视作都城的地方,她的母亲,他的父亲,每个人都面目模糊,与她毫无联系,陈桐生回到北朝,才发现与她连结最深的,竟然是宋川白。
她在此唯一能够信任的,也只有宋川白。
陈桐生不禁抬起看了他一眼,由她那个角度看过去,宋川白脸型格外坚毅,但睫毛又显得格外长,高鼻直眉,真是再让人心动亲近的长相也没有了。
想比姜利言的绮丽,陈恪的英俊,宋川白多出来的,是他身周散发出来的,那让人觉得安心和愉悦的气质。
陈桐生收回目光,下意识把头往宋川白胸口蹭了蹭,而宋川白不动声色地,带着自己都没有察觉的笑意,轻轻地揽了一下她的小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