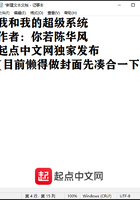与匪山间谈论,一句一叹尽心伤。
听了那“为匪不易”的说辞,杜安菱愈发对那些山匪生发出好奇来。苦笑后的疑问问的是怀王寨情形,不知道山里匪寨究竟如何。
“夫人一看便知。”
那化身为猎户的山匪如此言说。
去怀王寨一看吗?杜安菱确信这样做不怎么好办。
“不必了。”她苦笑。
若是要去那山中深处,自己还可能出的来?
怕是会跟瑜若一般,被留在那深山里面——杜安菱不是不信怀王的等人,而是不得不这么担忧一下。
毕竟,读过书的山匪不是乌合之众,能从一次次剿匪中生存下来的山匪集团绝对是有那么些不寻常的地方的——或许在山间作战,他们不会输给武备精良的正规军。
杜安菱自认为自己没必要白白把自己送进去。
……
“夫人可是怨怀王?”
耳边忽然传来这声音,却是那探子在一边询问。
怨怀王?或许有吧。杜安菱知道自己大概是难以和山匪摆脱关系后就认了命,对这些曾经暂住在自己宅子里的人没有什么爱恨了。
不过那探子为什么这样问?
回过头,却看着探子一脸真诚:“杜家娘子,妳不要怨恨我们怀王——他有些事确实做得伤了你的心,可他不像妳想着这样。”
杜安菱诧异了。
却看那人一脸真诚,走两步到自己偏前的地方侧过身一拜。
“杜家娘子该不会不知道我等为什么不时带些许山货出山来卖吧?”他问。
杜安菱摇头,她是真的不知道。
莫非?
“杜家娘子,怀王寨如今两大方法可得钱粮,一来是打猎买卖,二是远离这边,遥遥相对的那山里面有块地方挖得来铁矿。山谷里有些土地可供开垦,怀王寨粮食早可以自足。”
探子作揖——这和他的猎户形象是有些不符的。
杜安菱心惊。
却听着那探子继续说。
“抢商队地主富农这事怀王确实组织过,但我等已多年不曾做过了。”
“妳所怨的山匪,不过是深山里一村农人罢了。”
……
这话说下来于杜安菱无异于心头重击。
她怨怀王寨吗?
尽管嘴上说着没有,心里也一再以为自己并不在意这些——可心底还是对那群不速之客有着怨恨的吧。
可这怀王寨探子的话终究是信不得的,杜安菱在心底劝诫自己不能听信这种“一面之辞”。
可内心却终究有那么几分疑惑。
疑惑——那倒是缘于这山匪的来由,毕竟一开始就是走投无路的农人,到了山里面倒还真有那么几分安心种田的可能。
那这样,所谓“山匪”或许和隐士一个样了?
杜安菱心底浮现出这样一个想法,随即是与之相应的否定。
自己想什么呢——难不成还想那山匪是什么良善之辈不成?
他们确实有那么些可怜之处,可他们也是些犯下了罪行的山匪不是?
杜安菱这样劝说着自己,从心底否决了那一丝可怜。
却依旧好奇那“山里农家”的说法——“山间垦田?”
那探子便笑了,笑容里有终于说服他人的欣喜。
“可不是——不过杜家娘子,妳真应该进去看看的。”
进山里,还是往深山中去吗?
杜安菱再说一个“抱歉”,坚持自己的想法。
……
谈不齐不碍两人同行,将要卖去猎取物的探子也需翻过山脊,正和回屋的杜安菱同行。
同行之时路窄窄,不能并行时那探子让杜安菱先行一步。于是就听着她微微带喘的呼吸声,扛着录一步步向前爬上山岭。
时有突出的石块从左右两边伸出,或者带着刺的藤蔓树枝斜出路边草丛。杜安菱不时止步整理挂住的衣衫,因而眼角不时扫过扛着鹿的男子。
他就这么靠在路边的石块或树干上,看着她,嘴角带着微笑。
微笑吗?
那微笑看得杜安菱心里一怔——接着是避过他的目光。
可有大胆转过头来,问一句“怀王寨中近日如何”。
他闻言大笑。
“杜家娘子可是问对人了。”他道。
问对人了?杜安菱诧异的目光扫过。
“洒家行走内外,怀王寨里里外外多少事尽皆知晓,可不是问对人了?”他答。
依旧没有切入主题。
注意到杜安菱略带不满的目光投来那探子终究是说了怀王寨里的事情——却是一句大大的抱怨。
“杜家娘子,妳不知道妳那瑜若让怀王寨里面快要翻了天,整天搞出那么多事情来,还差点辩倒我宅子里的二当家!”
有这事?杜安菱诧异——“你们二当家是?”
“是胡书生!”
胡书生吗?杜安菱了然。
那个一心读得圣贤书的书生,倒是真有那么些可能跟自家瑜若争执——只不过被辩倒这件事还真是没想到。
不过还能辩倒怀王寨里的二当家!
杜安菱知道自己是小看瑜若了。
……
继续前行,很快道路变平易于行走,路边树木矮小被竹林取代。
山上多有这样的竹林,竹林里幽静凄清。百多步脚踏寸许厚的枯叶,道路有人行走也只是让竹叶堆积浅些。
竹林间,路转过几块凸起岩石。蜿蜒向下那头林木渐稀,抬头远望可见隐约有屋顶。
又到了自家宅院。
将就要分开,却听那探子一句,杜安菱脸色变了。
“二当家多次说,要出山与妳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