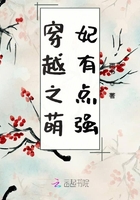浑浑噩噩数日久,天明日落事事愁。
出了人命的案子实实在在是大案,这事情一闹出来就被县里面的人注意到了,各种真的假的说法处处横飞——也不用一两天时间,周边人说着的就有十来种说法。
有贫苦农人说地主压价太狠导致那柯姓农民受不了,一气之下闹出大事的,也有一些流传地主见买地不成变抢地,却被农人反杀的——这些是农人间最为流传的说法。
可流传了一阵就变了味,什么“年轻农人”的阴谋都扯了出来。
说什么这一案件本来就是那贫苦农人的局,使唤一个人到前边去“误杀”了地主——之后一个“群情激愤”将那地主的财产抢了,进山中避祸去了。
这些说法杜安菱是不信的。
非但不信,看过一切的杜安菱还想过反驳——可反驳又有谁听?
她也不知道那些个人接下来的经历,不过据传言是揽尽了地主家的钱财,打开了家里的粮仓,还将地主的妻女与丫鬟绑了,进山林不知去向。
于是又有了“为劫色而行此事”的议论——经由陆红花传到杜安菱这里,她有些无奈。
不知道怎么评论好。
……
向南的窗户打开,阳光堂亮射入房室中。
看到前边来人,杜安菱从斜靠的床榻上直起身:“红花,又有什么新闻了?”
“县里面尹大爷下了令,全县买卖田地暂停一旬日子——告示都挂到村口来了!”
禁止买卖田地?这倒是个新奇办法。杜安菱适应着外面灼目的阳光,扫视一周后多少有那么些感叹生发。
“还有什么?”
“说是卖地的可以到城中去,县衙里按照原来的价格买——仅限最贫寒的农人可以去卖!”
陆红花说着时又看着宅主脸色,自从那一日回来就不知道听说过她多少叹息,想来那见闻还是真的骇人。
看着,却听到她开口。
“红花,这政令若要早些颁布,会不会就没有那天的事了?”
陆红花有些不解,却看着杜安菱又一次摇头。
“这样看来,倒是连尹县令都错了啊!”
……
民不议政,多少年就是如此。
官民之别何其大,这差距从读书人开蒙识字开始。识字的读书人天然高不识字的百姓一等,百姓向来不敢忤逆读书人。
身为市井小民的这些农人本能忌讳谈论什么为政不足的——而陆红花正居此列。
听了杜安菱的话语,一向的观念令陆红花一时不太好接受——却见着杜安菱有一次摇头,长叹一口气后下了床榻。
“你说,那么多人可以避免这事的发生,会不会——每个人都没有错?”
摇头,接着是一句“或者谁都有错”。
陆红花有那么一刻竟然无语了,听着杜安菱那边独白——杜安菱已经走到窗前,看着灼灼烈日下有些枯萎的杂草。
是不是自己想的太多了?
杜安菱心底隐隐约约有那么个声音在劝说自己,自己,不过是一个路人而已。
路人过客,何罪之有?
“红花,我出去一趟。”
或许,是时候散下心了。
……
没有往农田走,却上了后山。灼热阳光经由树林的过滤变为碎小光斑,风吹过荡碎一片斑驳如浪。
行山林,不久汗透衣衫。
上攀,下行,不多时是过去来过的地方。流入山洞的溪流没有多少水,迎着太阳一片白花花的河滩。
这里也是那一日跟瑜若相别的地方。
……
溪边逢猎户,猎户携来山间鹿。
猎户?不是的——杜安菱熟悉那所谓“猎户”,那“猎户”是怀王寨的探子。
鹿被放在溪边,猎户用溪水洗去鹿皮上沾着的血污。
洗到一半有所感,抬头却见着熟悉的人影。这探子一咧嘴,黄牙上有一两块没清理去的牙垢。
他看着杜安菱,杜安菱也看着他。
他诧异,她是知道山里有土匪的——可偏要往这里面来。
她也吃惊,不曾想竟会在这里遇上那探子打猎归来。
可吃惊和诧异并不是全部,杜安菱接下来却有着那么些不平静——不遇见不觉得,遇到了,她忽然有问题想问,很多问题。
于是就走上前,下到那溪边河滩上面。
那探子见状起身,说一句“令郎一切都好”。
杜安菱愣了一下,反应过来后苦笑——她并没有想过要问这个问题,哪怕这个问题最终也会问及。
她真正想问的是别的。
关于她亲眼所见的那件事的解答。
……
杜安菱记得,自己过去和那“胡书生”谈话时,胡姓书生说过山匪的来历。
那时候,胡姓书生一个“贫而无所以维生者将如何?”问得她哑口无言。
“或死于路途,或为匪也”是胡姓书生的原句,他说,因为贫穷而活不下去的贫苦农人成了今日的山匪,而越来越富裕的地主和商人导致了匪患的产生。
杜安菱知道是这样。
她想问关于那天的事。
她也问了。
“你知道那南边好几农人……”她说道一半,却被探子打断。
“知道,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探子说。
乌合之众?杜安菱有些疑惑了。
“大字不识几个,书也没读过几本的,能活得下去?”怀王寨的探子一针见血——“夫人真以为他们能成气候?”
“不懂策略的这等农人,用不了官军围剿,就是自个也会把自己困在山里边!”
杜安菱苦笑。
也是这样吧——看了当匪也不算是出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