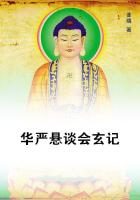盛宴有时尽,时光此刻短。一壶清酒眨眼干,四方天色晚。
总没有不散的宴席,诗词轮一遭眨眼便是半天。天色晚时鸟雀归巢,夕阳西落霞云一片如血。
终究是散去了啊。
时辰已晚,饮酒倒因为少有相佐的显得乏味了许多。有了退意的人再难聚集一起,纷纷要告辞了。
辞去就辞去吧,多少年皆如此。
太阴居士并没有挽留,只记着今宵又分别,往后又要一年才相会。
“去罢——明年记得再回来看看。”
叹一口气,送走一波又一波人。
直到徒弟到自己身前了,那屏风居士满脸不知悲喜。
太阴见了,眉头一皱。
“微之,你呢?”
“也想跟着他们走?”
……
是走,还是留?
屏风居士是有这样疑惑。
二月早已发春,稻秧此刻半尺高——过不了多久就插田,他金春想留下伴师父行农事,“悦心性”。
不是说他不想四处游乐了,实在是出去游玩也要找地方——而几十年过去,有些地方已经是游乐了“第三遭”。
“师父?”他问。
“去还是留?”太阴看出他眼底的挣扎。
“我还是再留此处半个月吧。”
话虽如此,心不对言。
“那记得走之前还我两个人的口粮!”
太阴一看事成,忙提出自己要求来。
“想要白吃白喝在我这住一个月,你想的美!”
太阴也是有骨气的,开口便是“有借有还”来。
弄得那屏风居士一时无言了。
……
“你这样,岂不是剥削自己徒弟了?”
走着,杜安菱忽而开口。
于是,太阴笑了——不仅笑了,眼里还闪现一丝异样神采。
“你不愿意?”
“或者说,你对他平白让我这山里多了两个吃饭的,是赞赏的?”
太阴一句话就到点子上,“多两个吃饭的”,可不是他自己和茗芬?
不过,貌似自己来山中,也带来三张嘴。
“我来这里,带来瑜若同秀儿,那是不是也该出去买些粮草相济?”
杜安菱笑了,半靠在树上,看得那才子窘迫了。
“怎么能——妳是我请过来的多带两个人无所谓。”
好吧,她服输。
自己确实是他请来的!
……
“妳不疑惑,微之他为什么要多留半个月吗?”
太阴居士见她发愣,难得挑起话题来。
问那屏风居士多留半个月的原因吗?
杜安菱笑了——屏风居士在诗会上的举动她不是没注意,目光倒是多追着茗芬看了几刻钟。
“一来,怕是不久农忙。”
“二来,茗芬那开蒙才一半,你这徒弟怎舍得自己徒儿!”
见她猜对了,太阴点头——“只不知,这半月下来,他会不会又要请示’再住一个月’了!”
两人心照不宣,并行下山路。
“妳今天那一阙,不错。”
太阴不知什么时候插嘴,惹来杜安菱一脸嫌弃。
“乱说什么呢!”
……
山谷里女儿言心事,总有些私底下情谊。
说到底是隐士这几间茅屋房间太少,令昨夜几人挤在一起——于是半夜闲谈,半夜同眠,这几人也熟悉了。
倩儿自然和秀儿谈到一起去了,茗芬倒找上璞若来。
“璞若妹妹——妳说,我多学会几个字,是不是就能让那些文人看上自己了?”
璞若一听变了脸色,这是什么话?
“妳这话从哪个地方听来的?”她问。
“是她跟我说的!”茗芬答,指着秀儿。
“这话不对。”
不是璞若想打击茗芬,而是她在春月楼里呆了十来年,看多了才子花心。
“那些文人心,妳怎么猜也猜不准的!”
……
“可是我看,那叫什么’南枝’的对妹妹就是有意。”
茗芬话里有羡慕,自己在那斟酒入杯中多少回,可不止一次见着邹南枝注视抚琴女。
那目光让她羡慕得紧!
“他啊!”
听了茗芬的话,璞若想起那词句里的兰,再联想往昔的邹南枝和自己,不禁摇头连连。
“我在他眼中,怕是还没有前途重要——妳不知,就前面这半年,他还失了我的约!”
苦笑,这又能怎样?
“想的多,伤心也多。”
既是对茗芬说的话,也是对自己的劝慰。
……
“这样吗?”
茗芬眼底微弱的光芒又熄灭了。
原以为多读书,长了见识,便可以走到屏风居士身边——原本就抱着“一步步走向成功”的心,怎想到会遇着这样一盆凉水浇下来!
“璞若妹妹——那我之前做的,都是白忙活了吗?”
第一次觉得读书是那样没用,茗芬挣扎着,有些沮丧。
“也不见得没用——那屏风居士,于妳也不是无缘。”
见惯了美人色,猜多了才子情,璞若认真开口。
“只不过——还需要些时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