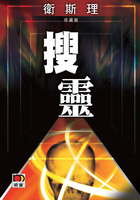“是的,我看上一个人了,”莫里斯老爹回答。“这是莱奥纳家族的人,一位叫盖兰的男人的寡妇,她住在富尔什。”
“我不认识这个女人和这个地方,”热尔曼答道,仍旧一副恭顺的样子,却愈加愁苦了。
“同你已故的妻子一样,她也叫卡特琳。”
“卡特琳?是啊,我真高兴能再叫这个名字:卡特琳!可是,如果我无法像爱前妻那样爱她,我会更加伤心的,因为这名字会更经常唤起我的回忆。”
“我告诉你,你会爱她的:这可是个好人,一位心地善良的女人;我很久没见她了,那时她就不是个难看的姑娘;当然,她现在已经不年轻了,她三十二岁。她出身名门,全家人都很诚实,她至少有八千或一万法郎的地产,她愿意把它们都卖了好在将来成家的地方重买一些土地;因为她也考虑要再结婚,而且我知道,若是你的性格适合她,她是不会嫌弃你境况不好的。”
“这么说,您已经把这一切都安排好了?”
“是的,不过还没征求你们俩的意见,这正是你们见面时要相互询问的。这女人的父亲和我有点沾亲带故,他过去待我很好。就是莱奥纳老爹,你记得吗?”
“记得,我在市集上见他跟您谈过话,上次你们一起吃的午饭;这么说你们谈了那么久就是谈的这件事?”
“当然啦,他一直在注意着你卖牲口,他发现你不仅干得挺好,还是个仪表堂堂的小伙子,说你看上去既勤劳又精干;当我和他谈起你的所有情况,说你和我们一起生活、劳动已经八年了,一直和我们和睦相处,从未说过一句令我们伤心的话或气话时,他就打定主意要把女儿嫁给你。坦白地对你说,这也正合我的意,因为她本人名声好,一家人都很正派,此外,我还知道她家的生意正处于兴旺时期。”
“莫里斯老爹,我觉得您有点爱财。”
“不错,我在乎这点。难道你对此无所谓?”
“如果您希望我这样,我会重视的,只要您高兴就行了;可您知道,我这人从来不操心这事:我们赢的利哪些归我、哪些不归我。对分财物,我一窍不通,我的脑子干不了这事。我熟悉土地,了解牛马,我会套犁、播种、打场、割草。有关羊群、葡萄、庭院、赚小钱的细活,您知道这是您儿子管的事,我不大插手。至于钱,我的记性不好,我宁愿分文不取,也不想为是你的钱还是我的钱争吵。我怕弄错了,把不归我的钱算到自己头上,要不是帐目一笔笔简单明了,我永远都搞不清。”
“这可就糟了,我的孩子,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你娶个有头脑的女人的原因,一旦我不在世,她可以替代我。你从不想弄清我们的帐目,可是如果我去世了,无法使你们意见一致,也不能告诉你们每人该得的份数时,这会引起你和我儿子的不和。”
“您会长寿的,莫里斯老爹!不要为您死后的事担心;我永远不会同您儿子争吵的。我信任雅克,就像信任您一样,再说我身无分文,可以归我的这一切都是您女儿留下的,它们属于我的孩子们,所以我很放心,您也放心吧:雅克不会剥夺他姐姐孩子的财产留给自己的孩子,因为他爱这些孩子几乎不相上下。”
“你说得对,热尔曼。雅克是个好儿子,好兄弟,也是一个热爱真理的人。但是,雅克可能会在你的孩子尚未成年前就先你而去,所以无论如何应该想到,在一个家庭里,不能丢下一群未成年的孩子而没有一位家长来指教他们,处理他们的纠纷。否则,从事法律的人就会乘机插手,搅得大家都不和,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打官司。因此,我们有必要考虑在我们家添加一个人,男的女的都行,我们要想到,有朝一日这个人就要管教全家三十来个孩子、孙子、女婿和媳妇,处理他们的事情……谁也不知道一个家庭能扩大到多少人,一旦蜂箱挤得太满,必须分蜂时,每只蜂都想带走自己的蜜。我招你为婿时,尽管我女儿富有,而你却很穷,可我并没责备她选中了你。我发现你很勤劳,我深知,对我们这样的乡下人来说,最大的财富就是像你那样的一双手和一颗心。如果一个男人带着这些进入一个家庭,那他带的东西就足够了。可是女人呢,这就不同了:她在家里合适的工作就是管钱,而不是赚钱。此外,既然你已为人父,并且又要娶妻子,那就应该想到,要是你将来的孩子一点都分不到前妻子女的遗产,你又过世了,那他们就要受穷了,除非你妻子自己有点财产。再说,你将为我们家族增添新的成员,养育这些孩子得花费不少钱。如果这只落在我们身上,我们肯定会养育他们的,并且毫无怨言;但是全家人的生活就不宽裕了,你前妻的几个孩子毫无例外也会缺吃少穿。如果人口剧增,而财产却不按比例增长,不管我们有多大的能耐,穷困还是会降临的。这就是我的观点,热尔曼,你好好斟酌吧,争取让盖兰寡妇看上你;因为她人品好又有钱,现在会助我们一臂之力,将来也会给我们带来安宁。”
“就这么说定了,父亲。我会竭力讨好她的,但愿她能看上我。”
“这样的话,你应该去看她,去找她。”
“去她那儿?到富尔什?离这儿远着呢,不是吗?再说这时节我们几乎没时间往外面跑。”
“如果是一场恋爱婚姻,就必须做好浪费点时间的准备;可这是一桩基于利害关系的理智婚姻,双方都不会异想天开,各人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所以会很快就定下来的。明天是星期六,你早点耕完地,午饭后两点钟左右你就出发,夜里便可到达富尔什;这会儿月亮还大着呢,路也好,而且还不到三古里地。那地方就在马尼埃附近。再说,你可以骑那匹牝马去。”
“天气凉快,我宁愿走着去。”
“好的,不过那匹马很帅,一个求婚的人骑着它去会更神气的。你穿上新衣服,带一块好野味送给莱奥纳老爹。你是代表我去的,你要同他聊聊。星期天,你可以和他女儿待上一整天,不管成功与否你星期一早上得回来。”
“就这样定了,”热尔曼平静地回答,可是他并不平静。
热尔曼像勤劳的农民那样一直安分守己地生活。他二十岁成了家,一生只爱过一个女人,自从他鳏居以来,他性子变得急躁、好动,但他没同任何女人嬉笑过。他的心里始终不渝地怀着一种真切的悲痛,他是带着不安和忧伤向岳父做让步的;不过岳父向来善于治家,热尔曼呢,全身心地投入家庭的共同事业,因而也效忠于这事业的化身:家长。热尔曼不懂,他其实可以反对这些正当的理由,不迎合大家的趣味的。
他仍旧很悲伤。只有很少的日子他不是在偷偷哀悼妻子中度过的,尽管孤独开始使他难以忍受,可是,与其渴望摆脱痛苦,他倒是更害怕重新结婚。他隐约感到,爱情若是出乎意料地降临于他,或许能减轻他的痛苦,因为以其他方式出现的爱情并不能使人得到宽慰。我们寻找它时得不到它;我们不期待它时它却来到。莫里斯老爹告诉他的这一冷酷的结婚计划,这个陌生的未婚妻,甚或人们对她的通情达理和品德所说的这一切赞扬话,都使他深思。他边想边走了出去,就像那些想法不多以免它们相互抵触的人一样思索着,也就是说不为自己设想出一些反抗、利己的漂亮理由,而是受着一种隐痛的折磨,对他就要面临的伤害毫不反抗。
这会儿,莫里斯老爹已经回到了田庄,热尔曼趁日落和天黑之际,正利用最后一点时间修堵羊群在紧挨房舍的一堵篱笆墙边捅开的缺口。他扶起荆条,抹上泥浆;这时,鸫鸟在附近的灌木丛中啾鸣,仿佛在催他快一点,迫不及待地要他离开,好来检查他的活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