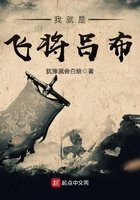1950年8月17日下午,关押在四德村拘留所的近百名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被集中起来,由邱所长宣布第二天搬家。叫大家回到监舍后收拾好背包行李和漱洗用具等什物,第二天一早便出发。
回到监舍后,大家一边忙着收拾行李,一边议论,猜测会搬到哪里去。
徐远举并不关心搬到哪里,他大声武气地说:“反正不是放出去,任谁搬到哪里也仍是蹲共产党的大监。我现在担心的是,明天是让我们乘车呢还是步行?如果光天白日地列队在街上扛着铺盖卷排着队走,共产党这不是故意拿我们示众出洋相么?太难堪了!”
周养浩一声苦笑:“破帽遮颜过闹市,既为阶下之囚,也只能把脸抹下来塞进裤裆里了。”
看守人员听见了他们的议论,在门边插话说:“你们好像情绪还很大,其实是好事情嘛,把你们这些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集中关在一起,不单监狱的环境更好,每月一个人16块钱的伙食标准,也要比这里要高8块,一般的犯人想去还没有这个资格呢。”
大家一听,这才高兴起来。晚上,监狱还打牙祭,吃回锅肉。被列入转移名单的人都显得很兴奋。
唯有王陵基因为向狱方提出带走他的生活副官的要求遭到了拒绝而痛苦不堪。这位前国民党上将、四川省主席,无论是在重庆,还是后来在北京,他的级别在战犯中是最高的,但是,他又是个独立生活能力最差的人,过去完全是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生活上的一切皆由姨太太和他的生活副官孔石贵伺候,即便是逃出成都后,为缩小目标,他一路上把跟随他多年的幕僚警卫全打发走了,最后关头,连大包大包的金条和手枪也扔进了川西一户农家院子中的水井里,可就是没敢扔下已经跟随他十几个年头的生活副官孔石贵。因为原因太简单不过,要没了孔石贵,他知道自己多在这世上活一天也艰难。
孔石贵也和王陵基依依不舍,流着泪说:“主席你走了,我今后再也吃不上好东西,主席也要受苦了。”
第二天吃早饭时管理员并没有催促,战犯们却比往日吃得快得多。出监舍时,王陵基还趁管理员不注意,多提了一只公用水桶,被渴望立功的刘进检举,遭到了管理员的严厉批评。
过了一会儿,哨子响了,管理员大声吆喝:“集合,快一点,到坝子上集合。”
到了坝子上,大家看见停着几辆大卡车,心里才蓦地一松,在管理人员的指挥下,大家依次登车。
囚车里装着的都不是等闲之辈,除了当年曾无数次在这块土地上发号施令,导演出一幕幕惨绝人寰大悲剧的徐远举、周养浩外,还有其他一些威名赫赫的大人物,他们是原国民党四川省主席、上将王陵基,原四川省党部主任曾扩情,川湘鄂绥靖公署中将主任宋希濂,第十四兵团司令钟彬,宝鸡警备司令刘进,西康省党部主任李犹龙等总共接近一百人。
在前后坐着武装士兵的车辆警戒下,三辆挤满战犯的汽车驶出了四德村监狱,缓缓前行。
街上自然有不少人驻足观看这支奇怪的车队。
不少战犯都把头偏向队伍里侧,以避免行人的视线。心里很想汽车能够开快一点,早一点到达目的地多好啊!但队伍的前面押队领先的一辆吉普车始终开得很慢。
当车队到达两路口的时候,忽然从观音岩方向开来了公安机关执行处决反革命犯的车队,这支装着战犯的车队只好靠边停下等着。
几辆先行的警戒车开过后,一辆车头前挂着白布黑字刑车横标的大卡车紧随其后驶了过来,刑车上五花大绑的犯人被威风凛凛的公安战士架着双臂,背上插着已经点了红的斩标,胸前还挂着一块纸牌,上面均清楚地写着处决反革命犯□□□。后面的一辆警戒车上,两侧站满了手持冲锋枪的公安战士,黑洞洞的枪口、寒光灼灼的刺刀,把路边的战犯们吓得魂飞魄散,赶紧低下了脑袋。那一天被处决的犯人大约有十多名。其中就有徐远举的部下、行动总队副总队长钟铸人和渣滓洞监狱看守长徐贵林。
徐远举骤然见到这样的场面,禁不住身上直打寒战。待行刑车队全部通过以后,战犯车队继续缓缓前行。自这以后,战犯们脑中不再是什么游行示众难堪的问题了,尤其是徐远举,心情更加复杂,既难受,又害怕,想不到自己的部下今天竟遭到这样悲惨的下场,也侥幸自己尚未被判决。但转念一想,自己现在是不是就保险了呢?今天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生杀大权完全操在共产党手里,万一哪天说我不坦白,是不是和他们一样的下场呢?又想今天这一幕怎么如此碰巧,偏偏就让我们给碰上了?是不是共产党有意安排,杀鸡给猴子看啊?对于人生,涌起了无尽的感慨。
当晚,徐远举在给他写坦白材料的纸上写下了这么几句:“昨日尊贵,今为阶囚,刑车去处,血洒荒丘。人生如此,真个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也百年身啊!”
出城以后,车队加快了速度,很快,便进入了歌乐山翠霭深浓、丛林清响的密林幽谷之中。进得深山后,一条小溪伴着公路蜿蜒,溪水清澈见底,水中游鱼可数。不久,车队驶过一座石桥,便停了下来。囚车中无数脑袋凑到了铁栏杆前,他们看到桥的左面,是个黑黝黝的深潭,沿途可见的溪水便是从这潭里流淌出去的。水潭后面是一座悬崖,一道冷浸浸的瀑布从悬崖顶上飘洒而下,在幽碧的潭水上飞珠溅玉,弄出一片细碎的声响。
“下车。”几个解放军从押送车上跳下来,跑到囚车边大声喝道。
囚犯扛着自己的行李,规规矩矩地从车上下来,听从一名押送军官的口令列队待命。多数囚犯好奇地打量着四周的情景,这地方真够清静的,三面环山,两边的山峰向下延展,包围了这片深潭。远远望去,山坳间匍匐着一座巨大的白色楼房。楼房后面簇拥着重重叠叠的林海。偶尔可见几处倚靠大树而建的岗楼,上面不仅有解放军战士的目光,也有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他们。
近百名囚犯成两列纵队,在战士的押送下顺着一条乡间的石板大道向着白色的楼房走去。
囚犯们众多的目光集中到了那座隐约在密林中的白色楼房四周。渐渐看清楚了,楼房四周裸露出的岩石上全都被涂上了白漆,树干也是白色的,环绕着楼房的墙,比石板坡监狱里的墙更高。墙上,还隐隐约约地看得见电网的支架……这一切,全都是国民党留下的。巨大的铁门,赫然出现在他们眼前。铁门上的横匾写着“香山别墅”四个大字。香山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别号,囚犯们在石板坡监狱里全都听过管教干部们讲重庆“11·27”大屠杀的事情,还看过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收敛共产党烈士遗体的纪录片,显然,这里就是半年之前杀害共产党人的现场之一——白公馆了。
沉重的铁门没有打开。高墙左边,几名解放军战士已经在办公室里等着。囚犯们依次被带进去,登记姓名、年龄、编号,领取一件印着白色号码的蓝色囚服。然后,从高墙边的侧门被带进去,迎面出现了一排楼梯,这排楼梯一半通向楼上,另一半通向楼下。侧门恰好开在楼梯中部转弯的地方,进门后可上可下。徐远举和周养浩刚一进去,来不及多看,就被带上了楼。楼上,宽大的走廊包围着牢房,四周的楼角,均有胸挎冲锋枪的战士看守。囚犯们跨进牢房后,都在忙着打开行李,整理自己的床铺,只有徐远举,将铺盖卷扔在墙边,靠墙而坐,久久一言不发,像一尊入定的老僧。
沧海桑田,历史已翻开了新的一页。离看守所三里之遥的五灵观1号、造时场军统局乡下办事处,便是他曾经多次发号施令的乡下老巢,白公馆保密局重庆看守所和二处渣滓洞看守所,都是过去徐远举指挥搜捕、关押革命志士的地方。毛人凤、徐远举等指挥的“11·27”大屠杀,血迹未干,尸骨未寒。今天,当囚车一进歌乐山,许多人还弄不清将把他们转移到何处时,他便预感到不是渣滓洞,就是白公馆了。等到被押进白公馆大门,他的心情沉重,思绪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