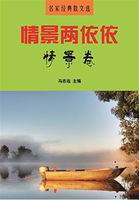小院里有石磨,石磨旁有辘轳,辘轳上有绳,绳上有桶,桶下有井,井里有水,清可鉴影。屋里有旧时人穿的三寸金莲,红紫金线,刺绣玲珑。一直不知道金莲三寸是什么样子,只知道很小很小,却原来是这样尖尖巧巧,足尖似针,可怜那样的时代,可怜那个时代里可怜的女人。屋里居然还有三十年前我的祖辈父母一直在用,现在已经难觅影踪的提梁壶,和我奶奶坐在院里纺线的纺车。一霎时有些眼花,仿佛看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盘腿坐在蒲团上,一手摇转车轮,一条胳膊伸得长长的,抻出一条细细白白的棉线,嗡……嗡……
一时间有些眩晕,不知道身处何地,我是何人。明知道这是井陉县的于家石头村,传说明代于谦避难藏身于此,后人一直繁衍至今。此地有石屋千间,石街千米,石井千眼,全村六街七巷十八胡同,纵横交错,结解曲伸,每条街道均以乱石铺成。石头瓦房,石头窑洞,石头平房,依高就底,顺势而建,邻里相接,唇齿相依,呼应顾盼。点缀其间的有深宅大院,古庙楼阁,遍布全村的有花草树木,春绿夏艳。这些我都不管,只希望有一天,心愿了却,再无遗憾,到这样一个安安静静的小村庄,赁一处清清净净的四合院,敲冰烹茗,扫雪待客,无人时吟啸由我,心静处僵卧荒村,听风听雨过清明,野草闲花中眠却,也算不枉了此生。
青梅老
梅葆玖老了。几年前在舞台上见他,还颇精神;如今再见,已是银丝相逐生,齿落舌也钝。六十八岁的高龄上台唱《贵妃醉酒》,颤颤巍巍,很让人有些心惊,再看两旁居然还有人护驾,简直就是一种嘲讽。都说他是梅兰芳先生诸子女中惟一酷肖乃父的,但见过梅兰芳留须小照,须发皆黑,眼神明媚婉转,对比其子老态,越见出时光残忍。
可是梅葆玖开始唱了。“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玉兔又早东升……”那样的眼神,那样的手势,那样的得口应心,那样的声调丝丝缕缕出来,就象飘飘荡荡展开一匹华丽的锦缎,说不出的美艳动人。无由想见其父当初演出的盛况,可是原来望梅真是可以止渴的,哪怕梅子已老,一样如临水照花,惊鸿掠影。
手里有一整套梅兰芳戏曲贴画,是我的宝贝,托朋友从上海远道买来。无事细看,论扮相毕竟是个男子,可是怕看他的眼神,丝丝入扣,随剧情一上一下地缠绕起你来。这个时候心就痛了,想:真要命,你不要做得那么美好不好?想起他在戏台上扮的昆曲《断桥》中的白娘子,一声“冤家”,一指头戳在相公额上,“唉哟”一声,许仙往后一倒,“她”赶紧一扶,又想起是这般负心汉,再轻轻一推,就是女子,若无柔情万种,也断然做不出这样举动。
京戏是慢的,一句话必定要拉成两三截,再咬文嚼字地吐出来,可是假如听了进去,没有谁烦,因为它滑得象丝,明丽如水,宛如在粗糙、灰暗的生活中突然冒出一个绝色好女子,或者白茫茫一片大雪里,猛绽开一树喷火蒸霞的梅。相信当年那么多力捧梅老板的人,是醉在了一场又一场的《霸王别姬》和《贵妃醉酒》里,醉得忘了谁是谁。一场大梦做过去,再带着一脸满足醒过来,全凭一个人的声音、眼神,手段,就带人赶赴了一场精神的盛宴,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
在《红毹纪梦诗注》里,张伯驹记王瑶卿当时评价梅兰芳的是这么一个字:“样”。这种样,就象丝绸做出来的华丽牡丹,宝相庄严,风华绝代。遥想当年,京剧舞台上红飞翠舞,玉动珠摇,攒三聚五,梅兰芳菲,一场华丽花事盛大上演。程砚秋象不事张扬的如珠茉莉,开在暗香浮动的黄昏;马连良给人感觉长袍大袖,飘飘然潇洒有仙人之概;麒派的周信芳老先生则是壁上挂着磨刃十年的龙泉剑,呛呛夜鸣,又如鸿门宴上的樊哙,瞋目而视,目眦尽裂;四小名旦中的张君秋先生的唱腔,每句第三、四字尾音上挑,是美人微微上挑的丹凤眼,无限风韵,尽在眉梢眼角。
可是,世上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随着名角相继谢世,一个粉光脂艳的时代终于走向终结。1958年,程砚秋去世,1961年,梅兰芳去世,1966年,马连良去世,1968年,荀慧生因被批斗引发心脏病,去世,1976春,尚小云去世……十万春花如一梦,大师仙去梅子老,还剩多少芳华共妖娆?
日前,看京剧后生王佩瑜在中央电视台11套开的个唱--齐派老生专场。一个谨约儒雅的年轻女子,穿深色西装,理清爽短发,戴斯文的眼镜,眼神清亮澹定,就那样一句句唱将来:“哗啦啦打罢了头通鼓,关二爷提刀跨雕鞍。哗啦啦打罢了二通鼓,人又精神马又欢……”比戴髯口、穿大袖地扮起来,别有一种剥笋露青之美。
年轻人唱老生,和老年人唱小旦与青衣,其实,都是美的吧。这样的美,既是对岁月风霜的抗拒和不妥协,又是尽着生命之树明亮着花的温柔姿态。青梅总有一天会老,不老的是情怀,老梅总会继发青枝,就这样一代代延续美的故事。
劫数与欢颜
读章诒和的《伶人往事》,通篇看过来,无非四个字:劫数与欢颜。
叶盛兰,中国京剧头号小生,祖籍杏花春雨的江南,故乡多水,白面剑眉的英气里竟然有水般的潋滟。唱做皆优,昆乱兼擅,小生戏会演,小旦的戏也会演。当年与小翠花合演《杀子报》,扎靠衣蟒的周瑜化身为官保的小姐姐金定,下跪为将要被杀的弟弟求情,哭得那叫一个恸,逗引得观众热泪滚滚。
程砚秋,抑郁端正,眉目含悲,活脱脱一副青衣相。他的唱腔鬼斧神工,“高出则如天外游云,低唱则似花下鸣泉”,乍听不惯,久听上瘾。
马连良好似戏牡丹的吕洞宾,风流入骨,飘逸斜出。一出《游龙戏凤》,别人扮演的永乐帝像流氓,他扮演的永乐帝才像皇帝--就有这样的华丽庄严。台下的姿态神情也颇可欣赏:说话疾徐适中,目不他瞬,动止中节,极艺术又极自然,圆通却令人不觉圆通,是由真性真情弥漫开的宁和之相。
看很早很早以前的京剧录像上面的演员阵容:梅兰芳、谭富英、马连良、裘盛荣、程砚秋、尚小云、言慧珠、俞振飞、杨宝森……那是一个多么奢侈的年代,一代名角攒三聚五,华丽得不像样;整个京剧天地梅兰芳菲,欢乐得不像样。
可是,马上劫数就来了!
一九五七年的叶盛兰,戴着右派帽子扮演小生,照样和杜近芳扮演的小旦在舞台上痴痴笑笑。他是吕布,她就是貂蝉,她是白娘子,他就是许仙,陈妙常和潘必正,梁山伯和祝英台,一个是妹妹,一个是哥哥,一个是儿夫,一个是女娘,一个是冤家,一个是天仙,梁兄死掉了,英台在坟前哭吃嚎啕,恨不能与梁兄白头同到老。可是,批判会上,杜近芳的近程子弹射得叶盛兰血迹斑斑:思想上他煽动我和党对立;政治上他拉我上贼船;艺术上他对我实施暴力统治;生活上他用资产阶级思想对我备加腐蚀……甚至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仇恨一路烧到舞台上,只要背向观众,杜近芳就会咬牙切齿骂一句:“你这个老右派!”转过身来,又是你侬我侬,轻爱蜜怜。
程砚秋一生钟爱《锁麟囊》,却终生禁演。从此他只有在梦里扮着薛湘灵唱:“在轿中只觉得天昏地暗,耳边厢,风声断,雨声喧,雷声乱,乐声阑珊,人声呐喊,都道是大雨倾天。”
马连良爱做人,会做人,劫难一来,却不能做“人”了,他连人的样子也没有了--红卫兵把他的家洗劫一空,古董、字画、摆设、玩意儿都砸碎在地,他瘫坐在自家的厕所里,面灰如土,穿的白衬衫全被撕破,脸上、身上都是伤。死前第三天拄着拐棍在剧团食堂买了面条一碗,还没到嘴,一个跟斗跌翻在地,拐棍、面条、饭碗扔出老远,三天后,1966年12月16日,与世长辞。
……
这不是劫数,是劫难。它不期而至,毁掉的不是几个人和几场戏,而是几百年、几代人含蕴出来的繁华盛景,珠玉宝光。可是,它又是一场劫数,否则怎么解释多少人不约而同,一起掉进厄运的深渊,一夜之间,欢颜就变了夕颜?
其实,说句冷心肠的话,没有那一场劫数,欢颜也会变夕颜。
我们的世界是快的,京戏是慢的,我们的世界是躁的,京戏是静的,我们的选择太多了,生命都被无数的选择淹没,浅尝辄止的欣赏习惯让我们再也无法专心倾听京戏发出的独一无二的繁响。
那一场全盛时代已经过去,留给我们的将是永久的空虚。这场空虚亟须一场新的艺术形式把它填满,可是,我们的思想如此凌乱,不知道何去何从。大道罔通成就了许多迷惘的生命。有哪一种艺术形式还能够让我们心无旁鹜,为它痴狂?现代文明汹涌而来,它那强悍的冲击力让传统文明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做什么?为什么?图什么?乐什么?一系列疑问悬在头顶,照耀着人们一边繁华,一边寂寞,一边吃喝,一边饥饿。
东篱黄菊和酒栽
赤日炎炎,逃进深山。干净清冷的空气,曲曲折折的山岭,疏疏落落几户人家,住几孔砖砌灰抹的窑洞。大锅贴饼子,柴烟袅袅地香。
我出身农村,老家还有二亩薄田。我早打算好了,等我跟先生都老了,城市生活也过够了,就解甲归田。三间清凉瓦屋,一个农家小院,院前一棵钻天杨,院后一块小菜地。五爪朝天的红辣椒,细长袅娜的丝瓜,丝瓜旺盛的时候,大家抢着往绳上缠,一捆一捆的黄花。长豆角在架上爬呀爬。
清早起来,掐两根丝瓜,一把红辣椒,在大锅里用铲“咝啦咝啦”地炒。或者到菜园子里拔两棵嫩白菜,旺火,重油,三五分钟出锅,香喷喷一碗菜就上桌了。再拔两根羊角葱,在砧板上噔噔地斩碎,香油细盐调味。煮一锅新米粥,上面结一层鲜皮。转圈贴一锅饼子。放下小饭桌,二人对坐,一边吃饭,回忆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那时候想必我的姑娘已经成家立业,一到过年过节,就会带着她的娃娃来看我们二老。小娃娃进门就一边叫“姥姥”,一边蹒跚着小短腿往前跑,我抱起来亲一下,再亲一下。
春天里薄幕清寒,五更时落几点微雨。这样天气不宜出门。现成的青蒜嫩韭炒鸡蛋,一小壶酒,老两口慢条斯理对酌。眼看着门外青草一丝丝漫向天边,比雪地荒凉。
夏天嘛,很豪华,很盛大的。远田近树,绿雾一样的叶子把全村都笼罩了。蛋圆的小叶子是槐树,巴掌大的叶子是杨树,还有丝丝垂柳。向日葵开黄花,玉米怀里抱着娃娃,娃娃戴着红缨帽,齐刷刷站立。
搬把凉椅,坐在树下,仰头看叶隙里星星点点的蓝天。一群群的白云像虎,猫,像大老鹰,一片片的草绵延着往外伸展,有的脑袋上顶一朵大花,像戴一顶草帽,摇摇晃晃,怪累的。蜜蜂这东西薄翼细腰,大复眼,花格肚子,六足沾满金黄的花粉。
然后秋天就来了,玉米也该收了,高粱红通通的,天蓝得像水,风渐渐变凉,使人忧伤。夜夜有如德富芦花的诗:“日暮水白,两岸昏黑。秋虫夹河齐鸣,时有鲻鱼高跳,画出银白水纹。”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冬天到处一片白,干净,利索,一场厚雪下来,枯草埋住了,路旁的粪堆埋住了,一切的一切都堆成浑圆的馍馍。走出家门,一无遮拦,一马平川的白色。
农村不是天堂,自古及今,它的象征意义都是多面的,既安闲隐逸,又辛苦寡薄。可是,人类从土地中诞生,成长,无论怎样显赫尊贵,抑或困窘贫寒,都有一种回归土地的本能的欲望。我是幸运的,将来有这么一个可意的栖身之所。其实,对于辛苦的现代人来说,哪怕没有丘山,没有田园,只要心在,梦在,一样可以东篱黄菊和酒栽。
曾是清明上河人
天色微明,睡眼半睁,住在东京汴梁的城郊,听不见和尚头陀走街串巷报晓之声,不知道是“晴”是“阴”。然鸟声啾啾,绿树染窗,这样天气,正好出门。
一路上薄雾疏林,茅舍掩映,河流穿树绕屋,蜿蜒前行,两岸杂花芳草,蜂蝶营营。猛见一树好桃花喷火蒸霞,映红了人面。
越往前走,行人渐多,河面渐阔。桥上行人捱肩接踵,小贩争相揽客,纷纷卖弄自家的好货品。一头乡下毛驴本来静等卸货,一扭头发现对面茶馆前也拴着一头驴,立刻发出“昂昂”的求偶声。两头驴一见钟情,奈何茶馆驴缰绳太紧,挣不动,于是这头乡下驴干脆撒开四蹄狂奔,吓得四周人惊叫一声。幸亏车夫眼疾手快,一把揪住驴缰,赏它两鞭,一个不知道躲闪的小孩子才免去一场大难。这边热闹,惊动了那边茶馆里的茶博士,也不敬茶,也不对客人酬应,也顾不上看杂耍人一上一下辗转腾空,只顾张大嘴巴呆看二驴调情。还不如近旁农舍里的两头牛,只顾嚼草,与世无争。
桥上驴马相争,桥下舟楫相争。码头上人头涌动,有的干脆跑到汴河大桥上,探出身子,挥舞手帕,冲着到港的客船大叫亲人。
下桥上街,马多,车多;人烟稠密处,有做生意的行商坐贾,有看街景的士子乡绅,有骑马的官吏,仪仗开道,威风凛凛,只可惜养尊处优惯了,眼见得疆界日缩,外患日盛,怎么保家卫国!有叫卖的小贩,有坐轿子的眷属,有背背篓的行脚僧,有问路的外乡游客,有听说书的街巷小儿,有酒楼中狂饮的豪门子弟,有城边行乞的残疾老丐,将身委地,尘灰满面,晚景凄凉。世界大都,万民来朝,几乘骆驼驮着西域商人的货品也来凑热闹,长得跟西域人一样,深目高鼻,有夷人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