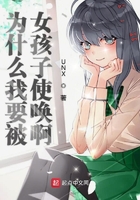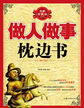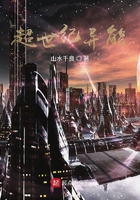说到戏曲艺人的艺术爱好和文化修养问题,人们常常提到京剧大师王瑶卿先生的名字。前年,在北京刚举行过他的百年诞辰纪念,被人誉为革新京剧的先驱。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于连泉诸名旦都曾拜于王氏门下。早年他被艺坛赞为“花部首席”,二十年代又被戏曲界颂为“通天教主”。他不愧为名副其实的戏曲教育家。写近代戏曲史和京剧艺术流变的,如果不提到王瑶卿的名字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王瑶卿之所以能成为培养戏曲人才的一代导师,有很多地方又得自他戏曲以外的功夫。比如他通文墨,精音韵,又擅绘画,尤其爱写菊花,故又名“菊痴”。罗瘿公赞他: “瑶卿花卉殊明丽”。李释戡说他“好写梅菊,深夜弗辍。”三十余年前,有人在北京偶得王氏早年所绘扇面一柄,视为奇货,这是可以理解的。
老舍先生即藏有他画的扇面。瑶卿是王氏的号,原名瑞臻,字雅庭,他的室名堂号则曰: “古瑁轩”。这个堂号,又说明王瑶卿是很喜欢古玉的。
我久已熟知古瑁轩为王瑶卿的堂号,却不知他之喜爱古玉已经到了入迷程度,甚至可以鉴别古玉之真伪,积历年的见闻还曾提笔立说。丙寅年(一九二六年)有一部《古瑁轩说玉》稿本写成。
今春偶见此稿本,又得许姬传先生赐教,证实王瑶卿果为古玉的鉴赏家。许姬传来信中说:“瑶翁善鉴别古玉,五十年前,余从天津来京探亲,曾数至其卧室兼书斋古瑁轩,瑁为三代玉,古代诸侯执圭,天子执瑁,余曾见原件,为白色不透明体古玉,古董行称为‘鸡骨白药铲’,盖象形也。”关于王氏的绘事,许姬传说,他曾见过画师颜伯龙与王瑶卿合作画龟册页。这都说明王瑶卿在舞台以外的爱好几与士林中人意趣相投。这自然要比一般戏曲艺人的修养高深,他之能别具见解,于京剧革新作出了贡献亦就不足为奇了。
《古瑁轩说玉》稿本用半壁轩九行一面之稿纸写成,共二十页。书前有王氏自叙,及目录十三题,题为:玉之出产、玉之名目、玉之本色、玉之受色、说碧琉璃、地土生熟境、新出土古玉年代质地、盘玉之功夫、辨玉之真伪、旧玉制作年代、灰提法、忌油污、养损莹。“自叙”不长,原无标点,今录如下:
余自幼嗜玉成癖。古玉一物,近时之人均喜玩弄,收藏者日见其多,然知者稀,辨者寥,虽有《博古图考》、《古玉图考》诸书,皆不能认定为凭据。古玉入土之深浅,出土之迟早,不可以时代计,安知三代之玉不早出土,而唐宋之玉不久入土耶?当分别有法以观之也。大凡古董一道,不可无凭据,又不可执定凭据。一物到手或真或假,变态万端,泥成说者非,狃成见者非,离成说而毫无成见者更非;心灵眼亮失之者鲜。余研究古玉二十余年,自己所藏有一百余件,朋友处所见不下千件,经眼一看真伪立辨,迄今未能自信而自觉稍有心得。丙寅春,病愈在家静养,就余所知者并参考诸书信笔写之,不过聊以自娱耳。
瑶青记于古瑁轩
据王氏所讲推算起来,他二十岁以后已经爱上古玉了。而王瑶卿二十岁时已在福寿班成为戏班的主角,稍后还担任了小长春科班的名誉社长。此时他已随戏班进过清宫,后来成为内廷供奉。
当时一场堂会戏,王瑶卿可得白银五十两。这些都说明他已经有条件来收藏古玉。那时旧京风习,古董店和个人经营玉石的小商人,常常有专走宅门,串大户人家的。当然也有串梨园界名角家的玉贾。王瑶卿恰有可能结交这方面的朋友,这更给他收藏和研究古玉提供了条件。
至于丙寅之春他养病的事,那是在一九二六年他的嗓音完全喑哑之后,从此他才专门从事传艺授徒的事业。这年他四十五岁,在各方面正是比较成熟的时候,于是撰写了这部《古瑁轩说玉》。
至今为止,这是我国唯一的一部以一个戏曲艺术家的身份写作的关于古玉的专门著作。
昔日唱老旦的老伶工龚云甫亦懂玉器,他本来是买卖玉器的商人,曾为票友,终于下海。但是,不曾听说他写过有关玉器的著作。至于王瑶卿是否就此向龚云甫请教过就不得而知了。
从“辨玉之真伪”一节,可以看到王瑶卿先生的丰富见解,多数来自他收藏古玉的实践经验。如说真正的旧玉,“其体质必温润沉重,精光内含,如属石类必干脆松轻,贼光外浮。稍一疏神,定难辨真伪。”因为旧玉受色之后与石最难分别,而世间“又有似旧玉之美石不下数十种”,连行家有时也会上当的。
据王氏介绍,宋朝宣和、政和年间,已有玉贾伪造“其色深透,红似鸡血”的名为“老油提”者,“今世颇少识家”,“玉贾常错认为南枣红、北枣红。近世玉贾,每以极坏夹石性之玉欲染红,则入红木屑煨之,其石性处即红;欲黑则入乌木屑中,或在石性处刷以酱油,用火煨之即有黑色。酱油浸入者成为黑紫色,谓之新油提。清乾隆帝,每因极好旧玉器受色太浅,传旨命加染颜色,俗呼为乾隆油提。此种并非伪货,若有好花纹者,价值甚昂。”这些知识,显然从书本上是不易查到的。
又说:“有名为瑞货者,是用近皮子处之玉做成器皿,染以淡赭色,一过十年,其色即退……”王瑶卿特别注明,“瑞货”是指北京瑞古斋玉器店的铺长姓颜的,专做旧玉。“近时伪旧玉有呼为颜货者,乃颜姓后人所做。” “近时又有一梁姓者,做假旧玉甚得名,是用硝镪水浸入玉中,再染以各种颜色,亦有瘢痕,极能乱真。新好古家受其朦骗者甚多,玉贾均呼为梁货。”这些像实地调查研究所得的第一手资料,不知王氏究竟是怎样得到的,我怀疑还是从玉贾朋友那里得来的,只有这些内中人才能对作伪的知识了如指掌。王氏的眼力当然超过了那些新的好古家,同时也说明他的聪颖智慧,自是一个有心人。此外,清末民初旧京富裕子弟的风习,从玩玉这一点上亦侧面地有所反映。当然,王氏既不是富贵人家出身,更非纨袴子弟,可也反映了他的习好。罗瘿公在《鞠部丛谈》一书中说:“瑶卿盛时极挥霍”,不过并未举出收藏古玉的事。那时有句俗话,黄金有价,而玉石向无定价,爱者为贵,无人喜爱的则一钱不值。这样看来,亦非一定是豪富人家才能玩玉。
王瑶卿还希望赏鉴家们留心一种“死玉”,不可不辨。他说:
“凡玉,性畏黄金。若玉入土中适与金近,久则受其克制,黑滞干枯,便成弃物。纵加盘功,顽质不化。若认为水银沁则误矣。”虽然作者还不能从矿物学的角度科学地说明其变化的化学原理,却也不能掩饰王氏对古玉知识的浓厚兴趣。
王瑶卿看轻新的好古家,同时对老嗜古家亦未必信服。如说新出土之旧玉质地未坚,或有断裂者,“老嗜古家”有谓“可以挂在贴身,常用人气养之,日久自能合拢。”对此一说,王氏持怀疑态度:“未曾试验,姑且记之。”
《古瑁轩说玉》既然是“聊以自娱”的著作,稿成后似乎不曾公开发表过,它在工艺美术史上有无价值我也不敢断定。仅从艺苑故实来考虑,无疑的这是一段极为珍贵的史料。
一九八三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