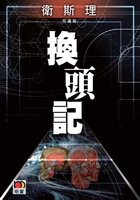伍宝慢慢净了手,扯了一条湿毛巾擦了黑皮汗津津的脸和脖子,轻声说,老表,晌午喝得不少吧?上级没说啥吧?
黑皮说,还是发廊那臭娘们找的事,狗屁证据都没有,只不过叫我多认识几个朋友。
伍宝分别给黑皮、胖子、瘦猴点了晕。最后问刘春庚,刘老板,他们可都精神焕发了,你点不点?不点,你迷糊着,小心他仨把你那两间发廊赢走了。
刘春庚敲敲他的头笑着说,伍老板,他们赢我不怕,我怕你害我哩。
黑皮说,捋掉他裤头,看看他长几个蛋,敢害你?
伍宝笑道,不用看,你们几个蛋,我几个蛋,大家都一样。我要有三个,会呆在坞坡镇?
胖子说,我总觉得你少一个蛋,委委琐琐,二妮子吧?说着便摸伍宝的头,说这个蛋算不算呀?四个人哈哈大笑。墙壁上的两只黑色苍蝇吓得展起翅膀,满屋子乱叫乱窜。伍宝举着蝇拍四下追打。那四人一撩门帘,俩苍蝇也紧随出了门,消失在明亮的阳光里。
文爷回来了。
几天不见,他的背明显驼了,像背着什么沉重的东西。很多人见他早上离开村子时没有拐杖,现在却拄了一根棍。他步履蹒跚,两眼无光,花白的头发上盖着一层浮土。伍宝刚在外面伸了两个懒腰,一扭头看见了他,赶忙迎上去,扶他坐进了店中圈椅。外面的天色暗了下来。
他倒了一杯水,文爷一气喝完。再倒一杯,又一气喝完。伍宝又倒一杯,文爷抿一口,握在手里,觉得有了点精神,马上想站起来。伍宝按住他说,老爷子,先歇歇,我给你洗洗头,理理发,再回不迟,反正也算到了家。
洗完了头。伍宝打开剃刀,文爷止住了他。文爷说,贤侄,你就给我捏捏头吧。伍宝合了刀,放回去。双手置于文爷头的两侧,做起了按摩。这种按摩,他只给文爷和老娘做。
坞坡镇之所以杂姓多,关系也复杂。是那年的滔天洪水造成的。逃往村外的人活下的极少。而走不掉的聚集在土岗上,洪水咆哮着,一望无际,滚啸而来。眼看着就要漫过土岗,水头撞上来的白沫都打在了人们的头上。这些老弱残兵齐刷刷地跪下来,祈求上天的保佑。说来奇怪,水都快冲到脚底板了,大人孩子一直跪着,没一个乱喊乱动的。到了晚上突然天上打了雷电。闪电擦着人们的头皮过去后,人们听见一声刺耳的马嘶,尔后觉得地面在摇晃。脚下的土岗长了起来,在闪电的映照下,人们看到土岗成了马,随着水涨而升高着。人们得救了……这传说,伍宝听文爷说的。他因此明白了为什么四板桥那边有马神庙。若不是小梅出事,文爷现在肯定正在门前的树荫里,摇着笆蕉扇,被一些人围住,讲东讲西呢。文爷可是前三皇后五帝天文地理地所不知呀。
仔细想想自己活了半百,有两个人影响了他。一个是清静坡林场的右派。别的右派垂头丧气,他不,整天乐呵呵的。有次他给右派理发,问右派牙咋掉了不少。右派说,牙太刚呀,太刚了易折,舌头柔,啥时都不会掉。这句话让他非常震动,他一下子明白了不少东西。另一个就是文爷了。坞坡镇虽有千口的人,真正能聊天的并不多。他有闲时,爱提了老酒,找文爷聊。这几天没见他,他果真语出惊人。
"今年春上马头处的炸弹一响,虽没伤人,我就担心出事。你想想,一个老日扔下的炸弹,在土里躺了几十年,咋会这时爆炸?"文爷说,"咱村逢马年就出事。"
1930年,庚午。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中原大战,咱这里年轻人不敢露头,怕抓壮丁。眼睁睁麦子熟了,壮年汉子不敢下地,一色的妇女儿童去收麦。时不时还有子弹擦着头皮悠来悠去,为了抢收,郑大腰的奶奶被冷枪打中左脸,死去。大半年里,壮年汉子不敢住家里,在洼地里东躲西藏。刘春庚的四爷就是那时抓走的,至今没音信。
1942年,壬午。谁都知道这是有名的"民国三十一年",水、旱、蝗、汤并起。土岗周围饿死了不少人。野地里连草根都找不到。雁屎都吃光。金大堤的爹跟刘春庚的爹因抢一粒雁屎打破了头。
1954年,甲午。春上也好,有风有水,风调雨顺,都以为是个丰收年。进入三夏便开始下雨,洼地里的水没人膝盖。眼看麦子要白白烂掉。群众只好下地去捞,那可是百年不遇的"水捞麦"啊,不少麦子在穗子里都生了芽儿,比绝收好不哪里。大家踩着水割麦头,瘦猴的爷被毒蛇咬了一下,当天死去。
1966年,丙午。"文革"开始,人像疯了。半夜里起床,敲着铜盆,迎接最高指示。冬天了,有人为表忠心,光膀子去光膀子回。砸了马神庙。秋季来了霍乱,家家难以幸免,死了八个老人。
1978年,戊午。搞承包本是好事。村东村西因为马车、牲口,农具等集体财产分配,发生大械斗,打伤三十多人,死一人。公社来了工作组,一住半年挨家挨户做工作,才剔除了仇气。
1990年,庚午。胖子家买来全村第一台电视,搬在村街上,人山人海围着看北京举办的亚运会,正为中国得金牌高兴,想不到呼隆一声,天上落下块磨盘大的石头,结结实实砸在电视上,砸进了地下,一村人惊悸了好多天。胖子的爷吓得拉稀,没多久就死了。
今年是壬午,一开春马头就爆了炸弹。想想以前的几个马年,不是天灾就是人祸,每年都有人死,今年我觉得也不会太平。谁知倒霉事就落到了俺家,俺家还不可怜吗?上天,你睁眼好好瞅瞅吧,咋不让恶人倒霉呢?小梅出事那天是五月二十五,"五月二十五,老龙去探母",每年这天都有一场雨,今年却没有,本不是好兆头,不该叫她去洼地除草呀。
他倒两杯酒,给文爷一杯,自己喝一杯说,咱得好好过呀!
文爷一口啁下,抖抖裤脚出了门。伍宝将拐棍递给他时,他没要。
躺进圈椅,他尽量放松神经,让自己平静。可是心一个劲地卟腾着,仿佛有人用锤子敲叩。只好起身,想再喝口酒。这时"四眼钱"来了,一进屋就让他拉亮电灯。外面已经黑下来,他却不想拉灯,他愿意在黑暗中静呆着。他似乎还没有从文爷堆砌的马年故事里走出来。"四眼钱"一进屋就嚷嚷,你挣恁多钱,还在乎几个电费?快拉灯,快拉灯。你都叫我想起美国的"9.11"事件了。灯亮后,映出"四眼钱"的焦急像。
伍宝说:"人家拉登也没惹你,你急啥?""四眼钱"说:"他是鸡蛋碰石头。"伍宝说:"肯定是美国把他欺得没办法,才去碰的。""四眼钱"说:"我碰上金大堤,是鸡蛋碰鸡蛋啊。"
"金大堤已下了最后通谍,再不把砖头运到他家,他可进城去了,反正他也不下洼锄地。""四眼钱"说,"老兄,你得想办法呀。"
接过"四眼钱"的烟,吸了两口,感觉烟挺香。他又吸,又吐掉。见"四眼钱"的着急样,他笑了,轻描淡写地说:
"你把砖运给他不就结了。"
"我能运给他,还来找你干啥?""四眼钱"说。
"四眼钱"这些天往砖场和王玉娥家跑了好多趟,腿都跑细了,脚都跑大了,心都跑烂了,肺都跑炸了。结果是把自己变成了皮球,让砖场和村长王玉娥踢来踢去,就是找不到可进的球门。王玉娥说建校款还没够,欠着刘春庚,多一笔也没什么,反正肉都烂在了锅里,没有给狗衔去。一个大学校都立了起来,一堵围墙算什么。让他到砖场去,让他们送砖到学校。刘春庚似乎知道他要砖,就是不给面见,好不容易见着了。他说建校款都该几年了,也该还了吧。我这里的砖头是泥巴烧的,又不是泥巴捏的呀,你总得给点押金吧。"四眼钱"说了王玉娥的意思。刘春庚哈哈一笑,说,村里穷得丁当响,我害怕账给黄了。第二次见面时,口气松了,却推脱说,眼下的砖头都有了主儿,不能乱动。这阵子农忙,出的砖头少,一闲下来,人家该建房了,万一到我这儿没了砖,我的信誉受了威胁,生意就不好做了。再等等吧。
"我是能等,人家金大堤可屎憋着肛门呢,我都牙疼几夜了。""四眼钱"说。
"那只能再去找王玉娥,她是村长,有办法。找我不中。"伍宝说。
伍宝坏坏地笑了。"四眼钱"明白他有了主意,马上凑近,递香烟。伍宝指指斜对面的杂货铺说,去弄两瓶白酒去。"四眼钱"问弄啥酒,伍宝说就光身仰韶吧,三块五一瓶。"四眼钱"扶扶镜框,兴奋出了门。一会儿回来,拎了四瓶,往桌上一墩,伍宝上前想看看摸摸,他支开他的手说,酒是加倍弄回了,主意呢?不出主意,我可要退回去的。
伍宝趴在他耳边嘀嘀咕咕一阵,连屋里的蚊子都听不清内容。
"四眼钱"连说:"好,好,好主意。"
他沿着村街,一路小跑,去了郑大腰家。郑大腰的三个女孩辍了学。他到郑家时,郑大腰还很惊奇,说看来让学习"三个代表"是对了,校长都来家访,送先进文化来了。"四眼钱"递他一支烟,坐下来一本正经地说,让孩子复学吧。郑大腰乐了,复学?简单,书钱杂费哪弄去?"四眼钱"说,这个我想办法,你只要应我一件事,我保证让你三个孩子全都小学毕业,不让你负担。郑大腰说,有这等好事,我应你十件事都成。"四眼钱"伸了一根指头,在眼前晃一晃,强调说就一件。
"不上访。"
"我都成了废人,不上访,出不了这口气。"
"你上访,解决没有?你别去了,仨孩子上学的费用,我跟乡里说说,全免了,中不中?孩子也大了,得想想名声。你瞅瞅金大堤,名声差,孩子连对象都没有吧。咱这是农村呀,你得面对现实。有病,咱慢慢看,比这样瞎磨强。耽误了孩子,事大。"
郑大腰不言语了,只吸烟,沉默半晌说:"我听你的,就是有点咽不下那口气。"
由郑大腰家出来,"四眼钱"高兴得只想唱几句。到了寂静的学校门口,他才哼出了,"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结果高音上不去,差点劈了嗓子。他没吃饭,蹬起自行车,往乡里去,也不怕黑洞洞的坎坷土道颠得他屁股疼。
到乡政府,找信访秘书。这人单身住在乡里。乡政府大院夜里没几个人。院子里有台彩电,几个人正看电视连续剧。"四眼钱"一眼认出其中一个光着膀子,摇着蒲扇的人就是信访秘书。
提起这人,整个坞坡镇都会发笑。前些年他曾在坞坡镇蹲点,突击计划生育。开会时讲了一段话让人学来学去,品出了不少可笑的滋味。那天他说得很有激情,声音高得吓人:
"一说结扎,我就头疼。一说下环,我就张不开口。一说流产,我就没脸见人。但是上面压的,旁边挤的,下面又乱动,我夹在中间实在难受。就是头疼也得结扎,张不开口也得下环,不想露脸也得流产。明天,我带头去结扎,大张口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