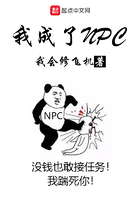关山月去温玉府里,站在门口。温玉的府就一个院,温玉在书房看见他了,急忙取过雨伞把浑身湿透的关山月带进屋里。关山月浑身湿透了,对着温玉一笑,绝不是原来的笑,这个笑是悲凉的凄苦的难受的。温玉给他擦了擦水:“你总要这样吗?你一直表现出笑,但你忘了笑本来的意义。”温玉转身去拿什么。关山月坐下,用内力烤干了衣服,一言不发。温玉拿过一碗姜汤:“喝了吧。”关山月接过来,喝着喝着喝哭了。关山月自从当上王爷这十几年来,从没哭过,不论高兴难受都是笑着的。“这就对了,不要以为你笑着是坚强,所有的坚强都是为了伪装起胆小。”关山月的眼泪落到姜汤碗里,他放下碗:“温玉,我是不是变了。”“人总会变么。”温玉也坐下说。“我变了,变成了小时候最痛恨的朝廷狗。”温玉看着他没说话。“我看着丁叔死在我面前,我是能救他的!”说着,刚止住的眼泪又不由自主的流了下来:“我所谓的顾全大局,不就是惧怕丞相吗?”说着他站起来,拿起碗摔向地上:“我不是人!”温玉走过去,拍着关山月后背,淡淡的说了句:“碗是我的。”关山月看着温玉,温玉让他坐下:“我们陪丞相下棋,没有主动权。”“那就只能被林迹牵着鼻子走吗?”温玉给他倒了杯茶:“以静制动未尝不可。”说着给自己也到了一杯。“以静制动?就是丞相杀了人我们给收尸?”“置之死地而后生。”“你......”关山月情绪很激动:“呆子!”温玉搂着关山月,和他勾肩搭背着:“你不该想想如何为你丁叔报仇啊。”关山月挪开温玉:“对,报仇,回王府。”往外就走。温玉喊了一声:“雨停了再走吧。”也没拦着他。关山月回了王府,一进门就大叫:“虎牙,虎牙呢?”吉隩站在门口:“虎牙?他没来过。”关山月又问:“丁一呢?丁一呢?”关山月已经进到了屋里。“丁一回来,就把自己关到屋里了。”吉隩有些奇怪。关山月进了书房,也把门关上不出来了,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关山月和丁一都没出过门。第二天,关山月一早出门,没吃早饭就离开了。他去找了国师,在景府外碰到了虎牙,虎牙要约他去河边,他同意了,跟着去了。虎牙在河边吹着风:“关,山,月。”他一字一顿的念了一遍。关山月捡起快石头打了个水漂,笑了笑:“你是第一个这么叫我的。”“你爹娘不叫你名字?”虎牙问他。“我爹,娘。”语气淡云流水。“大将军待你......怎样?我听说。”她顿了顿。“你听说的是对的,我爹他,传言是真的。”关山月叹了口气,看着水面的涟漪。虎牙小心翼翼的问他:“你爹真的待你不好。”关山月一笑,坐在河边:“我也不怕跟你说,是。”他叹了口气,虎牙在他身边坐下。关山月笑着:“我爹,总是莫名其妙。他骂我,我觉得他是望子成龙,但其实不是。他不喜欢我娘。因为我娘,所以不喜欢我,而我又是他唯一的儿子,也许他想对我好,但是看见我娘,又觉得不能对我好,说白了......”他又往河里扔了个石头:“就是面子。”虎牙能看出,关山月虽然表面云淡风轻,微微笑着,但内心的波澜是思潮暗涌的,以至于眼圈已经发红了。虎牙看着河面:“好了。我问你个问题。”关山月喘了口气,平复了一下心情:“问吧,反正也跟你说了这么多,再说也无妨。”“你,如果有个仇人,而这个仇人是你的兄弟,你会怎样?”“我没有兄弟。”“我说如果。”关山月一笑:“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虎牙一笑,没说什么。虎牙站起了:“走了。”关山月也站起来,虎牙已经走了。他又来到景府,直接进去,门口的家丁没拦住,给国师送了信儿了,国师出门相迎:“王爷来了。”关山月一笑:“先生进来可好。”“好。”国师也抿嘴一笑:“请。”二人来到堂内:“王爷请上坐。”关山月一伸手:“先生请。”国师坐下,关山月也坐下。“丁尚书死了。”关山月整着袍襟说。“我的确知道。”国师一摸胡子:“可我不能告诉你。”关山月一咬牙,没说话。“我还知道关于你的,关于温玉的。”国师又一笑。关山月看着他。“都是丞相说的。”国师吃了个葡萄:“嗯,不错,来。”说着递给关山月一颗葡萄。“丞相说的?林迹又病啊他告诉你!”关山月说到这,心情有些激动。“这葡萄可少,吃吧,没事。”“说啊,咱们俩......”关山月说着,不由站起来。“王爷原来可不是这样的,今个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关山月坐下,他今日心里总有些不安。“林相高啊,工于心计,设置大局。他设好了局,把事儿告诉你,让你知道办不到,最后入局按照他的路数走。”关山月听着:“拿着引子是。”“有两个。你,温玉和丁尚书。”“啊?还有这是三个。”关山月忍不住挑刺。“你和温玉是入局的门,丁尚书是设局的原因之一。”关山月盯着国师。“现在,带你入局的是丁家的老五了。”关山月看着国师,笑笑:“先生,你还知道什么?”国师转头盯着他看着,也是笑笑:“我知道的很多,丞相知道的,我都知道。”关山月笑着:“那你让我陪你们下棋?”他咬着牙说。“我苦于没有证据,而林相威胁我的筹码就是你们哥俩,这棋你非下不可,下不好就把命搭进去了。”关山月探身,离国师很近:“我好好的在外地,莫名其妙的卷入了你和丞相的争斗。还有性命之忧,我何苦啊我。”说着站起来,走到了国师的面前。“不。”国师抬头看着关山月:“王爷你错了。不是我和丞相,是丁尚书和丞相。”“不是,丁尚书和丞相和先生又有什么关系。”关山月又往前探了探。国师用手推了一下关山月的脸,站了起来:“丁尚书有林迹通敌的证据,林相要杀他毁证据。”“然后呢?”“然后。”国师拍了拍关山月:“丁尚书被下属告发,入狱,满门被杀......”“这我都知道,然后呢?”关山月有些着急。“然后丁尚书跟我说了,好像半夜也跟你说了。”“再然后呢?”“再然后你都知道了。”“没有别的要说的?”关山月有些恼。“没有了。”国师一笑,走了两步摸了摸放在桌子上的花叶。关山月直接出门走了,国师也没看他:“恭送王爷。”
关山月走在街上,又掉头转向了丞相府。到了林府,家人带的路进去,正巧丞相刚刚摆下棋局,关山月来下棋。关山月坐下,笑笑:“丞相黑子先行。”丞相落下一子:“怎么,从国师那讨不到好处,来我相府了。”关山月也落下一子:“我只是不想成为棋子入局。”“可你就是棋子。”林迹又落下一子。“好棋!”关山月举着棋子:“就算我注定是颗摆阵棋子,也要明白自己在哪啊。”关山月想了想,落了一子。“棋子要是知道了位置,不知还会不会任人摆布。”关山月一笑:“你与国师下棋,我是他的棋子,我乱了他的阵脚,怎说都对林相您有益。”林相笑笑:“王爷好棋。”关山月笑笑,拿起扇子搅乱了棋局。林迹看着他:“你愿意听?”关山月打开扇子扇扇:“愿闻其详。”“好,让你做个心知肚明的棋子。你娘叫什么?”关山月一愣,林迹又说:“那都不要紧,你只要知道,那不是你亲娘。”关山月更愣了。丞相一笑:“爹也不是亲爹。”关山月收了扇子。“你爹是谁,我不知道。你娘为了夺宠,害了正室的儿子,也自己的儿子,所以就找来了你,作为关挫的儿子。”关山月收住了笑容。林迹笑了一下:“还受得了吧。”关山月看着他:“我......有些乱。”“还要听下去吗?”丞相笑着问他。关山月也做出了个笑容:“你继续说,说下去。”“好,说。你爹后来知道了,要找到那个孩子。那个孩子我找到了。”丞相笑出了声。“谁!”关山月抓着林迹的胳膊。林迹看了看他的手,关山月赶紧放手,林迹说:“这个人,就是......”说道这,国师突然推门进来:“林相,一向可好。”二人一齐看向国师,国师施了个礼:“王爷也在啊,臣不知王爷驾到......”关山月有些不耐烦:“行了,起来起来。”转过身看着林迹:“告辞!”林迹冲着他出门的背影说了句:“知道此事还有三人,我,景先生,当今皇上。”
关山月回到王府,想着这些事,来到了丁一的房间里。丁一在床上躺着。关山月过去,丁一坐起来,他问他:“害了丁大人的证据在哪你知道吗?”说完又觉得没有,一个四岁的孩子知道什么。丁一有些浑浑噩噩:“王爷,钥匙,钥匙。”说着掏出钥匙,关山月接过来,发现不对,抓着丁一的小手想:这么烫!用手摸了摸丁一的额头,也是烫,这才注意到丁一那红红的笑脸,他赶紧叫来吉隩,吉隩一看:“他这是染了风寒。”写了张单子,关山月拿过单子就走。他跑去药房抓药,他心里乱,脑子更乱,他快速奔跑在街道上,他已经不知道该干嘛了,他想走一步看一步,但是,这些事情又让他不得不想。他抓了药,回来交给吉隩,丁一又睡下了,他总觉得丁一知道什么,现在,只能治好他。关山月觉得,自己事情很多,不知道该干什么,但是想一件件完成时,又一件都想不起来,他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他疯了一样,冲出了门,他又开始狂奔,街上的人觉得他是个疯子,没错,他现在就是个疯子,他穿过热闹的集市,冲着没人的小巷大喊,喊得撕心裂肺,只看到一群惊鸟飞天而起,听到院子里的鸡叫。他跑到河边的树林里,他用轻功上树下树,用内力打向树干,再用扇子扇动树叶射杀天上的惊鸟。他跑着,打着,吼着,一头钻进河里,经过冰凉的河水洗礼,他不但不觉清醒,反而更加乱了,不过心情还是好一些的。夏天的天总是爱下雨的,淅淅沥沥的又下了雨,天色将晚,只见的落日红阳,太阳天下小雨,雨下的让人惬意。他从河里出来,转着圈的用轻功和能够从河里出来,落到岸上,衣服一成潮的,不在滴水,但被雨水一打,又湿了些。岸上站着一个人,拿着伞。关山月不由自主的向她走了过去,是虎牙。虎牙把伞递给他:“王爷,冷静冷静,今晚在‘竹雨楼’,我请你吃酒。”说着上树走了。关山月拿着伞一愣,看着虎牙走了,转身绕过河直接去‘竹雨楼’了,没想到虎牙已经在那等他了。二人坐在楼上雅间,看着街上人来人往,青色的天上下着小雨,虎牙要了壶温酒,给他倒了一杯,自己先干了。关山月拿起酒喝了。虎牙什么也没问,关山月什么也没说,就是一杯杯的饮着酒,喝到脸已经微微发红,关山月先醉了,他喝了好多酒。他并不想借酒浇愁,因为他不想愁更愁,但是他还是喝了,就是想喝,而且喝多了,他从没醉过,虎牙是第一个看到他醉相的人。
他喝多了,失声痛哭起来,只是哭,什么也不说,他从没向今天这样,虎牙也没问,看着他哭,也没劝他。后来醉晕过去了,被虎牙扥这领子拎回了王府,扔到了门口。酒宝出来时看到了,把关山月抱回了房间,吉隩给熬了碗醒酒汤给他灌了下去,关山月还是昏昏沉沉的一副醉相,倒在床上睡了。关山月睡梦中嘟嘟囔囔,酒宝和萌槐一直守着他,又这么两个亲卫真好。
第二天清晨,关山月一早就醒了,可他并没有起来,醉酒后的头疼让他有些受不住,还是晕晕乎乎的他用手揉着脑袋。萌槐靠在墙上睡着了,摇摇欲坠,酒宝也趴在床头迷迷瞪瞪,关山月的动作酒宝醒了,急忙站起来,扶起关山月,倒了杯茶。关山月喝了茶,掐着自己的人中低着头。酒宝问他:“王爷,没事吧。”关山月抬头看了他一眼:“酒宝,”说着低头看了看自己:“我这是......”酒宝笑了一下,看着关山月又收住了笑容:“王爷,您昨晚喝多了,被人抛在门口,我们把您抬进来了。”关山月揉着头看着酒宝:“我昨晚喝多了?”酒宝实在忍不住笑,转头看见了差点摔倒醒来的萌槐,关山月看着他们,揉了揉眼:“你怎么知道我倒在门口?”酒宝憋了憋笑,转过头:“不瞒王爷您说,我从小喝酒长大,酒的味道我很远就能闻到。”说着还是笑了一下。萌槐拿来了关山月的衣服,关山月穿着衣服,想着事情。萌槐从外边端来了早饭,关山月也没吃,直接出门去了。萌槐端着早饭看着关山月出去,一直盯着他,酒宝拿着给关山月的早饭吃了一口:“别看了,走了。”吃着,走了出去。
关山月出了门,被早晨的风一吹,头还是很晕的。他想了想,去找了温玉,一进门就问他:“温玉,你有爹吗?”温玉被这个问题问的一愣,让他坐下,给倒了杯茶,还是回答了他:“有,又没有。”关山月喝了一口茶:“那怎么说。”温玉有些不自然,抻了一下袍子翘着二郎腿:“我有爹,但不是亲爹。”关山月看着他,眼神有些波动:“现在,咱们一样了。”温玉有些惊讶,但面不漏色,看着关山月,觉得他眼中像是一汪水在波动,不知道他怎么了:“王爷,你怎么了。”关山月抬头仰望了一会,又低头看着温玉:“我只是昨天知道了一个事实。”温玉看着他,他接着说:“丞相国师丁尚书和我爹,也就是关挫存在着某种联系,这就是丞相的棋局,好像我们和国师是一伙,但国师和丞相是一伙的。”温玉是彻底蒙了:“王爷,您到底想说什么。”“我昨天得知,我不是亲生的,而是许多年前作为一个条件和筹码,所以小时候丞相抓我杀我不是因为怕我当官,还有不为人知的事。”也只有温玉能听他说的胡话:“王爷,您是说父债子还?”关山月有些异常的郑重:“倒也不是,可能是他们原来把事压下,现在又事发了。”温玉到是微微一笑:“你这到是让我想到我来王府的目的。”关山月抓住温玉的手:“什么目的?”“报仇啊。”温玉平淡着说。关山月听到这笑了:“我想来想去都忘了,小时候你说过来的目的,被你那个不着调的师父叫来报仇的。”说着坐会椅子上笑了一下:“你说你都不知道仇人是谁,怎么报?又来到我王府......”说着自己想了想:“你师父是谁啊?”温玉看着前面,没看着他:“不知道。”关山月又笑了:“你师父是谁你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姓温,小时候隐约好像是买豆腐的。”温玉面无表情的说,但是关山月能看出他已经很努力在想了。关山月看着他:“你一直以为他是你爹?”温玉放下退换了个姿势做好:“不,我知道他不是我爹,我小时候好像还有名字,但是记不清了。”关山月凝重的看着他,温玉一笑:“王爷,你是来调查我的?”关山月一笑:“好奇,多问了一句。”温玉转过头看着他:“王爷和大将军是怎么回事?”关山月叹了口气:“他不是我爹。”温玉看着他:“说清楚点。”关山月把丞相说的话跟温玉说了一遍,温玉觉得很不可思议,关山月决定,先从查清这个事入手,他又预感,这个自己爹的问题查清,其他丞相国师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关山月还在温玉府上的时候,就有人找他入宫了,皇上要召见关山月和温玉。二人来到了皇宫,皇上说的话让他们很奇怪,皇上让他们去绍兴查案子。关山月问皇上:“皇上,有县衙,有府衙,京城有大理寺,朝中有文武百官,怎么就叫我去......”说着走到了温玉的另一边:“去去去查案?”皇上笑笑:“我是叫温统领查案,你陪同他查案。”关山月欲言又止,温玉跪下接旨。皇上给他一份卷宗:“温统领好好看看。”温玉拿起卷宗看,皇上站起来:“对了,关山月啊,你说我要不要给你挂个官职。”说着走到他面前。关山月看着皇上一笑:“皇上,臣有官职,您封的,南平王。”皇上看着他:“我是封了你南平王,可是你这个王在京城能保你衣食无忧,到外边可能就性命不保了。”皇上走了两步又笑笑:“要不,朕封你个捕快?”关山月笑着,然后收住了笑容:“皇上让我从一个一品的王去做一个没品的吏?”“你是在质疑朕吗?”“那臣不敢,臣接旨就是了。”关山月又笑了起来。皇上看着他:“朕又不是免了你的王,我只是在王的基础上给你加了个官,你现在是一品多。”关山月五官都绕道一起了,又做出一副微笑的样子跪下谢恩。一旁的温玉说话了:“皇上,让我去绍兴查一起贪污案?”皇上走回到桌案后坐下:“这起贪污案关系到前户部尚书丁大人,让你们去查不行吗?”关山月一听:“可以,当然可以,皇上,就我们两个?”说着看看温玉。“听说温统领读了万卷书,也该行万里路了。”皇上写着什么东西。“皇上说的极是。”温玉附和到。“你们到了绍兴,不要惊动知县,知府死了,你们去吊吊丧。”关山月刚要说什么,皇上又说:“你们去,我跟文武说让你们去绍兴看看风土人情,朕也想去看看,其他的就不要多说了。”皇上说完就走了,走的时候说:“明天就走吧。”温玉和关山月互相看了一眼,离开了殿内。
出了皇宫,关山月拉着温玉去面摊吃午饭,他没吃早饭饿坏了,要了两碗面。二人坐下,关山月拿出一双筷子递给温玉:“温大人,哦不温统领,我请。”关山月又拿了双筷子,擦干筷子上的水,老板端来了面,关山月笑着,把自己面前的面和温玉面前的面掉了个个,温玉一看,笑了一下:“王爷,您的俸禄不少吧。”关山月笑笑:“省吃俭用嘛。”温玉一笑:“王爷,请。”关山月狼吞虎咽的吃起面条,温玉不紧不慢的擦干了筷子上的水,不急不慢的夹起来吃。关山月夹起一片牛肉放到温玉的碗里,嘴里含糊不清的说:“给你一片。”温玉看着他,又夹了回去:“王爷吃吧。”关山月真客气,夹起温玉夹回来的肉放到嘴里:“不吃浪费了。”温玉站起来:“王爷您慢慢吃,我还要回去再看看卷宗,收拾收拾东西。”关山月端过温玉的面:“都没吃完,浪费。”说着把他那碗吃了两口,心里想着皇上为什么偏偏在自己刚找到方向时,把自己调到绍兴,他觉得绝对不是偶然。想着,面也吃完了,两碗面,吃的很饱,他放下银子,溜溜达达的走,还想着这事。明天出发,时间很紧,他回到府里,通知了大家。吉隩曹彰听说要去绍兴,很高兴,有望一无既往的面无表情,不过他心里琢磨着这件事。关山月查到的所有事,他联想到的所有事都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包括温玉都不知道他到底知道多少,当然,他也不知道温玉知道多少。吉隩曹彰高高兴兴的收拾东西,突然发现,丁一不见了,丁一的烧还没完全退,所有人满城疯了似的找他,找到了半夜,依旧没找到,因为他们不知道,丁一就在关山月府里膳房的水缸里。凌晨的天又下起了小雨,关山月他们在雨中奔波,而丁一半身泡在水里,在阴暗的水缸里偷偷的掉眼泪,他也许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
天亮了,他们要坐船从京城到绍兴,雨停了,温玉拄着把伞在码头等他们,看到的是关山月领着吉隩曹彰有望浑身是水,满脸雨水的奔来,气喘吁吁的来到温玉面前,温玉一眯眼睛一歪头:“你们......”关山月叉着腰喘气:“丁一,丁一这小子,不知道跑哪去了......”温玉看着他:“王爷,找到了吗?”关山月还是喘着气,不过把气喘匀了点:“要是找到了,还能这样吗?”温玉略歪着头又打量了打量他们:“走吧,上船。”几个人上了船,来到了各自的船舱,关山月他们换了身干衣服,关山月去找温玉,吉隩曹彰想着要回家,就去找最能说话的关山月,有望跟着他们,都来到了温玉的房内,温玉正坐着看卷宗,他们来了,也就顺便讲一下案子的内容,主要就是绍兴闹灾,户部丁大人拨了五千万担粮食和十万两银子赈灾,如今粮食是掺了沙子的,银子更是不翼而飞。丁大人死了,银子也不在丁大人那,都不在京城,皇上让他们到绍兴看看,也是有缘由的,而且听说知府大人死了,皇上派个朝中的人去慰问,显得君王仁慈么。温玉滔滔不绝的讲着案子,关山月认认真真的听了,还时不时的提出疑问,吉隩小声对曹彰说:“成林哥哥,你有没有觉得,温玉像是王爷,小王爷像个仆人。”曹彰看着吉隩:“别瞎说,要杀头的。”关山月听的认真,因为这次的事真的刺到了他的心,他甚至有些恐惧,虽然他没有什么害怕的。关山月打发了吉隩他们,和温玉单独说事,吉隩和曹彰出去之后,自然趴在门口偷听,酒宝和萌槐,站在墙外的假窗户,使劲往里看,有望一个人回房间了。关山月当然知道有人偷听,一边说着:“温统领,我们到了绍兴去哪啊。”一边悄悄走向门口,吉隩曹彰从小练内功,耳力并没有多好,关山月极轻,二人没发现,酒宝发现了,拉着萌槐到旁边的死角里。关山月用意识命令温玉打开门,温玉只好照办,门是朝里开的,他伸出手想拉门,关山月向前了一步,温玉只好也向前了一步,拉开了门,吉隩和曹彰摔了进来,温玉要后退,可关山月站在后边,脑子里反应了一下下,吉隩已经扑了过来,温玉用手一扶她,她跌到了他的怀里,他急忙把她推开,扶稳了,直接从门出去了。关山月用扇子点住扑来的曹彰,吉隩看着关山月,用眼神瞟了一下温玉,关山月做出了一个很无奈的表情,好像是说:你得罪了温玉,我也没办法。温玉突然又进来了,把吉隩曹彰推了出去,又给关山月施了个礼,连请带推的弄了出去,把门关上。关山月捂着嘴笑,冲着门缝喊了一声:“温统领,记错房间会很尴尬的。”
吉隩的目光很快被船的一层跑动的人所吸引,好像是有贼。吉隩快速的跑下去,随着他们一起抓一个人,吉隩会武,很快追上了,没想到那人是个练家,和吉隩对了几招。吉隩的内功很深,但是使不出来,因为骷髅神功是没有能好好贯穿内力的外功的,所以打了几招渐渐处于下风,打都的过程中,吉隩发现了那人手中有火药,那人把火药攥在手里,拔出了长剑,吉隩没有兵器,剑架在了脖子上,曹彰不敢上前,吉隩手背在后边,这在找毒药,她会随身携带的。突然,从二楼正对面飞下一人,一脚踹开了门,正踹到那人的后腰,那人倒下,吉隩也在同时洒出了一些黄色粉末。飞下之人,正是温玉,他算是被关山月挑唆下去的,关山月这拿着扇子扇着,笑着,往下看着。温玉把那人踢倒,又飞身上去,走回自己的房间,进去把门关好。吉隩从楼下跑上去,看着笑着的关山月:“小王爷,你就看我笑话。”关山月依旧在笑。“还笑!”吉隩有些不高兴了。关山月走了两步,合上扇子敲了两下温玉房的门:“隩儿,还不谢谢你的大恩人。”吉隩十分不耐烦的趴在门口说了句:“我谢谢你啊。”说完走了,关山月推门要进来,温玉说了句:“王爷您受累,快回房歇息吧。”关山月说了句:“无趣。”也就走了。
温玉在房里坐在,想着绍兴,大家都不知道的是,温玉的老家也是绍兴。他自然想到自己家的林口县,但是林口县离省城远,他正想着如何回去,还是不露声色的把王爷他们骗过去,想着想着,他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师父,他不得不承认,他的确想师父了,虽然已经十多年没见了,都快忘了师父长什么样子了,但是他还是想师父了,他还有问题想问师父,他师父当上在他十四岁时把他送进王府,告诉他要报仇,杀母夺父之仇,这个仇,他已经报了。他记得,所有人都管他师父叫温头,是个卖豆腐的,当时送温玉进京时,对他说的话他现在还一字不差的记着,师父说他娘被人陷害,又被他爹误会致死,他差一点命丧贱人之手,而被他救下,这个仇人,就是关山月的生母,温玉到王府的目的,就是诛杀关山月的母亲。而关山月的母亲,其实也不是郁郁而终,是被温玉杀得,这谁都不知道。他住进王府,本是为了监视关山月,后来,自己却意识渐渐模糊了。他甚至都有些忘了自己来的真正目的,他觉得关山月已经知道了什么,他要去问问自己师父。吉隩拉着曹彰去关山月那磨,求着说着让关山月去林口县,因为他们的师父,他们的茶叶铺也在林口。关山月让曹彰留下,让吉隩去问温玉。
行着船,又下起了雨。雨水拍打着船板,还有些惊雷,天阴下来了。温玉在房里,在船上,蹲在床上,裹着被子,还有些发抖,他没病,就是怕打雷,从小就怕,长大些更怕,因为在他十四岁杀关山月生母的时候,正是一个惊雷雨天,滚滚的雷声震响在耳边,一道闪电划过那女人满是血的脸,以至于每次打雷的大雨天,都想到杀人的情景。他刚才在想这事,突然打雷,船也有些摇晃,心里莫名的恐惧油然而生,而且愈加的强烈。吉隩找温玉,也没敲门,直接进来了,看到了温玉这样,他先是一愣,随后笑了起来:“温大人,原来堂堂的温统领还和小孩子一样怕打雷?”她嘲笑着温玉,温玉都不敢抬头,打闪的白光照在吉隩的脸上,这让温玉更害怕了。吉隩打趣着温玉,说了几句话看出温玉是真害怕,倒了杯茶:“温大人,你真害怕。”温玉喘了口气,平复了一下心情,他有点后悔坐这艘好船,带窗户的好船。吉隩把茶递给他:“老天要打雷下雨你管不了,就让它下去吧。”温玉喝了口热茶,用内功护体:“我没事,你出去吧。”吉隩给自己倒了杯茶:“温大人,我找你来是有事问你。”温玉好像缓过来点了:“你没敲门。”吉隩一撇嘴,走到门口,敲了两下:“好了吧。”温玉坐在床上:“什么事?”又打了个霹雷一道闪,温玉一哆嗦。吉隩坐过去:“到绍兴咱们去林口呗。”温玉一愣:“你去问王爷。”“王爷说问你。”吉隩看着他。温玉自然答应,吉隩很是高兴。临走前多问了句:“你怕打雷?”温玉坐在床上:“没有,我......”有一道闪,带着雷声,温玉颤了一下。“还说你不怕。”吉隩笑着,站起来,找了块布,把窗户堵上了:“堵上就看不见打闪了。”温玉看着,又打了声雷,还说一颤,用了内力。“温大人,最好别浪费内力。”温玉看着吉隩出门的背影,莫名的笑了一下。
到了晚上了,在船上其实早晚差不多,雨停了,但是天却还打着干雷,天气真怪。吉隩和曹彰,聊着天在船板上吹风,看到了惊人的一幕,船被雷劈了。船被雷劈的接近断了,舱里的人都出来了,温玉出来,看着霹雷,更有些害怕了。关山月知道他这个毛病,紧挨着他站着。船被雷劈了,这可是大事,船员都去紧急修补船去了,后来乘船的其他商人,都不得不去帮忙,因为雷劈到了火药上,着了。就是偷东西的那个人的火药,他贩的烟花火药,着了。吉隩他们帮着灭火,船着了,船底又露水了,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吉隩曾经给那人撒过黄色粉末,是“毒息散”,遇上灼烧会散发毒气,吉隩又急忙每个人发解药,忙的手忙脚乱。更让人手忙脚乱的是,船触礁了,掌舵的人莫名的晕了,没人掌舵,乱撞了下去。船上的商人还在担心他们的金银细软,萌槐直接把其中一人的丝绸,全部扔到了水里,那人扑过来要打萌槐,萌槐一只手制住他,另一只手又扔了些东西。吉隩都奇怪:这么短的路程为什么还遭遇船只失事。曹彰也跟着往下扔东西打架,直到水已经没过脚踝,没过膝盖,才舍得丢些东西下去,有些人为了逃命,跳船游着逃走。关山月一下跳到了水里,吉隩没来得及喊他他已经跳了下去,下去抓着一个人飞身上来:“就是他,捅漏了船板。”那人突然伸手,和关山月打了起来,那人武功还不错,二人打了起来,随后又飞出十多个人,和他们打了起来。
温玉独身一人,来到舵房掌着舵,他用内力拉,尽力控制,还是拉不住,关山月也来帮忙,一边掌舵,一边打着那些蒙面的黑衣人。随后又来了一拨穿着夜行衣的人,和那伙黑衣人打在一起,温玉看着,好像是一拨冲着自己来的,另一波好像是保着自己又刺杀王爷。他们在舵房打着,船舵还是控制不住了,温玉和关山月边打边退出了舵房,看到外边的商人死了一片。酒宝拿着一根绳子,绑在自己身上,又递了一根给萌槐,二人绑着自己,扒着船绑往下一点点的爬,因为如果是故意弄破船,肯定有逃走的小船。萌槐跳到了水里,游到了船底,从船底的暗格上去,真的有一直小船。他叫酒宝来帮忙,偶然发现酒宝是个旱鸭子,萌槐笑了两句,一个人把船拖到了水里。酒宝顺着绳子爬上去,萌槐弄好了船,发现自己的手被船上的刺扎破了,把破了一个小血珠的手指放到嘴中舔了舔。温玉和关山月不想恋战,可那群人缠着他们,纠缠不放。船已经半沉入水,吉隩在水里朝着关山月他们游了过去,曹彰跟着吉隩,也游了过去。
那两伙黑衣人招招狠毒,招招毙命,又互相打来打去,吉隩和曹彰帮着关山月和温玉打,水已经到腰了,一伙人在水里扔了两瓶粉末,吉隩会用毒,知道是毒药,自己也把剩下的毒息散撒了出去,没想到那伙人竟然自尽了,另一伙人中毒也死了。四个人用轻功,飞到了小船上,萌槐掌着小船,向岸边游去,他觉得那边应该是岸。船行着行,突然船底楼了,吉隩坐到了那个漏洞上,没想到又漏了个洞,曹彰坐了上去,还是堵不住水,船底已经有一层薄薄的水。萌槐的神色有些异常,酒宝问他:“怎么了?”“没事,我只是觉得,这事蹊跷。”酒宝也没太注意:“是蹊跷,小船上的漏洞,是用土封上的,一过水,就漏了。”关山月说看看温玉:“看来,黑衣人没想过走啊。”温玉却一笑:“中计了,却不得不中。”说着,跳下了船,关山月也跳下了船,吉隩曹彰全部跳下去。萌槐拉着酒宝跳下来,拽着酒宝向关山月游去。没想到的是,水里竟然还有埋伏好的水贼。
吉隩和一人打着,她的内力在水里完全使不出来,曹彰这几天练得外功够自保,他游过去,想帮吉隩。吉隩就仗着水性好,可还是处于下风,不过,那伙人是冲着温玉来的。对方有剑,吉隩被刺破了胳膊,鲜红的血和水融合了,曹彰看着,急忙赶了过来,可又有两个人围了过来,吉隩用手捂着胳膊,感觉脚下又一股力量,她被人拽下了水里,她会水,憋着气,可那人抓着他不放,她也有些憋不住气了,用劲踹着,可是挣不脱,渐渐意识有些模糊了,眼睛也闭上了。她突然感觉有人推他,随后感觉抓着脚的力量不在了,随后有人晃她,她微微睁开了点眼,看到了温玉的脸,随后感觉眼睛一凉,又闭上了。随后脸朝上向下落去,温玉又下去捞起她,尽力向上游去,游到水面发现,周围竟一个人都没有,他们在水下,不知道顺着水漂了多远。他看着吉隩,昏过去了,拍了拍,还是没醒,对于救不救她,他还是有些犹豫的,毕竟和她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的,但是,还是救她了。温玉给吉隩渡气,用内力渡她,本应该口对口,温玉内心不肯,但看到吉隩危在旦夕,之后硬着头皮,撕了块衣服隔着,给他渡气,渡到一半,内力竟然消损的甚快,他如若停止,二人姓名都不保,只得硬挺着继续渡。吉隩的骷髅神功是至纯的真气,不可又一丝外气,人没醒,但内力相冲,以至经脉血流加速,一口血喷出,喷到温玉嘴里,温玉继续渡气,吉隩就可能走火入魔,不渡自己就内力受损。他立刻停止渡气,毕竟人命关天,他也吐了口血,内力过耗,有些迷糊。当二人醒来时,是在岸边,已经是早上了。吉隩先醒的,发现自己躺在温玉的身上,赶紧站了起来,站起来后吐了口血,蹲下晃了晃温玉,温玉没醒,吉隩一摸脉搏,没事,她立即打坐,平复内力。温玉也醒了,坐起来吐了口血,看见了吉隩,也打坐调息起来。
二人都调息完毕,站起来,才发现温玉的小腿伤了,温玉自己都不知道。吉隩蹲下,给温玉上药,温玉直勾勾的看着吉隩,吉隩扯下衣襟,给包扎了一下。温玉看着吉隩,吉隩看了一眼温玉:“你盯着我干嘛?”温玉啊了一下:“哦,没事,你的胳膊好点了吗?”吉隩一笑:“呦,温大人怎么也知道关心人了?”温玉站起来,腿一疼,咽了口唾沫,不说话了,向前走去,虽然不至于一瘸一拐,但是也很不自然。吉隩跟上去:“温大人,我问个问题,行不行。”温玉背着手,微微有些仰头的往前走:“问。”“温大人,你说你什么时候不装啊?”“我什么时候装了?”温玉有些不屑。“就拿现在说吧,你腿伤了,非要装出一副无事的模样。”温玉走的快些了:“我本就无事。”吉隩追了上去:“好好好,随你吧,走慢点。”温玉好像走的刚快了:“我是武官,烦劳吉姑娘叫我统领。”吉隩一脸看不起的感觉:“武官叫大人的也有,你怎么就这么特殊。”“我不够大人。”吉隩笑笑:“原来是官太小。”温玉一撇嘴:“让你叫你就叫,那那么多废话。”“好好好,温统领你厉害。”吉隩走到前面去,二人走上官道,顺着走下去,温玉还有些钱,但是有些不愿给吉隩花,买了两匹马,一好一坏,骑马去绍兴,一路打听关山月的下落。
到了晚上,吉隩的马已经不行了,二人找到一间无人居住的旧房,温玉让吉隩打扫一下,吉隩自然不肯,做到了椅子上。温玉把吉隩拎起来,自己做到椅子上,又翘起二郎腿。吉隩很是生气:“我说温玉,我也是江湖有门有派的人物,你......”温玉一只手拖着脑袋:“我要睡一会,出去吧。”吉隩说着伸出手要打他:“你......”温玉闭上了眼,吉隩收住了手,又对着温玉一呲牙,吐了吐舌头,走了,温玉睁开眼看了一眼,微微一笑,又闭上眼了。吉隩饿了,到后边的树林里打了一只野雉,回来的路上,险些迷了路,后来有些什么声音,跟着就走出来树林,拎着野雉到了膳房。温玉用手掐着人中,睁眼看着吉隩。膳房里落了很厚的灰,吉隩生起了火,烟囱被堵,屋里很快浓烟密布,呛的吉隩满脸是灰跑了出来,咳着喘着气,温玉换了个姿势,看着吉隩。吉隩在外边,不知从哪找来一把烂蒲扇,扇着看着膳房里。过了一会,吉隩把烤好的雉鷄拿到屋里,温玉看着,表皮焦黑,散发着糊味。吉隩撕下一个鸡腿,看见了看着他的温玉:“温统领,给。”把鸡腿塞给温玉,作作的说:“感谢温统领一路的银子。”温玉一笑,接过鸡腿看了看:“你这能吃吗?”吉隩看着他:“什么叫能吃吗?”说着扯下另一个鸡腿,咬了一口,嚼了嚼,立马吐了出来。温玉一笑,站起来把糊鸡腿塞还给他,走出去了,一会儿又进来,扔给吉隩一个果子:“给。”吉隩接过果子,瞪着他,咬了一口,哼了一声,出去了。第二天,吉隩的马死了,温玉极不情愿的把吉隩搭跨在马背上,一路向绍兴狂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