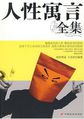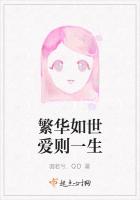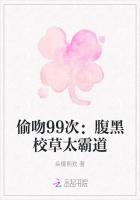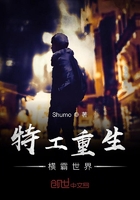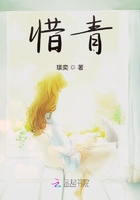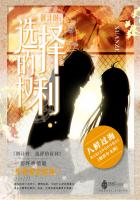孙犁(1913~年)作家。河北安平人。建国后,任天津作协副主席、《天津日报》总编辑。有《孙犁文集》。
孙犁是作家,对图书近乎痴迷地爱好,他潜心收藏、阅读,对版本的钻研具有颇深的造诣。他广泛涉猎,远离尘世纷争,取精用宏的解读作品的方式,将读书比作游览,“宁可到有实无名之区,不遑去有名无实之地”(《风烛庵文学杂记》),都显示了其个人的审美趣味、学识和爱好,表现了一个作家对其所处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真实的理解和探求。
孙犁是藏书家,是深谙书之三昧的读书人。
他戏称收藏的是“百衲本二十四史”
孙犁是1949年初到天津的,当时他发现旧书摊书店很多,书籍品种丰富,而且很便宜。由于刚解放,物品比较短缺,大家更注重添置一些生活物品,没有多余的钱买书,且对书感兴趣的人也不多。一部白纸的《四部丛刊》连箱带套才一二百元,多种“二十四史”也没人买,有的就堆在墙子河边的街道上,经受风吹日晒。也有不少大部丛书被拆散后流落到旧纸店去。孙犁当时虽十分拮据,无钱他顾,但由于年幼起就养成的爱书的习惯,使他不能不为之所动。开始他只能在小书摊上买一两本旧书,后来有了一些稿费,才敢于购置一些成套的书。他的“二十四史”,就是东拼西凑积累起来的,他戏称是“百衲本二十四史”。
孙犁藏书,很重视书目书,他说:“要购买一些古籍,书目是不可缺少的,虽不能说是指路明灯,总可以增加一点学识,助长一些兴趣。”解放初期,他按照鲁迅开给许世英的书目,先买了一部木刻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后来又买了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本《四库全书总目》,他对这套书评价很好,认为它们“无论从版式、印刷、纸张、装订上讲,都是既实用,又方便,很好的古籍读本。”此外,他还配置了禁毁书目。
孙犁认为,《四库全书总目》虽然学术价值很大,但并不是购置旧书的门径书。因为它所收集的版本,现在多数已无从寻觅。在指导购书方面,他比较推崇的是《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它的好处是在各书的后面,都注明近代的版本。另外,孙犁也很喜欢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觉得它具备《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的优点,而比之更简明。
孙犁还收藏有清末琉璃厂书肆编印的《书目汇刻》。据此,可以略知当时各省书局所印的书。它还附有上海制造局所印的一些地理、数学、机械、化学方面的书籍目录,反映了当时崇尚新学的特点。
孙犁的许多藏书,包括许多书目书,都在十年浩劫中散失了。到发还时,他开列了一张遗失书籍清单,其中大多是古旧书,近百册,令人不得不惊诧“他平时记忆力那么糟”,却对他的这些破旧书籍记得如此清楚。
阅读史书的兴趣,像顺藤摸瓜
孙犁在青年时并不喜好史书,在学校读书时主要阅读一些抽象的哲学、美学,或新的政治、经济学说,也读了不少文艺作品。购买和阅读古书是从解放以后开始的。他阅读和购买史书的兴趣,像顺藤摸瓜一样。例如,他先买来一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仔细阅读后知道还有一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就又买了来,但因部头太大,只读了一部分。又如,他买了一部《贞观政要》,对唐太宗贞观之治和初唐的历史发生了兴趣,就又买了《大唐创业起居注》、《隋唐嘉话》、《唐摭言》、《唐鉴》、《唐会要》等书。他从《贞观政要》中知道了魏征,就买了魏征辑录的《群书治要》。孙犁说“买书就像蔓草生长一样,不知串到哪里去。它能使四部沟通,文史交互。涉猎越来越广,知识越来越增加,是一种收获,也是一种喜悦。”
由于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孙犁的阅读倾向也发生了变化,到后来,他对文艺书籍的虚无缥缈、缠绵悱恻,已不感兴趣;对于翻译过来的哲学、理论书籍因句子太长,修辞和逻辑复杂,也不多看,主要是阅读史书和笔记小说。从阅读一些与文史有关的《武林旧事》、《东京梦华录》、《梦梁录》等发展到阅读名为地理而实为文学名著的《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由纲领性的历史书如《稽古录》、《纲鉴易知录》,进而读《资治通鉴》、《十六国春秋》、《十国春秋》等。
孙犁与一般藏书家或某一领域专家的藏书不同,并非只收某类书籍而极少旁及其他。文史经哲、农林畜牧、金石考古、书法美术等等,各种门类的书籍,他都广泛搜集,涉猎研读。
孙犁被抄家的书籍于1973年得到了部分归还,第二年春天,他搬回天津多伦道旧居,书籍也随之搬回。当时搬家是由报社文艺组的同事帮忙的,后来文艺组的同事们打扑克,谁要是牌运不佳,就会说一句:“孙犁搬家,总是书(输)。”由此可见孙犁藏书之富。
收藏与阅读,为深化对社会人生的理解
在各种门类的书籍中,孙犁的收藏与阅读,偏重于传统典籍一路。这并非因为他沉湎故纸,厚古薄今,而是想通过阅读这类典籍,以历史经验为借鉴,加深对现实社会人生的理解。
孙犁的一生,是与书籍相伴的一生,他在工作之余,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阅读上面。且不说他进城以后,特别是从50年代中期开始,通过多种渠道购买大批书籍,孜孜不倦地整理和阅读;也不说在晚年,他的读书兴致之高和阅读量的惊人;就是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也不会忘记在书包中装上一两本书,一有空,无论是沙滩溪边或山崖路旁,都要读上几段。在行军时,身上有两样东西是少不了的:一是手里的一根棍子,一是用破裤子缝成的书包。鲁迅的《呐喊》、《彷徨》等是他随身携带的书籍。
孙犁在河北安国县读高小的时候,当时那所学校的设备已较为完善,有图书馆和阅览室。他就是在这个阅览室里开始接触“五四”前后出现的各种新期刊和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的著作,这使孙犁有机会在小学时代就受到了“五四”进步思潮的启蒙教育。后来他又广泛阅读左翼作家和苏联作家的小说,同时也读了大量文化史和文字语言方面的书,以及哲学书和古典文学。在此期间,报纸和杂志都是他的涉猎对象,读得多了,竟能够辨别出《申报》副刊上鲁迅的化名文章。
高中毕业后,他曾在北京工作,单位的后门,正好对着北平图书馆,他一有空就去那儿看书,也常去北新桥、西单商场、西四牌楼、宣武门外等处逛旧书摊。每日下班后逐摊浏览,总要买一两本书回寓所夜读。
1936年春,孙犁失业,在家闲不住,每天手不释卷或读或写。没有书柜书桌,妻子的衣柜就变成了他的书柜书桌;没有安静的环境,场院里树荫下就是他自得其乐的读书环境。在外面订报养成了习惯,在偏僻的家乡,他也很想订份报纸,这在当时,已超出了家庭的承受能力,他的父亲和妻子拗不过他,成全了他。那年夏天雨水多,他们结婚时裱糊过的屋子,顶棚和墙上的壁纸都已脱落,有些人家,到集市上去买旧报纸糊墙,妻子就和他商量,是不是拿他那些报纸也把屋子糊一下,孙犁同意了。于是,“妻刷浆糊我糊墙。我把报纸按日期排列起来,把有社论和副刊的一面,糊在外面,把广告部分糊在顶棚上。这样,在天气晴朗,或是下雨刮风不能出门的日子里,我就可以脱去鞋子,上到炕上,或仰或卧,或立或坐,重新阅读我所喜爱的文章了。”(《报纸的故事》)这段生活经历,后来写进了他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
孙犁对书籍的洁癖是很出名的。每得一本新书,他都要用废旧信封纸加以包装,见到哪本书破损了,他就补补贴贴,修理完好,哪本书书口有了灰尘,他就用小块细砂纸打磨,拂拭干净;如果外借的书弄脏了,他是宁愿送人,也不收回了。他老伴曾用“轻拿轻放,拿拿放放”八个字,形容他爱书的情状。
孙犁著有“读书记”、“读作品记”、“序跋”等书话类型的作品,他的《耕堂杂录》、《书林秋草》、《耕堂序跋》、《耕堂读书记》四个集子选录了其中大部分。这些作品真实地记录了他的书之情、书之梦、书之缘、书之趣和他晚年的读书轨迹:70年代他多读古代的文史杂著;80年代以后,增加了许多当代的文学品;到了90年代则对清人别集、稗史野乘、碑帖画印、泉话镜谱等多有涉及。他曾作《书箴》以记其志:
“学泊晚年,无竞无争。抱残守阙,以安以宁。唯对于书,不能忘情。我之于书,爱护备至:污者净之,折者平之,阅前沐手,阅后安置。温公惜书,不过如斯。”
“勿作书蠹,勿为书痴,勿拘泥之,勿尽信之。天道多变,有阴有晴。登山涉水,遇雨遇风。物有聚散,时损时增。不以为累,是高水平。”
孙犁的晚年生活,不仅把读书当作解读人生、涉猎学问的最佳途径,而且当作一种精神寄托和修身养性的高雅消闲。70年代初,孙犁刚获“解放”,尚未恢复到以往的创作境地,便以这种方式“消磨时日,排遣积郁。”他利用废旧纸张一一包装发还的旧书,然后题书名、作者、卷数在书皮上面。遇有感触,便写上一段即兴式的文字。这类写作活动,在“文革”后持续多年,后来略加整理,汇集发表,他名之为《书衣文录》。
林象平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