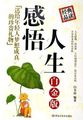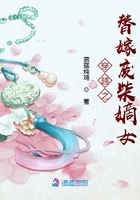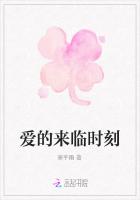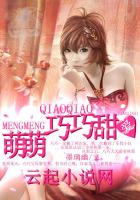施蛰存(1905~年)古典文学专家、文学翻译家。上海松江人。建国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1957年后,转向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研究。有《吴越金石志》、《金石百咏》。
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文坛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可谓多矣;但这些人物中,能够挺过后来一连串的风风雨雨,并在桑榆之年老骥伏枥,笔耕不辍,依旧堪为文坛或学界之翘楚,且最终走向新千年、新世纪的,则实在是寥寥无几。施蛰存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施蛰存,一生从事文学创作、办刊、翻译、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等工作,历任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教授,是一位“通才”型文化人。施蛰存一生与书相伴,人生的每一步都投下书的影子,其读书治学之经历与方法无疑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我是读书人。我的职业要我读书,
我的业余工作也要我读书。”
施蛰存一生读过多少书?这是一道算不出结果的加法题。从父亲给六岁的他举行开蒙仪式那年(1910年)算起,施蛰存读书的历史长达近一个世纪。读书,成了他生活乃至生命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一篇题为《为书叹息》的文章里,他说:“我是读书人。我的职业要我读书,我的业余工作也要我读书。”这无疑是他为自己的读书生涯所做的最朴实而又最确切的总结。
施蛰存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父亲也爱读书,家里的藏书就有十二箱,经史子集都有。所以他说,他的中文是家学。如果说,隔壁私塾里的徐老夫子是他的启蒙老师,那么,父亲的十二只书箱应该是第二个老师。正是这两个老师,激发了童年施蛰存对读书的浓厚兴趣。七、八岁的他已经开始跑到外面的书摊和书肆里买书了。在《我的第一本书》一文里,八十高龄的施蛰存回忆道:我买的第一部小说就是金圣叹批本七十回的《水浒传》;第一本古典戏剧书是《蕉帕记》;郭沫若的《女神》是我买的第一部新诗集。《少年维特之烦恼》是我买的第一部新文学出版物的外国小说。五彩斑斓的文学世界使施蛰存流连忘返。进入中学后,施蛰存更加勤奋地在书海中遨游,并且萌生了搞文学、当作家的念头。
由读书到买书、再到走文学道路、自己写书,这本是一条分外艰辛的路,可对施蛰存来说,这条路似乎走得特别自然,特别顺畅;也许,除了兴趣、天分之外,还有一种非由人定的机缘吧。历史往前推进时,似乎充满了这样那样的偶然性,可回过头看去,又会发现,过程与结果之间,有着一条若有若无而又明灭可见的发展之链、必然之链。从小就爱读书的人,未必都能成为大师,但最终成为大师的,却往往是那些从小就被书籍和知识“俘虏”了的人。
“乱翻书”的作家与“见异思迁”的学者
在读书方面,施蛰存的兴趣相当广泛,举凡古今中外关于文学之名著,只要有可能,无不找来一看。上大学他先是学英文专业,于是“钻进了英国文学”,一年之间就通读了英国文学史和大部分英国散文与诗歌。后来,转学至上海大学念中文系,在陈望道、沈雁冰、俞平伯、田汉等老师的影响下,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阅读,并开始了初步的研究。四年级时,又相继转到大同大学和震旦大学读英文和法文,在叶上之、胡宪生等老师的指导下,继续阅读欧洲文学。在读书方面,施蛰存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好胃口”,从不挑肥拣瘦,更不会因噎废食。1928年到1937年,施蛰存在上海做“亭子问作家”,正式走上了文学道路。这十年,他的“职业是书局编辑,业余工作是写小说,翻译外国文学。”除了阅读苏联、东欧和美国的文学作品,还“热衷于明人小品,把公安、竟陵派的几十部诗文集看了一遍。”
在《我治什么“学”》一文里,施蛰存谦虚地说自己“读书没有计划,得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对于法国诗歌,也只是“似懂非懂地乱读了一阵”。事实上,这种“没有计划”的“乱读”,对于学术研究也许是不合宜的,却正是作家的必修课。这种读书状态,使他“知识面广了,眼界开了”,创作灵感纷纭而至,源源不断。短短十年间,施蛰存先后写作和出版了近十种小说集,还有数量不菲的翻译作品,被后来研究现代文学的人,称为“新感觉派主要作家”、“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者”。在总结创作经验时,施蛰存说:“在我写小说的时期,古典文学对我实在没有影响。”但读古代的作品,却对“学习语言文字”、“提高文学写作的基本功”,大有裨益。
“乱翻书”为施蛰存提供了创作的充足营养,却不能在研究工作中大显身手。从30年代末开始,施蛰存的小说创作就自动终止,开始了辗转十多所大学的教书生涯。在教学过程中,他发现,“光是读书,纵然读得很多,全不顶事。”要解答学生的问题,就得深入研究。于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相长”、学以致教的读书治学生活开始了。值得注意的是,施蛰存的治学也是“跟着兴趣走”,因而除了涉猎广,还具有钻研深、见性情的个人特色。随着教学工作的变动,他先后钻研过云南古代文献、敦煌变文、史传、宋人笔记及词话、唐诗宋词和金石碑版,其间还翻译了近二百万字的东欧、北欧及苏联小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的研究著作,深入浅出,娓娓道来,一反时下流行的“八股”做法,显得亲切自然,引人入胜。
在谈到读书与治学的关系时,施蛰存说:“任何人不会一上手就研究一门学问,必须有一个逐渐走向研究工作的过程。这个过程,我把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浅尝到博览。对某一门学问开始感到兴趣,渐渐地一本一本找这方面的书看,熟悉了关于这一门学问的各方面情况,这是第一个阶段。……在更广泛的阅读与思考之际,必然会发生问题。碰上了问题,就要自己去解决,这才走上了第二阶段,可以称之为‘入门’。入门之后,你会觉得欲罢不能,索性把一切弄不清楚的问题弄弄清楚。于是不能不展开更深入、更广泛的探索,这样才到达第三个阶段,开始做研究工作了。”这一段话真是读书做学问的经验之谈,凝结着施蛰存一生的求索与智慧。
施蛰存还自称自己做学问是“见异思迁”,并勉励青年学者要“一步一步地走完治学的全程”。其实,施老的“见异思迁”,未尝不昭示着这样一个道理:没有对研究对象的兴趣与热忱,随便找一个课题来做研究工作,是做不出真正的学问来的。对青少年来说,“朗读能巩固记忆”
在具体的读书过程中,施蛰存提出了三种读书法:朗读、背诵和“看书”(默读)。
和鲁迅一样,施蛰存幼年所受的也是“三味书屋”式的私塾教育。长期以来,这种教育模式一直被钉在“封建”、“刻板”、“戕害儿童心灵”的耻辱柱上。在中学语文课本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的寿镜吾老先生被“分析”为封建教育的迂腐代表,三味书屋也成了百草园的对立物,鲁迅对启蒙老师的追怀之情被一笔勾销。然而事实究竟如何呢?八十高龄的施蛰存在回忆自己“甫就小学”,接受这种“读背结合”的语文教育时,意味深长地说:“一本《千字文》,半年就读完而且背熟了。这就意味着我在初上学半年内就认识了一千个字,虽然不很懂得它们的意义,但也并不是毫无所知。现在小学一年级学生,恐怕识不到五百字。因此,我对旧社会中以‘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为小学生启蒙读本的办法,现在也不很反对了。”
何止是“不反对”?施蛰存还曾经说过,读书之乐,在于自己读书,为读书而读书。也正是这种读书之乐,培养了我一生乐读书的习惯,同时也为我后来能用细密的理性分析方法去读书打好了基础。因此他认为养成经常读书习惯、打好读书分析基础的最佳时期在于中学阶段,即十四五岁到二十岁这一段时期。在此期间,恳请中学语文教师,要做好对中学生课外阅读的指导工作。对中学生主要是要善于培养他们爱读书的习惯。后来,八十七岁的施蛰存在一篇题为《看书·读书》的杂文中,还以极大的热情向中小学语文教师“建议”:一、应当多多指导并带领学生朗读,朗读能巩固记忆。二、希望高中语文教师选一些文言文作补充教材,最好是议论文,也希望高中学生多看一些文言文的课外读物,以补充教材的不足。此外,在文字方面,还必须熟悉繁体字。鉴于当前在大、中学生普遍存在的“厚今薄古”现象,施蛰存的呼吁除了出于读书方法本身的考虑,还蕴涵着一个爱国学者勉力维护祖国文化血脉畅通不断的良苦用心。值得欣慰的是,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教育主管部门已经认识到现行语文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终于把增加文言文含量作为下一步教材改革的重要内容了。施蛰存的远见卓识得到了证实和回应。
“朗读”、“背诵”之外,施蛰存也主张“看书”,即默读。他说:如果你能理解“看书”是默读,“读书”是朗读,这才可以理解“看书”也是“读书”。“成年人读书不出声,只是对着书看,这是因为他们很容易通过语言文字获得知识。中学生必须朗读课文”;“过了中年,只能看书(默读)了。”这显然是说,青少年时期“朗读”“背诵”功夫练成了,“看书”的过程中,才能更好地进行“慎思明辨”并学有所成。再深一层推究,“朗读”、“背诵”开始得早,在“看”的过程中获益并爱上读书的时间就会大大提前。如今的中学生对大部头著作往往望而却步,其深层原因恐怕正在于此。
刘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