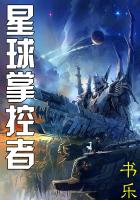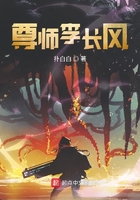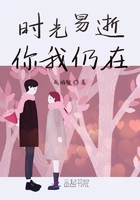夏丐尊(1886~1946年)教育家、编辑学家。浙江上虞人。留日。长期在中学任教。主编《中学生》、《一般》杂志。1926年始专任开明书店编辑所所长。著有《平屋杂文》。译作有《爱的教育》、《近代日本小说集》
夏丐尊从未在政府衙门任过一官半职,他一生从事中学国文教学和杂志编辑,是一位学者型作家。
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夏丐尊在杭州浙江省立师范学堂任国文教员,与鲁迅共事。“五四”运动时期,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与毛泽东共事,很受毛泽东的尊重。
夏丐尊虽然是个旧教育工作者,但他就教育谈读书,在青少年杂志上谈读书,对读书提出不少新的见解、新的方法。
“我最感到快悦的,是加盖自己的藏书钤记”
夏丐尊从小爱好读书。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二十年来,我生活费中至少有十分之一是消耗在书上的。我的房子里比较贵重的就是书。”早在辛亥革命后,他在做学校舍监时,很注意读一些有关道德修养和青年教育的论著,甚至还读了宋元明三朝的理学书籍。凡是有关教育学生的书,都设法取来认真阅读。这样他积累了很多的书,随着时光的延续,他的藏书越来越多。
夏丐尊有一个习惯,就是不喜欢向图书馆借书,而是喜欢买书、藏书。他采购的书籍类目极广,有宗教、艺术、生物、哲学,但最多的却是各国文学名著译本和中国古今诗文集。他购置图书只是讲究应用性强和阅读便利,因而并不在乎版本的稀罕和它的历史价值。在他的藏书室里,几乎找不到一部当时被藏书家视为善本的珍籍。
夏丐尊经常购书,天南海北,每到一处就逛各种书铺,寻找喜爱的书籍。他买到书后,首先就是加盖自己的藏书钤记。他说:这是“我最感到快悦的时候”。当这些书有条不紊地安放在固定的书架上时,夏丐尊就眯着眼观赏。后来他著文叙说此时此刻的欢愉心情:“我常自比为古时候的皇帝,而把插在架上的书,比诸列屋而居的宫女。”
有人喜欢买书,但买书的目的不同,有的是为了装潢门面,迎浪头赶时髦,跟着他人的感觉、评论走;也有的读书不求甚解,讲究趣味,浅尝辄止。这都属于盲目无计划地阅读,以至事倍功半,得益甚浅。夏丐尊喜欢读书,他从长期读书生涯里,养成适合自己有效的学习方法。他说:“读书的时候,常把我所认为要紧的处所标出,线装书大概用笔加圈,洋装书即用红铅笔画粗粗的线。”
当然,成功的读书还在于成功的用书。夏丐尊学以致用,读书所增进的知识就用来编辑和著译。1920年,夏丐尊得到日译本和英译本的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教育小说《Coure》(考莱)。他反复地读了多遍,边读边译,边译边读。后来他回忆说,我是掉了三个日夜的眼泪才读完它的。他将这部书取名为《爱的教育》。每翻译一节,由朱自清审读后在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上连载。在黑板报写几个字:是夏丐尊,不是夏丐尊
夏丐尊很重视学生读书。
他自1905年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先后在浙江师范、湖南第一师范等校讲授国文课。在教学中,他发现学生读书受到传统的读书观念影响,通常有两个误区:一是把读书视为高尚风雅的事情;二是把书作为接受文化的唯一载体。而此中还有一个通常被忽视而又不得不注意的事,那就是许多人读书不求甚解,以至读半边字音,读白字。
读书,首先还得识字,读字。
有一个故事:每当新学期开始,他走上讲台,就先在黑板上写几个字:“夏丐尊,不是夏丐尊!是教书先生,不是叫化子。”因为有些书报一而再、再而三将其名字误刊为“丐尊”。
读准了字,就可以多读些课外书了。
1943年,在上海沦陷区,五十八岁的夏丐尊为求温饱和生存,应聘屈就在私立南屏女中教国文。他教书认真,要求学生严格,而对他们的观察又是细致入微。他曾说:“女学生的优点是,一般的比较用功,缺点往往是喜欢死抠书本,知识面不广。”因而鼓励她们应多读些课外读物,学校图书馆的书满足不了,他就把自己的藏书送来给她们挑选、阅读。在阅读过程中,还时时指导她们如何读才能有收效,才能提高文化水平和写作能力。他说,读书并不轻松,认真的读书,是要有毅力的。因此他提出精读离不开毅力和意志。他经常说,当你选择了一部书后,须定了时间好好地读。“用不着计较时间的长短,把自己喜欢读的书永久地读。”
有一次,夏丐尊从家中带来一部线装《淮南子》给学生陈仁慧阅读,还特地指定书里一批文章要她精读。陈却对传统文化书籍冷漠,觉得不像读小说那么有趣味。几天之后当夏丐尊查问她阅读进度和收获时,她竟然瞠目不知所对。这时,从来待人和善的夏丐尊有点生气了,沉默了好一阵子才说:“做学问,要锲而不舍才行呵!”
“一书到手,最好先读序,次看目录”
因为读书多、知识广,夏丐尊对书的功用的认识也就更为深刻。他经常就自己的读书实践向他人介绍。
1935年12月,南京教育部聘请时任《中学生》主编的夏丐尊为中国国语课教育讲学,不久他又应南京中央广播电台邀请,向全国中学生作《阅读什么》专题讲座。当时,社会上风行的仍是十年前梁启超、胡适等名流为青年学生所开的“必读书目”,以为这才是正规读书法,否则就是“野路子”。经常与青年人有文字交往的夏丐尊,通过编辑了五年的《中学生》,认识到时代在变化,出版事业也在作日新月异的变革,仅仅根据过去的书目按图索骥地寻找、阅读,只能造就书呆子,而不能解决学习根本问题的。他说,读书不能脱离生活,应该是“把读书和生活两件事联成一气,打成一片”;好的书籍“乃是培养生活上知识技能的工具”。
以实际生活为起点,根据自己需求,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夏丐尊说,每个人要阅读的书通常只有三种:一关于自己职务的;二参考用的;三关于趣味或修养的。他认为其中提到的用“参考书是因为有了题目才发生的”。如果没有定题,“学校图书馆虽藏着许多的书,诸君自己虽买有许多的书,也毫无用处。”要参考的书浩如烟海。因此选择主要和必读参考书尤见重要。他说,“在到图书馆去寻找参考书以前,我们应该先问自己,我所想参考的题目是什么?”“有了题目,不知道找什么书好,这是可以问教师、问朋友查书目的,最怕的是连题目都没有。”
要选定一个好题目是不容易的。
夏丐尊还说,读书要有专题,那就是要懂点目录学知识,通过目录学就可以较好地使用参考书。他说:“无论全读或略读,一书到手,最好先读序,次看目录。了解该书的组织,知道有若干篇、若干卷、若干分目,然后再去翻阅全书,明白其大概的体式,择要去读。”后来,他在南京就《这样阅读》作专题报告时就此作了详细叙说。他说:“比如对于汉武帝扩展疆土的题目,想知道详细情形,要去翻《史记》、《汉书》;还得先翻目录,通过目录中的本纪、列传、表、书等项目,就可知其大概了。”为了介绍目录学的功能,为读书人打开知识之门径,他还列举了研读达尔文的《进化论》:“如果要多知道些详细情形,你可到图书馆去找书来看,假定你找到了一本陈兼善著的《进化论纲要》,你可先阅序文,看这部书是讲什么的,再查目录,看里面有些什么项目,你目前所参考的也许只是其中的一节或一章,但这全书的概括知识,于你是很有用处的。”夏丐尊与叶圣陶合著《文心》中,在谈及类书编排方法时,又再次讲到查书,“你不妨到学校的图书室里去,见有什么类书,就看它的编排体例,这样到用得着它的时候,就可以翻查了。”这些话看起来平淡、朴素,然而却是大文人从自身博览群书的经验之谈。
早在1931年,他针对当时流行的读书不喜欢读基本之书,而好高骛远地读大部学术专著的弊端,对中学生说:“我敢奉劝大家,先读些中国关于哲学的原书,再去读哲学史;先读些诗集、词集,再去读文学史;先读些古代历史书籍,再去读《古史辨》。万一必不得已,也应一壁读哲学史、文学史,一壁读原书,以求知识的充实。钱索子原是用以串零零碎碎的小钱的,如果你有了钱索子,而没有可穿的许多小钱,那么你该反其道而行之,去找寻许多的小钱来串才是。”他将《论语》、《春秋》、《诗经》、《礼记》比喻为一些有孔的小钱,哲学史的《孔子》一节,即是把这些小钱贯串起来的钱索子。他还以阅读杜甫诗集为例,指出如果经常翻翻杜甫传记、年谱以及他人诗话里对于杜诗的评价,那就更能强化对杜甫诗作的理解。
朱守芬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