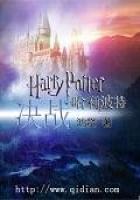嗬!口渡镇就在我脚下了。我以那种胜利者的姿态,长叹了一口气。
口渡,这是我为自己定下的最近目标。要是你还没走出山门雨就又下开了,那你就再拐回来吧,石柱兄弟是这么跟我说的。而出门不久果真就下了雨时,我是这么想的:你下就下吧,反正我已经走出来了,哪怕我只走到口渡,落脚在口渡镇,我也不会再走回头路了。说实话,这真有些像发誓,甚至有点小悲壮的意味,当然远远说不上是什么壮士一去不复还,我不会这么自况的,也没那么自恋。然而,此时你已经站在口渡镇的中心大街上了,这也算是个小小的胜利吧,有点可喜可贺呢,但是我并不打算在此为自己弄上一杯庆功酒什么的。我只是看了一眼那平时并不佩戴的手表,差一刻两点钟。哦,我是十一点左右出的门,用了不足三个小时,走了约莫二十五里的路程,若不是路上几番耽误,应该更早一些就走到这口渡镇了。现在也算是很不错呀,我还行,毕竟抵达了第一个目标。更值得欣慰的是,腿脚未报告劳累的消息,身体也不说自己疲乏的事,肚子也没闹什么意见。搁在往常,这会儿正是在午觉里做白日梦的好时候。而现在,你不累,不困,不饿,也就不必在此歇脚打尖儿,更不会在这里食与宿了,还想朝前走,还要往前走,我当然很清楚,前边的路还长,下边的路还远着呢。
酷暑午后,口渡镇大街上显得空荡荡的、静悄悄的,镇政府大门口无人出入,两旁的商店也没什么生意,几乎看不到行人,只有三两只狗卧在房檐下的阴影里乘凉,谁也不理睬我。感觉着,身上湿乎乎的,抹了把额头,汗津津的,便自嘲地笑道,我已经莅临口渡镇的地界上了,可是口渡人民一点动静也没有,他们好像浑然不觉呢,没人夹道欢迎你的到来嘛。呵呵,那就让我催马扬鞭离开此地好啦。走吧,还是赶紧走你的路吧。事实上,这里跟你是没什么关系的,你不过是经过此地罢了。
我边看边走着,一个黑脸三轮车夫赶过来,问我要去哪儿,非得拉上我不可,我摆了摆手谢绝道:不,我不想坐车。
黑脸车夫紧跟不舍,显然是要做我的思想工作:你怎么不坐车呢?坐上来吧,坐车快呀。
坐你的车也快不到哪儿去。我笑了笑说,我要去的地方,你拉不到的。
那黑又壮的车夫才不信这个邪呢,他一手扶车把,一手拍胸膛:你说去哪儿,我保证拉你去哪儿。你要去的地方我拉不到?笑话!说,你要去哪儿吧?
我要去商城,你行吗?我说。
那黑又壮的三轮车夫啊了一下,有点傻眼了,想来我这人就不是个生意,便哼了一声,蹬车而去了。
走到一家粮油商店对过时,我脚步迟疑了下来,一个三岔路口横在了眼前,也可以说是个丁字路口吧。一条向西,通向那个口渡集;一条朝东,通往一个叫做两河口的集镇,那边好像要比口渡繁华热闹得多,我多次听山民们说起过这个镇子,他们也常到那里去做买卖的,由于他们的口齿咬不清,听上去还以为是联合口呢;第三条是朝南的,也就是通向浮云山的。向西的路,再走上两三里,就是我曾经去过的口渡集了,现在我不买也不卖,不想去赶集,也就不想朝那个集市上拐了;朝南的,那是我的来路,我更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眼下只有朝东通往两河口的这条道路,才是我前进的方向呢。其实,这一切是用不着选择的。当然啦,口渡集那边正好临着国道,一样是通往商城方向的,可那样你就得绕上十几里路,握着汽车方向盘不过是抽支烟的事,可是要用你的脚板子来对付它,便要踏踏实实一顿饭的工夫了,眼下我可没有那么傻,不想再去干这种舍近求远费力气的事情了。
口渡镇毕竟是弹丸之地,迈开大步,越过两排店铺,一座石桥,眼前就是绿油油的田野了。我之所以走得这么快,是前面一位胖大的中年妇女召唤了我的脚步。我要赶上她,以问路的名义与她搭几句话,或者与她说话的时候顺便问一下路。
的确需要问一问路。我看到了,朝前的路再走上半里地光景,就又要分岔了,不知哪条路通向我要去的两河口。现在我可不想走错路啊。哦,这么多年,你走错路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最难忘的是那年在金沙江附近走错了路,那是跟妻子和友人一道乘汽车去泸沽湖的夜路上。万籁俱寂时分,一辆面包车颠簸在崎岖的高原山路上,像只逶迤在洲上的帆船,像是游走在梦乡里,怀里依偎着新婚的妻子,望着茫茫暗夜里的高原,心想就这么一直朝前走下去吧,管他走到哪里呢,也不一定非得去什么泸沽湖,尽管想象中的泸沽湖一定很美丽。我想,只要是你行走在异乡,行走在远方,行走在暗夜,去哪儿都是美妙的。不过,司机可并不这么想,他越走越觉得不对劲儿,觉得不对路,是路不对,走错路了,开始时他是自己小声嘀咕,自问自答了好几声,随后便停下了车,谁知道路这么一错,居然错出一个美丽来了,看到了我此生难再得的一次夜之美景。我拉着妻子的手,刚一跳下车,就惊叫起来,天哪,看天上啊!我的惊叫把车上人全都召唤下来了。哦,天上的星星那么多,那么多,犹如一条奔涌而来的银色河流,天上的星星那么低,那么低,好像就在我们的头顶上,或者正朝我们头顶压过来,压过来,天上的星星那么明亮,闪闪烁烁,就像节日城市里的万家灯火,真的就能看见它们眨巴着小眼睛了,不远处,传过来金沙江水哗哗的拍岸之声,脚下,一棵棵叫不出名字的奇异植物,一地看不清是什么的庄稼,路旁还有朵朵斑斓的野花,看着眼前这童话般的景象,大伙先是像群野狼那样号叫了几声,接下来便是如此干巴巴的感叹,哦,天哪!太美啦,真是太美啦,美极啦,从来没见过这么美丽的星星,没见过这么美丽的夜景啊。发出这种感叹的,当然也有我和妻子。记得,妻子当时紧紧拉着我的手,依偎着我,还踮起脚尖,轻轻吻了吻我,那么深情,那么诗意,甚至那么庄严,这是此前和此后所没有过的。一阵感叹过后,大家都不吭声了,全都默默望着天上的点点繁星,感受着这金沙江畔梦一样美妙的夜色。多年之后,我和妻子还时常回忆,说起那次走错了路的繁星之夜。呵呵,你怎么又想到了这件往事呢?那次走错路,是在高原云南,在金沙江畔,在一个绝美的夜晚,那是不可多得的。现在是在平原上,是在你要步行着走回商城去的途中,是在大白天,我可不想再走什么错路了呀。现在你要是走错了路,那就是走冤枉路了。于是,我就大踏步赶上了前面那位中年妇女。
在大嫂和大姐这两种称呼之间,我似乎斟酌了一下,选择了后者。后者扭头看了看我,很和善地笑了笑。这是一张介于山区大嫂与镇中学教师之间的脸,浓浓的朴实里,携带着一股淡淡的文化味儿。
大姐,去两河口要走哪条路?我问道。眼下,我和她走的是条上坡的东向路,前方不远下坡处,又岔出了一条向北的路。
你跟我朝前走一段吧。大姐指了指那条下坡的路说,然后你就走那条道儿。
哦,谢谢。我说,大姐,你是位老师吧?
你怎么知道?大姐默认了自己的身份,对我的身份也感了点兴趣:你是做什么的?
你看我像做什么的呢?我故意卖了个小关子,也就是没话找话说吧。
不是诗人,就是画家吧?大姐像是在仔细打量我:我猜得对不对?
差不多吧,我对陌生而热情的大姐笑道。差多少呢,我没说。自己的身份究竟是什么,我也没说。好在这位教数学的大姐并不想再求证了,她只是像明白了一样笑笑。
到两河口还有多远?我再次向这位教师大姐问道。
有十五六里路吧。这位教数学的大姐模糊地说,坐汽车一二十分钟就到啦,坐三轮车要用三四十分钟,走着去得一个多小时吧。说完,大姐笑眯眯地看了看我,像是在课堂上面对着自己的学生,用那种征询的目光。
她一下子就给出了三种答案来。其实,这答案听上去更像是提问。我想,接下来这位大姐该劝我坐车去了吧,我想让她这么做,如此,我就可能会有一番比较慷慨、比较男子汉的说辞了。然而教师大姐并没那么说,这让我有点小失落。我不太甘心,就很气势地主动坦白道:我要走着去!此时,我想听到的是劝阻,那种善意的,甚至是温情的劝阻。
教师大姐像是打量了我一眼,给予我的是理解,是鼓励,甚至是赞赏:好啊,像你这样壮的好身体,这点路不算什么事,不大会儿你就走到了。我们在两河口上中学那会儿,都舍不得花钱坐车,就是步行着去的。
哦。我微微一笑,笑意有点甜蜜蜜,有点酸溜溜,也有点苦兮兮。
两个人又搭着话儿走了一段路,大姐指着前面那片塬上的房舍,热情地说,我家就到啦,你上去歇会儿吧?
谢谢大姐。我说,不必啦,我还要赶路呢。
教师大姐指着前面那条岔开向北的下坡路说,你一直走,不用拐弯儿,就到两河口了,我又说了声谢谢,两个人相互笑了笑,摆了摆手,说了再见,然后,她回她的家,我走我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