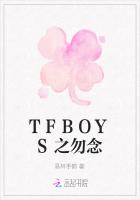那一夜,是人生苍凉的开始,也是老虎另一个十年的开始。
那一夜,在黑茫茫的四野跌跌撞撞的老虎,直到天明时分,才在一条偏僻的荒山野沟里停下脚。沟坡上的灌木密密实实,沟底泉眼涌流,草坪葱绿平坦,鲜有人迹。一路奔波得口干舌燥的他趴在泉眼上喝了个够,然后,将自己一直随身带着的一个磕碰得没有了漆皮的军用水壶灌满泉水,警觉地观察了一番,仰躺在泉边休息。早晨的鸟叫声在这条沟里叽叽喳喳,穿梭不停,微风扬起的空气中飘散着晨露的清香,浸人心脾。疲惫不堪的他在一夜劳乏后泛起困来,不知不觉间竟歪着身子睡了过去。当他惊惊怍怍地从噩梦中惊醒,已经是日上中天。梦境中的恐怖尚还弥漫在他的意识里,不由得起身躲到一边的灌木里,惊悸地把头藏在树叶间四处张望。这时候,肚子里咕噜咕噜地叫,腿肚子也跟着打哆嗦,他暗自慨叹:老了,真的是老了啊!手边的荆棘棵上有一层密密麻麻熟透的快要干瘪的红酸枣,他一个一个地摘着吃。干酸枣的果肉太过于薄,吃在嘴里,无疑于是在喰一种味道,在吃着饥饿,肚子里空荡荡的肠鸣声依然不断。灌木丛里还有着许许多多大大小小成熟的果实,他一样一样采摘,然后浅尝即止,慢慢等待身体的反应。
此刻的他挥不去心头的哀伤,他想:自己难道就像这野果,长不到家里,也长不到村子里了吗?不觉鼻子酸酸的,有泪水滚到了嘴角。在这条人迹罕至的山沟里,他靠着泉水和野果,一躲就是四五天。他觉得自己可能是走不出去了,甚至悲观地盘算着在哪块草地上种上庄稼,再养些牛、羊,就在这世外桃源般的地方来打发自己的余生。
这天日暮时分,他看见山沟口有个人顺着山溪走进沟来。进沟的是位老人,挑着担子由下往上走得很吃力。他躲到灌木丛中,观察着老人的身后是否有人跟进来。老人一直走到沟底宽阔的地方,选择了一处草丛稀疏的土台子,放下担子一屁股坐下了。他纳闷,天快黑了,这老人不赶着回家,一个人钻进这山沟里做什么,难道也是和自己一样的逃难人吗?
他怕自己的突然出现会惊着老人,从藏身的地方走出来,远远地就打招呼:“老人家,您好,天快黑了,怎么还一个人到这山沟里来啊?”
老人打量了他一下,朝四周看了看,反问他道:“这山沟是你的吗?呵呵,你在我就不能在呀?”
老虎看老人的面相还和善,就大胆地走过去,在老人身边蹲下来。老人戒备地审视着他,问:“你问我,我也问问你,天快黑了,你怎么不赶着回家啊?”
老虎叹息一声说:“我是被困住了。”
老人再次打量了他一番,恍然大悟地说:“哦——明白了,你是农场跑出来的下放干部——牛鬼蛇神!”
老虎想说不是,但还是点了点头,说:“我的事情太复杂。”
老人憨厚地笑了笑说:“大长一夜呢,有聊的。你先帮忙把这边上的草薅了,咱能埋锅造饭。”
老虎突然就掉泪了,他感激地说:“不瞒老人家,我已经好几天没有沾粮食籽了。”
这一夜,老虎和老人聊得很投机,他知道老人是个靠着吹糖人手艺走南闯北求生活的人。见多识广的老人很开朗也很豁达,建议老虎跟着他走,“别小看这吹糖人的小生意,有了它,你就能天不管地不收,把这个糊涂世界丢给别人,自由自在地过活。”
老人的话进到了老虎的心里,走投无路的他立马就赞同了,决定跟着老人去游街串巷地吹糖人了。他甚至乐观地想:如果吹糖人能吹到西地去,没准就能一路吹到圣地麦加去,照样去朝觐嘞!
老虎开始跟着老人走乡串村了,两个人换着挑一副担子,一个村头挨着一个村头坐,围着他们的都是些天真烂漫的小孩子。孩子们喜欢老人吹出的糖人,猴子、公鸡、狗——吹什么像什么,有钱的一分二分五分买,没有钱的可以拿粮食换,有碎铜废铁、破布烂鞋也可以换,总之是拿手艺从孩子们手里讨生活。两个人一起风餐露宿,苦是苦,可有个伴的乐趣还是让他们少了许多的孤寂。
天长日久,老虎渐渐地也学会了吹糖人,又弄了一副担子,和老人白天分头进村,晚上相约碰头。老虎说:“咱们向西吧?”老人说:“行啊。”他们便一路西行,一行就是小半年。老人说:“西边人烟稀了,咱还下东边吧?”老虎说:“走。”他们又一路向东,还是小半年。这样的日子过起来沧桑而令人惬意呀!
就在老虎跟着老人无牵无挂地行走在天下地上的时候,家里人正为听说老虎犯事而忧心忡忡。坐卧不宁的秀更是按捺不住,安慰完公婆,扔下大大小小的孩子和家务,一路打听着深一脚浅一脚地找到了高山。高山的多斯蒂知道是马阿訇的媳妇找来了,都羞愧呀,好好的一坊回民在着,阿訇却没有了去向。单乡老对秀好生安抚,大家凑了钱、粮食和山货,专人把老虎撇下的书籍、行李和秀送回了庙下。
秀从高山走的时候是哭着走的,一步一回头,像是老虎还在这里,兴许就藏在坡坡岭岭上的某个地方。她真后悔让老虎来这里,夫妻一场,说不见就不见了,这辈子还能有见面的一天吗?一路上,她悲伤地对送她的多斯蒂不住交代,要是看见老虎,就叫他赶紧回家。
老虎也曾路过了庙下。他看见庙下的大路上奔跑着贴满红绿标语的汽车,还有街巷里也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人们昂扬地生活在批林批孔的斗争中,整个气氛让他惊悸不安。想家的焦渴使他强壮胆闯进了街里,用烂草帽遮脸,在庙下学校的门口心慌意乱地坐了半天。打发完不认识的孩子们,失魂落魄的他还不忍离去,像做贼似的溜着街边往家的方向走。走到东寨的时候,他是想让路边擦身而过的乡亲们认出是自己回来了,可又是担心会被他们认出。在自己的家门口,他终于停下来,看着虚掩的门,他试着叫了两声,“换糖人了——换糖人了——”。心都砰砰地要跳出来了!他是多么的希望孩子们会跑出门来,可此时的街道上正好走来了下工的社员们,只好一如惊弓之鸟般地离开了,终究还是没有胆量走进自己的家门。
实在不舍得离开的他绕到寨外,昔日宽大的寨墙已经似有似无地被损毁了,他像一个啼血的杜鹃鸟,顺着那段他曾经熟悉的寨墙来回地反复走了几遍,口中不住地喊叫着“换糖人了——换糖人——”。他继续在期望着秀能听见他的声音,能听出是他的腔口,赶来和他见上一面。可一切都是枉然!大街上的高音喇叭里传来了雄壮的革命歌曲,歌曲中浓烈的战斗气息不仅令人生畏,也盖过了他的声音。当他满脸泪花花地离开时,忍不住站在离村不远的高坡上回望,久久不愿抬起脚步,已经长有半尺的灰白胡须在微风中扫着脸颊,把滚落的泪水拉成了细碎的线!
一晃几年,老虎像影子一样跟随着老人,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老虎的兜里揣着一个精致的,但由于时常触摸已经变得脏兮兮的塑料封皮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他走过的每一坊回民所居住的村名。这些地方的清真寺绝大部分都不再为安拉乎上拜下拜了,阿訇们恓惶地住在寺里,应付一坊回民日常的宰牲和婚丧嫁娶。一路走来,看着教门里一片落败的气象,让他心生悲凉。
每见着一坊回民聚居的村落,他都会带着老人悄悄地到清真寺里去上拜。刚开始老人笑他,说自己是啥都不信,就相信一天三顿饭吃到肚子里实在。老虎说:“你不知道有信仰的好啊!”
老人也点着头说:“你能这样信,那就肯定有你信的理儿。”
一次,老虎和老人见到一个阿訇亲自带着一个落难的多斯蒂,挨家挨户去回民家里收乜提。转过来脸,老人对老虎说:“您这教门是真好嘞,人心都变成了金子啊!”
有一天早晨,老人的眼皮耷拉下了,抬起来都很困难,更别说人能站起来。虎泪流满面地把佝偻成一团的马明抱在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