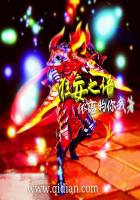自从四里八乡来了知青,各个村子里都不安宁。老百姓经常谈论着知青们偷鸡摸狗的勾当,无奈地直摇头。
有了招弟的那件事,老虎看着这些无事生非的年轻人暗叹:这样下去可怎么行啊!他故意站在门口没话找话地问这些年轻人:“多年没有去,洛阳现在变化大吗?”还笑容可掬地招这些本就好奇的知青到清真寺里玩,跟这些知青说过去洛阳城的事情。他不是卖弄,他是想告诉这些知青,今天的幸福生活来得不容易,至少没有了过去遍地狼烟的不太平日子,人在哪里都该知足安分地生活。他说出来的话很让这些知青钦佩,这样的一个小地方难道还藏着一个见过大世面的老革命呀!他说他当年在洛阳城里打老日保卫洛阳城,怎么一刀一个日本鬼子;他说他怎么被皮司令看上当八路,上军政干部学校;说他在洛阳城里做地下党,怎么跟杨平县长做交通员送情报;说自己当区干部怎么一枪打碎了狗地主的头,把土改搞得轰轰烈烈……当然他也讲了,自己是受了地委一个领导的报复,所受的冤屈连杨平县长也帮不了他。他说:“俺扭头就背起铺盖卷不干了,革命累了,还是歇歇吧!”他当然还不失时机地向年轻人透露自己喜欢写诗,写的诗歌还发表过。总之为了教育这些年轻人,他是竹筒倒豆子,把该说的都说了。
年轻人对他的诗歌感兴趣,特别是女孩子,喜欢听他朗诵。虽然他朗诵起诗歌来,女孩子会因为他蹩脚的普通话而掩着嘴笑,但在索然无味的乡村里,这毕竟能让年轻人感觉到文化的美好。
他在诗歌中写道:
在瓦蓝色的天空上
飘动着雪白的云朵
羊毛一样的云朵啊
还真像是一群被放牧的羊
整个天空都是羊群自由游走的牧场
放牧的老羊倌
就是那个一刻不停的太阳
……
他还写这个山村:
鸡啼唤醒了沉睡的山村
炊烟升起在家家户户
勤劳的农民在生产队的钟声下聚集
队长一声号令
他们像军队一样奔赴田野
碧绿的田野里满眼青翠
茁壮成长着丰收在望的庄稼
层层的梯田
像是挂在山坡上的画
……
知青们纷纷说:“哪里有那么好啊,破破烂烂的,要不是没有办法,打死也不来。”
有知青奚落老虎说:“你眼里的景致这么好,是不是打算在这里扎根啊?”
更有的人讥讽他说:“你也是无奈吧,要不然能放着洛阳的干部不当,跑到这里来当阿訇,这里哪儿好啊?”老虎不跟这些年轻人一般见识,他们好奇教门,就给他们讲教门,至少讲经能使他们狂躁的心收拢起来,不再去胡作非为。
又一个春天的风吹来了,老虎感觉不到那风的柔丽,他深陷在焦躁不安中,因为招弟的举止让他感到怪异。平时在众人面前沉默寡言的招弟,常常自己躲在没有人的角落里掩着嘴傻笑,而且笑得很开心。发现一次也就罢了,被他发现多次后,就不得不多了个心眼观察招弟。奇怪的是招弟除了会背着人偷笑,其他的行为并没有什么异常,这让他稍微放了点心。他说招弟,想笑就笑出来。招弟面无表情也不做回应,好像不是在说她一样地不理不睬,过后依然故我。发展到后来,老虎不用去发现就能感觉到,她又在哪个角落里偷着笑。如果不去打搅,她可以躲在那里想想笑笑,掩着嘴笑上半天,甚至笑得前仰后合如舞蹈一般。这让老虎的心里头越来越不是滋味。
老虎的心情很郁闷,愁眉不展地跟单乡老聊天。他说:“再不嫁出去,怕是要把这闺女糟蹋了。”
单乡老不愁,只是埋怨道:“人往清真寺里一丢,当爹娘的倒是省心了!”
老虎说:“你是这一坊的乡老嘞。”
单乡老讪笑道:“乡老也不是她爹娘啊。”
老虎说:“我说你咋就不愁嘞?”
单乡老说:“愁啥愁,愁也是这事儿,不愁也是这事儿。这时节人都拴在庄稼地上,忙得脱不了身,等秋罢各坊间串来串去说亲保媒的多,有的是茬口,有剩男还能有剩女?”
到了秋罢,果然就有外坊的回民们跟高山这里沾亲带故地跑来说媒拉纤。隔三差五就能见到一个少男或者少女,羞答答地跟在年长者的身后,在街巷里被带来带去。各地的回回居住地都是小集中大分散,小集中的大多是近亲,想结门亲就得顺大分散的势,所以远嫁他乡是在所难免,男婚女嫁于百里之外甚至千里之外都很正常。
招弟也被安排着见了几个,离得近的,她都是冷冷地没有多少热情。最后一个是外省的,老虎以为是不行了,哪有愿意远嫁的女子。谁知道招弟竟红着脸羞答答地答应了。老虎看出来了,这闺女显然是要远走他乡,这让他心里涌出几分怅然!
招弟要走的时候,天已经明显地寒起来,西北风吹在身上冷飕飕的。招弟穿上了她娘给她缝的碎花蓝棉袄,外面罩个绛红色的外罩,棉袄长出外罩一圈,像是绛红外罩上的一道镶边。下身是一条黑斜纹裤子,据说是招弟弟弟结婚准备的男裤,临时改成了女裤让她穿。裤裆肥大,裤腿还长,里边套了棉裤,显得臃肿不堪,走起路来像是急着往水塘里跑的鸭子。
老虎也怜惜招弟,远嫁的伤感虽然没有挂在招弟脸上,但他能看出是招弟的伤是在心里。她已经不在背着人想想笑笑,是背着人流泪。有一次老虎问她:“孩子,不想去就说出来,咱不去那么远,一辈子想再见你娘一回都难。”
招弟噙着泪对着老虎若无其事地笑了,她声音颤抖地说:“俺从小做梦就是想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让俺娘想找俺都找不到。”
老虎叹息一声,招招手要招弟近前,把手里攥着的一张汗津津的十元钱递过去。招弟惊慌得把手背到后面握着,不敢接这张皱巴巴的钱。十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一毛钱可以买一尺布,两毛钱可以买一斤肉,五块钱足可以打发一家人一年的油盐钱,可想老虎这时候递出的十块钱对招弟的震撼!老虎手递了几递,招弟摇着头就是不肯把手放出来。他索性强拽过招弟的一只手,把钱踏实地放进她手心里握起。
招弟握着钱的手在抖擞,她说:“大大,俺亲娘已经给俺了五块钱,缝在贴身的棉袄里子上了。”
老虎说:“那你回屋,把大大给你的十块钱也缝上,在家百日好,出门一日难。”
招弟转身走了,过了一会,腼腆着脸过来站在老虎面前,柔顺地告诉老虎说:“大大,俺把钱缝在一起了,这棉袄暖和得很。”
老虎慈祥地微笑了,说:“快走了,多回两趟家,温存温存两家的人。”
出嫁的日子单乡老也给招弟安排好了,正好洛阳城里要来一辆汽车,往村子里送下乡的新知青,回城的时候能顺脚捎他们一程,可以让招弟跟新女婿省下几毛钱的车票钱。
知识青年们来的那天,天色阴沉得很,但是村口的大队部门前却热闹异常。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被组织列队夹道欢迎,不但许多人手里举着红红绿绿的三角纸旗,上面写着欢迎的口号,还有锣鼓齐鸣的动人场面。看似很隆重,老百姓们已经没有了迎接第一批知青的新奇,都是一肚子的不情愿——庄稼地打下的粮食连自己都吃不饱,再分来这些知识青年,这分明是在抢口粮嘛!
村支书也在大家面前喊话了:社员群众不要乱发牢骚,这些知识青年都是毛主席派来的,得罪不起。毛主席说农村是广阔天地,咱这儿不是比城里宽敞嘛,不派他们来咱农村插队落户,城里就挤不下了。再说,城里人就是不来,咱们不是照样得交公粮养着他们吗?他们来咱农村干活挣工分吃饭,已经很不错了。咱也是当人家的农民伯伯嘞,为了毛主席,咱们也得摆出高姿态,也都得高兴点儿!
单乡老一直跟在支书身边,招弟他们要趁顺风车全凭支书打招呼,他不能不在心。幸亏送知青来的车上有几个随来的家长,不敢不给支书面子。单乡老一脸兴奋地跑过来对老虎说:“马阿訇,都说妥了,赶紧给他们准备准备。”
打发闺女的两家人都像是做错了事情一般,愧疚地把招弟和新女婿围在清真寺的墙角说些送别的话。老虎吩咐招弟:“给亲人们说说话吧,别着头这哪像是出嫁?这不是三里五村,想回来走娘家抬抬腿就来了。”
老虎的话让招弟泪流满面地哭出声来,两家人都是哀哀地哄劝。还有几个以前和招弟亲近的小姐妹,都过来抱了头哭。这边的动静一下子引得人纷纷朝那里看,弄乱了场面,惹得支书在那边吆喝:“正欢迎知青嘞,那边动静小点,像啥?”
单乡老跑过来交代一番,叫老虎带一干人去清真寺给招弟念个“伊扎布”,简短举行个教门内的仪式。
一干人再簇拥着招弟出来的时候,单乡老已经催着上身通红的招弟往车边去。车上坐好了送知青过来的几个家长,那些家长的神情和车下送招弟的人差不多,没有几张是能笑踏实的面孔。他们是把孩子撇下了,而车下的是要把孩子送走,都是依依不舍的,脸上却挂着勉强挤出来的笑容。新女婿先扒上车,他在上面拽着招弟的手,下面人推扛着把招弟送上了车。站在车上的招弟一下子高高在上了,朝着下面送她的亲人们泪巴巴地笑。人们往常看习惯了那个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的招弟,今天再看这个一身簇新的招弟,一下子都惊讶于她苍白美丽的面庞。许多人都在议论着,叹息着,又一个好姑娘远嫁了!
站在远处的老虎不知道自己的泪是何时流出来的,他沾着泪,把招弟看成了自己的亲闺女小叶,小叶也该是出嫁的年龄了,嫁女的惆怅怎能不淹没他柔软的心呀!
汽车没有留给人过多告别的时间,发动机地轰鸣声响起时,招弟的娘终于是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了。她哭喊着:“招弟呀,你咋恁憨嘞,你就这样舍下娘了吗?俺的闺女呀,你叫娘啥时候还能见你一面啊——”车上的招弟木呆呆地,很快就被汽车扬起的一溜子烟尘给遮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