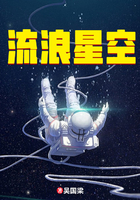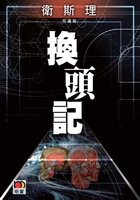老虎说:“我无愧,当时分地用弓丈量。”他说的时候还要比画,所谓“弓”,就是将竹片弯成弓形,用绳子绑起来,以“弓”的一端为圆心转动,一弓就是一丈,既简单又实用。“区公所、农会派出的干部手里拿着弓,一丈一丈的主持分地。一个村分地的时候,往往几个村的人都来围观,有人唱戏,有人扭秧歌,有人放鞭炮,有人高兴得掉眼泪,别提多热闹了!谁还能少分哪一家一寸地?我无愧呀!”
这句话老虎已经在县政府大院说了不止一次,所以关于对他的处理,谁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大家都很替他抱屈,可也没有办法,杨平县长的证明材料都不顶用,谁还能保?但大家都安慰他:“去吧,黑的白不了,白的黑不了,调查得越清楚你越清白,怕什么?”
老虎嘴上轻松地说:“谁说不是呢,身正不怕影子斜。”
可是夜里躺在床上,他还是不免心里有些打鼓,满腹委屈地流下了两行清泪。当时面色阴沉的杨平把他叫到办公室,将一张加盖着大红印章的信函递给他看的时候,他的眼睛一扫就模糊了,红印章马上膨胀出满脑子的红,像当年他杀鬼子时候的血红,很血腥很恐怖。但他想到这也许是为主的前定,马上心里就淡定了。他很不屑地拿眼瞄着信函,上写着:由于马老虎在战斗部队工作期间,涉嫌多次脱逃,问题严重,疑点较多,请县政府迅速交送到专区专案组给予调查甄别并作出定论。
杨平十分气愤地说:“这才解放几天,就使开官僚作风了,拿着人民给他的权利替他的地主老子打击报复同志,这样的领导终究要被人民拉下马!他们揪住你在战斗部队的事情,我很清楚,却不是当事人,真还让他们钻了空子。我要替你申诉,你先接受他们调查去,怕什么,黑水里还洗出白萝卜呢!”
老虎再次揉揉眼看那信函,故作平静地微笑着对杨平说:“我要当诗人,不会去在乎这些,反正也不是党员,他还能想办法开除我的党籍不成?我蔑视他!”
杨平被他不知轻重的诙谐逗笑了,也擦着眼角的泪水说:“你别想不开就行,事实终究会水落石出的!”
老虎是被杨平亲自送往专区专案组的,去的时候两个人一路上走着还说说笑笑。杨平担心地问:“老虎,你真不害怕呀?”
老虎笑着摇头说:“我不害怕,不瞒您说,有了王阿訇给的书,我有使命了,心里比啥时候都踏实。他们想将我咋样处理都无所谓,我不在意就不害怕,我是要当诗人的,要为我们回回写一部史诗!”
杨平爱惜地轻叹了一声,说:“真是个天生的宗教坯子!”
老虎纠正道:“错了,我们回回都是安拉的信士。”
分手的时候,杨平一再叮嘱他要坚强些,不要意气用事,要相信组织!
老虎在专案组的表现是气定神闲,问什么说什么,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是什么就不是什么?既然是非要他交代在战斗部队前后的细枝末节,他就还像在战斗部队一样的做派,默习拜功,一刻不落地做五时拜,闲暇时间就背诵《古兰经》。专案组的人也都是从战斗部队转业的,大部分都是一个部队或者是兄弟部队的,听说过老虎当兵前一个人打鬼子的壮举,也知道些老虎在部队的怪诞行为。这些过去都是当笑话说的,现在当案子来办,都同情他,也能理解他,更不难为他。半月下来,老虎脱逃的事情还是似有似无,朦朦胧胧。
老虎还见到了那个气急败坏的李专员,那个和他有过一面之缘的李师长。他看老虎一脸超然世外的神态,讥讽道:“你倒很不在意自己的错误呀。”
老虎不卑不亢地说:“我是不在意,皮司令和程部长都不在意,还派我当地下党的交通员,我还在意什么?”
李专员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说:“你不要拿领导的失察当挡箭牌,来蒙混过关。”
老虎不软不硬地顶上一句:“我要不蒙混过关,洛阳的城防图就到不了咱解放军的手里。现在这洛阳城已经是人民的城市,不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老财的天下了,更没有蒙混过关的必要。”
李专员的脸一赤一红,直瞪着老虎说:“别以为我收拾不了你!”
老虎也起了火说:“日本鬼子我都敢收拾,还怕你收拾我,你要是替你那地主老财的爹反攻倒算,就明着来!”
老虎的嘴张开就合不拢了,他激愤地指着李专员的鼻子说:“对您那地主老财的家,我无愧。当时分地用弓丈量,区公所、农会派出的干部手里拿着弓,一丈一丈的主持分地。一个村分地的时候,几个村的人都来围观,有人唱戏,有人扭秧歌,有人放鞭炮,有人高兴得掉眼泪,别提多热闹了,谁还能少分哪一家一寸地?人民都高兴嘞,我无愧呀!”
李专员被老虎弄得下不来台,气愤地和他脸对脸地拍桌子,最后气喘如牛般背着手摔门走了。老虎跳着脚拉开门追到院子里,不依不饶地对着灰头土脸的李专员的背影喊:“你捏造事实收拾我,为你那地主老财的爹爹反攻倒算,公报私仇,你还是个称职的共产党吗?你不亏心就和我当面辩论呀!”
气头上的老虎狂躁不堪,想起自己为此事弄得和素素成了仇人,乡里也把自己推了出来,在县政府里还是落了个不明不白,到现在还要被没完没了地审查,不由得悲愤交加,伤情的长啸一声,对着监视审查他的干部们说:“有李专员在,我无路可走。我就再脱逃一次给你们看,从此不当这干部了。”说着甩开步子走出了审查他的小院。审查他的干部们追出来,假意的拦截哪里能敌过真的要脱离,终被老虎挣开,拂袖而去。
老虎很洒脱地回到家里,连夜写了四封信,给素素的,给杨平的,给王阿訇的,给地委的一封公开信。第二天大早往邮局一送,挑了个担子,一头是铺盖卷,另一头是书籍,头也不回地出了洛阳城。
他是要往哪里去呀,他也不知道自己的脚是在向哪里走?脑子一片空白,只想先离开这个城市,随意走到空旷的城外去透口气。在离城不远的一处野风轻抚的山冈上坐下来,回过头来看着这个复杂的城市,他的心情糟透了。这里有他崇信的宗教,这里有他爱恋的老师,这里有他沉醉的女人,这里有他憎恨的小人!按说他在这里是最能品尝人生的,但他怯怕那个小人,因为怯怕一点,却要舍弃很多,他是多么的不舍啊!
坐在悲凉的风中,冷静下来体会自己的莽撞,他想自己也许是真的把自己糟蹋了。为什么就这样地走了?走了就是屈服了啊,消失和回避不都是属于屈服的举动嘛,如果自己的举动被人当做了逃避,那可真的成了无话可说的屈服!他在一个山冈上的一座低矮残破的山神庙里,放下自己的铺盖,想着要不要再冲回去。
山坡上一个放羊的老汉在天色落黑的时候凑过来,问他:“客官,你不会是想占我的窝吧,想跟我做伴?”
他看看已经围在山神庙前的一群白羊说:“这庙是你的吗?呵呵,呵呵,那你是这群羊的官了,蒙你的福,我也当一夜羊倌如何?”
老汉说:“俺可没有带你的干粮啊!”
老虎说:“俺是回回,不动你的吃食。”
老汉很诙谐地说:“你是回回嘞,看看俺是啥?”说着,一把抓下头顶上破得不能再破的烂毡帽,很珍惜地从怀里掏出一顶被汗渍浸黄的礼拜帽,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骄傲地看着他。
老虎也赶紧从包裹里拿出已经多日不戴的礼拜帽,庄重地戴在头顶,很自豪地与老汉对视着,两个人都哈哈哈地大笑起来。
老虎问候道:“老表,身子骨硬朗呀!”
放羊老汉声音洪亮地说:“遇上老表了。托靠主,结实得很!”
这个山神庙是放羊老汉过夜的地方。他对老虎抱怨说:“以前的羊群是地主老财家的,天黑了就赶回去上圈,羊们路上啃两口庄稼苗,那庄稼苗还是地主老财家的,没啥。如今不成了,羊都是一家一户聚拢起来的,地里的庄稼苗也成了一家一户的,羊们啃了谁家的庄稼苗,谁家就跟我吵,倒是不敢再往村子里圈了!”
老虎看着放羊老汉黢黑苦楚的脸,说:“给自己买顶麦茬蹄儿帽子吧,风吹日晒的。”
放羊老汉抖了抖手里的烂毡帽,矜持地笑了笑,说:“就这个烂毡片将就着吧,要是换顶新麦茬蹄儿帽子,他们指不定怀疑我背地里薅了多少羊毛呢?”
老虎问:“你放羊不图个羊毛图什么呢?”
放羊老汉狡狯地说:“羊毛一年只能下一回剪子,图羊毛我一家几口还不喝西北风去?不瞒您说,图的是母羊下羊羔,产俩有我一个,产仨有我俩。”
老虎说:“那要是只产下一个呢?”
放羊老汉爽朗地笑了:“我就朝那公羊屁股上抽两鞭子!”
老虎问:“多斯蒂,您一个月能进一回寺不能?”
放羊老汉惭愧了,说:“咱那一个村就俺几户回民,请不起阿訇,更盖不起清真寺,每年只有过开斋节的时候,去城里请阿訇来给亡人们走个坟。”
老虎表示理解也不解:“那见天怎么礼拜?”
放羊老汉自豪地用手朝西方指了指,手捂在左胸上说:“天房在那儿,咱穆斯林可不敢当着为主的说假话,一天的五时拜咱也一拜不少,都在心里呢。别的咱不知道,就知道穆斯林是为主的护佑着,不拜主还能叫穆斯林呀!”
放羊老汉确信老虎是要在这里跟他一起过夜后,高兴地去拾柴禾生火,用一个漆都被磕磕碰碰得看不出颜色的旧军用水壶给老虎烧水。他说:“我一个人,喝口凉水啃口馍就是一顿饭,你来了,总得喝口热水吧。老表是干啥的,看着不像是土坷垃里刨食的?”
老虎想告诉老汉自己是逃出来的干部,可为什么说出自己的痛苦让别人也跟着没有好心情呢?就顺嘴说:“我是搞文学艺术的,就是写诗歌,要为咱们回回写一个史诗。”看着放羊老汉一脸费解的样子,也难为的不知道该怎么去介绍自己。索性就把自己那无师自通的诗歌背几段给他听。
放羊老汉恍然大悟,说道:“你是编顺口溜的!”
老虎说:“对,就跟顺口溜差不多。”
放羊老汉突然就不恭了:“你也是光光鲜鲜的少年,咋就学这二流子的营生,咱回回还没有见过这样求生活的,你家老人就不管你吗?”
老虎一下子就感到了屈辱,想说他愚昧,但看着为自己烧水泡馍的,还是很快释然了。轻叹一声说:“怎么能说是二流子的营生,这是读书人的事业,读书人你总该知道吧?我是东关清真寺的海里凡,也读过汉书,想把咱回回的事情写下来,让咱回回知道自己上辈的事儿,也让天下人知道咱们回回。”
放羊老汉虽然听得一知半解,但“海里凡”三个字又让他对老虎肃然起敬了。他不轻不重地打了一下自己的嘴,懊悔地说:“看俺这张嘴!”又很欣喜地对老虎说:“你会念经,那就为俺当回伊玛目,叫老汉也能听着经做回礼拜吧!”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脸上带着十分虔诚的企求。
那一夜老虎没有睡着,习惯了孤单的放羊老汉也是兴奋得丝毫没有睡意,两个人在寂寥的破山神庙里,你一句我一句的说话到半夜。
放羊老汉跟老虎聊到回汉千年亲家,说他们村也是个这样的村子,回、汉两门人都姓张,回回张家跟汉人张家当亲戚处。据说是大宋年间从西地波斯来洛阳做生意的穆斯林商人,生意做大了,挣的钱车拉马驮都带不走了,就地娶了张家的闺女立了门户,连后辈的娃儿们也随了张姓,家谱还能续到一起,多少辈儿人都是舅跟外甥的表亲。
放羊老汉总结说:“你说咱回回是哪儿来的?回爹汉妈,老辈儿人都是这么传说的。”
老虎感慨地说:“你倒也常常思考这么深远的问题!”
放羊老汉说:“放羊没事儿闲的,羊吃草,我能不找点事儿想。”
老虎问:“对咱回回的事,你都想了些什么?”
放羊老汉说:“我想咱回回就像那天上飘来的一朵云彩,到汉人这地界变成雨了,落在这土里走不了了。是这个理儿吧?”
老虎说:“肯定是这个理,你能带我去看看张家村吗?”
放羊老汉摊着手说:“羊咋弄?你自己去吧,不远,就说见着我了,有热腾腾的饭让你吃。要是这时候把羊赶回去,那是挣骂名嘞!”
第二天,老虎去了张家村,在弯弯绕绕的山路上挑着担子,汗流浃背地走了将近半天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