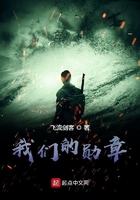一顿酒足饭饱之后,刘文河和严中在刘文河的房间歇息,两年过去了,刘文河的房间布局依旧没变,而严中却是对刘宅一草一木充满好奇,严中出身贫寒,对大户大宅人家陌生而又向往。
“刘学员大人,严中自由出身贫苦,小的时候见到大户人家的府宅很是好奇,今日一见果然是,您家的床都比我家的炕好。”严中出身贫寒,学识有限,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刘文河却没有严中那样好心情,反问严中:“严中,你是怎么当的兵?”
严中老老实实说:“去年家乡遭遇洪灾,淹死不少人,我们一家命大活了下来,但是我家八口人,养活不过来,正好赶上帝国一个当官的对我父母说,要么服徭役,要么当兵,我爹当时就决定让我当兵。”
刘文河还想说什么,严中问道:“刘学员大人,您说我们这次组建团练的事应该没问题吧?”
刘文河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可是也不想扫严中的兴,他不想落下自己还未上任就摆官架子的名。
“严中,你早点睡吧!”
严中顺从地脱衣,脱到一半却发现刘文河没有脱衣之举,“刘学员大人,那您怎么不睡?”
刘文河整了整军容,“我出去走走,你就不用管我了,对了,叫我文河就可以了,叫我大人,我心里不舒服。”说完,径直走出门。
严中一脸不解,自己怎么得罪刘大人。其实他根本不知道,今夜不仅刘文河睡不着,还有整个刘家所有人。
错落有致的楼阁,沁人心脾的花香,藓斑点点的台阶,连荫遮天的古柏,都是刘文河成长的见证者,也是刘文河记忆最深处最温暖的地方。
家里的布局依旧是他离家去军校报到时候的样子,甚至古柏下的梅花桩也依旧矗立在原处。
摩挲着梅花桩,刘文河回忆起自己十一岁那年要习武,被父亲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母亲在旁边默默流泪。也回忆起自己不管严寒酷暑,反反复复地在梅花桩操练。
“少爷,族长请你到祖宗堂。”一个轻柔的声音嗫嚅着,是小翠。
小翠是家中的丫鬟,刘文河去军校报到时,小翠只有十五岁,已是豆蔻年华,而如今已是亭亭玉立,尽管穿着丫鬟宽松的衣服,却仍然掩盖不住曼妙的身段。
去军校毕业的那一天的路上,大街的行人投来羡慕的眼光,而刘家上下却没有人为他送行,只有小翠在他临走之时,送给他一些衣物等生活用品。小翠对他的好,他心里明白,只是此时此刻他不知道如何向小翠开口。
刘文河满怀感激地看了小翠一眼,就来到祖宗堂。
祖宗堂灯火幽暗,若隐若现,缭绕的烟雾轻浮在幽暗的空中,很清晰地扭曲成各种形状飘浮到上空直至消失不见,错落有序的牌位林林总总,无声地讲述着刘家的历史。
“来了。”声音很苍老无力,却很有威严。是族长刘谨钊?
“是的,族长爷爷。”
“跪下!”
刘文河很顺从地跪在牌位前,刘谨钊从幽暗深处缓缓地走到刘文河面前。
刘谨钊养着牌位,问,“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这里吗?”
“是回乡组建团练的事。”刘文河很诚恳地回答。
刘谨钊摇摇头,“是让你对着列祖列宗的面起誓。”
起誓?刘文河不解,刘谨钊缓缓地转过身子看着刘文河,刘文河第一次认真地看着刘谨钊的眼神,慈祥和蔼。
刘谨钊缓缓道,“太祖大帝南征北战时,我们的老祖宗刘荣就跟随太祖征战,为帝国的成立立下汗马功劳,太祖大帝建国登基后,祖宗拒绝功名利禄回到了家乡经商,祖宗到了晚年,夜里噩梦不断,便一直怀疑是他当年斩杀的仇敌冤魂索命导致,所以祖宗劝诫我们这些子孙,莫入军中,你读军校我不说什么,毕竟我不是一个腐朽不化的人,文河,当着列祖列宗的面,你只要说你不组建团练,剩下的事我会写信给你其他的叔叔伯伯们搞定”。
“族长爷爷,这是为何?”刘文河不解。
一缕香烟诡异地闪现在刘谨钊面前,扭曲了一下很快消失不见,刘谨钊喃喃,“祖宗回归故里,给我们后世拟定了家谱,荣锦归故里,子嗣乃谨记,文武勤见习,永不入飞骑。这二十字就是在告诉我们后世永远不踏入军队。”
刘文河从未忤逆过族长爷爷,也从未敢忤逆,族长爷爷的权威一向都是刘家人不可侵犯。刘文河多年以后回忆起这事,其实他可以答应族长爷爷,发动家中各种关系完全可以上任一个清闲美差,但是他没有这样选择。
刘文河半天嗫嚅,“可是当今局势您也知道,南方半壁江山已沦陷路氏叛逆之手,他们接下来就会向北进军,我们这里就是首当其冲。”
刘谨钊脸微微一寒,“难道你就想用柳河镇的乡亲们的尸体来给你的胸前添加那一颗所谓的勋章,孩子,你这是草芥人命。”
刘文河继续说着,“不,我从未想过用乡亲的尸体为我加官进爵,我只是想带领乡亲们抵御外敌侵犯我们的家园,杀戮我们的家人,掠夺我们的财产。”
“你敢对着列祖列宗的面起誓你说的话?”刘谨钊脸色寒意未退。
“是的。我敢起誓,路氏占领南方,他们接下来就要攻打北方,中州地处九州之衢,路氏叛逆无论如何是绕不过中州之地进攻北方,中州首当其冲,我一路上回来忧心忡忡,就是很担心这个事情。”
刘谨钊脸上的寒意退散,佝偻的身材颓废地坐了下来,喃喃道,“难道这真是天意?”
“族长爷爷,您若不信,可以随时关注柳河镇商贾带来的消息,您到时候就知道该怎么决定。”
大街上幽幽传来打更人的打更声,已是子时二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