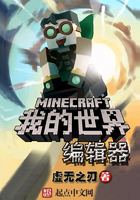魏僮是被悠远难辨的吟诵声吵醒的。
心想着昨天两位姑娘说的都是十分标准的北方官话,可这绵绵不绝的吟哦,他愣是一个完整的字词都识别不出来。
他伸着懒腰,想要睁开双眼看看是谁在扰人清梦,努力了几次后仍是一片漆黑。就像一盆冰水从头浇下,他呆呆地愣在原地。
“小公子,小公子,你醒了吗?”
“嗯。”隐约听到小奶猫叫一样的呼唤,魏僮呆滞的灵魂隔了半晌才想起来回答,“噢,小小姑娘,你……早上好!”
“嘻嘻,小公子你真有趣。身子还乏么?我给你带了桂花粥,今早刚做的,可甜!”
“谢谢姑娘,我是真饿了。”魏僮深吸一口气,缓了缓,才转头对着声音的方向微笑道。
“好嘞!小公子你等等,我,奴家这就伺候你吃粥!”小小甜甜地应了声,扶着魏僮靠在床围子上,又搬了个小几子到床上,侧坐着喂他吃粥。
“啊!张嘴!好吃么?”
从来没享受过此等待遇的魏某人有些不好意思:“嗯,嗯,好吃。小小姑娘,我自己来就好,我自己来,嘶……”
一边囫囵吞着被塞进嘴的粥,一边慌张地说着话,没有视觉辅助的魏僮显然低估了这等操作的难度系数,狠狠地咬到了舌头。
“该!小小,你过来。”魏僮这才知道师师姑娘也在这里,“我家笨丫头看来是伺候不了你这大少爷啊!”
“师师姐,小公子,小公子他……唉,是我,奴家太笨了。”
听得小小泫然欲泣的伤心话,魏僮赶紧开口解释:“不、不似仄样的,我从来,从来也不曾被人服饲过,我们那边,都似自己动擞,丰衣足嘶……”
魏僮一边说话,一边倒吸着冷气,舌头那是半点都不敢卷的。
“笑话,你这身皮囊,也敢说自食其力?”不曾想师师姑娘更加气急,“照你话说,你是能想起‘你们那边’的事了呵。既然没摔坏脑子,就别整天装失忆扮可怜!小小,粥给他放那儿,咱们走!”
“嗯,好……”小小的声音仍旧低落,轻轻拉起魏僮的手,说道,“小公子,来,这是粥碗,这是勺子,这边放了个小几子。你喝完粥就把碗放上面,奴家会来收拾的。”
“谢,谢谢小小菇凉。”魏僮含糊的答谢没得到回应,“哎,无妄兹灾啊。”
叹息了一声,魏僮摸索着拿起碗,舀了勺送进嘴里。粘稠的糯米和板栗泥包裹着酒香,桂花的甘甜在唇齿间慢慢晕开。
他不自觉咀嚼得更慢了,舌尖细细分辨着桂花和红豆,咽下的暖流迅速从胃遍及全身,整个身子活了过来。
感知着胃和身体的逐渐满足,魏僮鼻头有些发酸,他越发察觉到这世界的真实,便也对这真实的孤独越发地恐惧起来。
“梁发财,你个狗东西……可别死了啊……”
静静的脚步声传来,小猫一样的女孩子怕是又心软了,魏僮赶忙补救:“咳,小小姑娘,粥真好吃!刚刚,刚刚不好意思,惹你伤心了,对不住。”
小小似乎有些幽怨伤心,脚步声渐住,却没等来回应,魏僮又说道:“我,我不知道……”
话音未落,脚步声陡然如急雨。魏僮正自纠结着说道歉的话,猛地像是一把钝剑抽打过来,正击在他脆弱的喉头,包了半口没来得及咽下的粥混着口水从鼻腔里呛出来。
他的头被这股力量带着,狠狠地撞在身后的床架上,木质的雕纹小刀一样把后脑的皮肤刺了个鲜血淋漓。掐住咽喉的手掌如若铁铸,干燥的皮肤似乎要突破到他的喉管里,猛烈的窒息感超越了一切疼痛。
魏僮奋起全力挣扎,手里的瓷碗扔到了空处,四肢像炸毛的野猫一样发狂地抓挠,却只是徒劳地消耗着本就不多的体力。
掐住他喉管的人很有经验,侧身站着避开了所有可能的反击,另一只手握着他的前额,把他的头朝着床架用力且稳定地撞击。
一下,一下,一下。
木刺越扎越深,后颈密集的血管都在压迫和撞击中迸裂,颧骨到耳侧的皮肤火烧一样,根根暴起的青筋无比狰狞。
魏僮第一次这么清醒地感受到死亡的逼近。
一下,一下,一下。
他的意识在一次次机械般精准的撞击中濒临崩溃。
“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我就要死了?反抗的机会呢?为什么啊?是谁……我连最后看一眼这个……这个操蛋世界的机会都没有么?”
“为什么……非要是我?”
或许是回光返照的加持,或许是充血挤压的错觉,魏僮恍惚间好像看到了来袭者的身型——一个身高颀长的男人,双手分别握住他的前额和喉管,躬身站在他左前方,头部黑乎乎的影子似乎是在确认他的死状,离他的鼻尖只有一拳的距离。
他心中发着狠,鼓起所有残留的力气,用左手朝幻觉黑影的太阳穴打去。
“砰!”
肉体相撞的闷声和左手断裂一样的痛感,都在宣告着徒劳的最后一击打到了实处。魏僮咧咧嘴,心中发苦。
“嘿,还是给我打中一……”
“砰!”这是魏僮的后脑勺再次狠狠地撞上木板的声音——弥留之际的击打,哪怕是用尽全力,哪怕是直击要害,显然——并不能起到丝毫作用。
行凶的男子甚至没有一秒的迟疑,他握住魏僮前额的右手微微下移,捏住太阳穴,就待两手一同发力,拧断眼前这个富家公子稚嫩的脖子。
“咻——哧!”
尖锐的破风声响起时,一块瓷片已经深深扎进了刺客的颈窝。他的头被带动着猛地前倾,双手却顺势一撑,向右侧一个鹞子翻身,竟头也不回地跳窗跑了。
“休走!”小小的怒斥这才传来。
刺客走得太过果决,她偷袭成功,占尽先手,却还是眼睁睁看贼人逃遁。
她垫步上前,就想跟着从窗口跳下追击,余光却瞥到一旁瘫软在床、烂布口袋似的魏僮,吓了一大跳——刚刚离得远,她只看到歹人掐着小公子的脖子,不成想下手如此之重——魏僮的眼、耳、鼻、口,都洇出暗红的血迹,头发被汗和血拧成一绺一绺,眼泪鼻涕糊了一脸,凄惨得不成样子。
“小公子!小公子!你、你醒醒!”
小小动也不敢动,摇也不敢摇,半抱半揽着魏僮,英姿飒爽的女卫瞬间回归手足无措的小哭包。
“咳……咳咳,小、小小?”魏僮贪婪地吸了一大口空气,舌根处的铁锈腥甜而恶心。
“欸!小公子,你醒了?”熟悉而陌生的呼唤将魏僮从昏厥中惊醒,昏迷前经历的残酷袭杀仍在脑海里潆洄,他的手脚猛地抽搐,想要弹起的身子却只是动作了小半,便被无边的痛楚和乏力按在了原处。
一只温暖柔软的手轻轻贴在了他的额头上。“小公子,别怕,没事了!师师姐在这,没事的,没事的……”
耳边细声细气的安抚并没能让魏僮有半点心安,他脑门上冷汗渐起,用尽最大的力气沙哑地喊出:“小小……小小,你,是你么?”
“欸?欸?小公子,公子认识我?我……”
“小小,别和我开玩笑啊!贼人,那个袭击我的贼人在哪里?”
“什么……什么贼人?小公子,你,你吓到我了……”小小有些手足无措,“公子,我,我不知道你说的贼人是谁。你躺、躺好啊,大夫说了,你的眼睛、眼睛要好好将息,现在都渗血了,我、我,大夫只说了要喝药的,我、我去给你端药!”
小小慌乱地小声念叨着魏僮熟悉的台词,他的背后已经被冷汗浸湿,从未有过的危机感芒刺在背,他用两只手的大拇指狠狠地掐住食指,来不及深吸一口气,忙不迭地阻止正待逃离的小女孩。
“姑娘,小小姑娘。你别怕,我刚刚,刚刚做噩梦了。我以为,你是我家妹子,我有个和你一般大的妹妹,小名也叫小小。”魏僮闭着眼说着瞎话,默默祈祷着接触不多的小小如他想象般单纯天真。
“欸!小公子你有个妹妹?她和小小同名么?”
“嗯,嗯,我家妹妹姓魏,‘晓’是‘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晓,你看多巧。”
“嘿嘿,是挺巧的,我,我叫苏晓,‘晓’是‘断肠明月霜天晓’的晓,师师姐给我取的名字!”小小一脸傻笑,旋即又担心起来,“小公子,你缓点说话,当心嗓子。我伺候你喝药好不好?大夫说你喝了药,多多休养两天,一切都会好的。”
“没事,不急。”魏僮不放心小姑娘就这样离开,再醒来一次的他还记得“之前”小小的仗义出手,更记得喉咙被掐到快断裂的绝望和窒息。
不管表演得多拙劣,他也必须把眼前小姑娘的迷惑糊弄过去,“清清白白”地做一个被救的富家公子,悄然融入角色不被怀疑。
“小小姑娘,在下姓魏,单名僮,还无表字。伤残之身不便行礼,拜谢你的救命之恩了!”
魏僮挣扎着拱手,引得小小一阵惊呼:“别,别别!公子……魏公子,我,不是我救的,不是,是我和师师姐……是师师姐救的公子,公子给奴、奴家行礼,使不得,使不得……”
“小小姑娘客气了,僮方才虽昏厥,但从楼上摔下时意识尚存,耳听得姑娘仗义执言在下才能苟全性命,姑娘当得僮一拜!”
小小脸色通红,小侍女似乎从未遇到这样的情况,呆呆地看着魏僮勉力行完大礼,才声如蚊蚋:“魏公子,你太客气了,我,奴家愧、愧谢。”
“小小姑娘叫我的姓名就好,家父母早亡,在下和舍妹相依为命,称不得公子。”魏僮给自己补充着人设。
“嗯……嗯,那,那我叫你僮哥儿好了,僮哥儿,你,你也叫我小小就好。”小小无从知晓魏僮心里的弯弯绕,有些扭捏有些纠结地答应了魏僮,“僮哥儿,我去给你热药,等师师姐演出结束,我再和师师姐一道来看你,你先歇会儿吧。”
“好的,好的。麻烦你了,小小!等师师大家到了,僮再向大家拜谢救命之恩!”魏僮哑着嗓子表演着自矜洒脱的样子。
“嗯。”小小低着头,也不知道在答应谁,一溜烟跑走了。
房间里陡然安静了下来,魏僮仍能感受到全身每个细胞里传出的痛苦呻吟,却不敢像上次那样任性地晕厥过去。
他提起十二分精神戒备着可能钻出来取他性命的歹人,就算是刚刚和女孩的对话,他也没有完全排除一切都是“小小”的表演,甚至一群人看耍猴一样看着他拙劣演出的可能——他想活。
黑暗中,魏僮没办法准确把握时间的流逝,他只能估摸着捱过了半个小时。这时候他终于觉察到,他此次醒来和之前那次不同,除了依旧目盲,他的状态好的出奇。
没有窒息,没有虚弱,没有疼痛,好像换了副身子骨似的。
他数着自己的脉搏,耐心地等着,直到月上梢头,直到人声渐歇,直到万籁俱寂。
他慢慢撑起快要僵掉的身子,靠在床架上,蜷缩成一团。
他不知道屋子里有没有其他人看着,可他真的已经到极限了,生理或心理意义上都是。
蜷缩的动作他做得很是吃力,足足花了三十个呼吸的工夫,他终于抱住了没能撑得太高的膝盖,把头重重埋了进去。
魏僮,在这一刻,终于成为了一只蜗牛,一只没壳的蜗牛。
“断肠明月霜天晓,么?”
“真是。江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