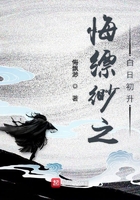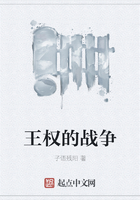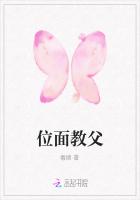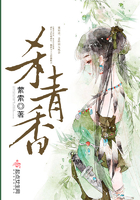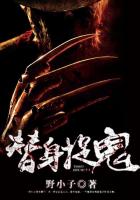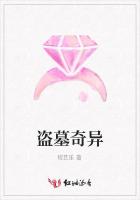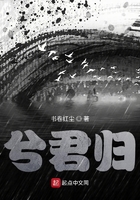迷茫的青春
转眼间,刘季已到成年,长得鼻梁高挺,前额隆起,稀疏的胡须随风舞动,按照看相先生的说法,这是龙的相貌。(具体形象可参考年画中的龙)。
刘季喜欢交朋结友,做事不拘小节,为人仁爱豁达,和当年的信陵君有很多相似之处。
小时候他就听父母讲过自己奇异的出身,加上在书院几年深受英雄主义教育毒害,他相信自己将来一定要干一番大事业。
刘季很少帮家里干农活,不是不能干,而是不想干。他不想成为农民,走回父亲的老路。但自己的家世比起含着金钥匙出身的人,又差了几十条长安街,他必须面对现实。
自古以来,底层人民要想改变阶层,要面对四重障碍。
一,解决最基本的吃饭问题。
二,面对周围庸俗的眼光,要坚持自我,不忘初心;
三,抓住有限的机会,突围出去;
四,要有一点运气,逢凶化吉,活着撑到成功。
百分之九十的人在第三来临前,已经放弃了。
刘季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但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他在迷茫中渡过了他的青年。
他有两个爱好。
一个是喝酒,而且是很豪爽那种。他经常拿家里的钱请朋友在外面买醉,那杯中液体,似乎有种魔力,能让他很快拉近和别人的距离,忘记烦恼。
中阳里有两位妇人,叫王媪和武负,开了两家酒家,刘季经常去赊账饮酒,有时聚饮,有时独斟。说来奇怪,每次刘季去,买酒的人都会爆增,成交量是平日的好几倍。每当刘季喝成交量是醉了倒在店里头睡觉,两位老板娘都会看见刘季身上浮现金龙。到了年终结账,两人发现赚的钱比刘季赊的账还要多很多,干脆给刘季免单,欢迎他常来。
刘季第二个爱好是好色,有时会去某些娱乐场所消费,就是那种运动(你们懂的)。由于话题比较敏感,不多说。要跟大家说明的是,当时的人们,性观念比较自由的,男欢女爱,嘿嘿咻咻也不是什么大不的话题。
那是一个真性情的时代,大家在今慢慢体会吧。
我们还可以推出一个重要结论,刘季同学的腰板是相当不错的,男人最重要的就是两个肾,没有旺盛的精力,以后肯定是干不了艰苦的革命工作滴。
刘煓也算中阳里有头脸的人物,现在年纪大了,大家都称他刘太公。
他对小儿子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样子十分反感。最气人的是,小儿子从来没把教诲和训斥当回事,那不争气的挫样,让他丢尽了脸,他真后悔当年生了这玩意。
刘煓自己清楚刘季不想干活儿的原因,但是作为一个地道的农民,他对儿子没信心:饱读诗书、武艺高强、口齿伶俐、文韬武略,这些词语,刘季一个都不沾边,就算打了一千千瓦的探照灯,浑身上下也找不出一技之长,谈理想?痴人说梦。
在他看来,当农民虽然辛苦,但也强过因改变而产生的痛苦。只要辛勤耕作就能保证衣食无忧,总比不务正业、有上顿没下顿强。况且在外闯荡,是要冒风险的,那些没闯出一丁点名堂就领了盒饭的例子他也见了不少。
他愿意相信,当年在水塘边看到的异像和刘季股上72个颗黑痣,不过是他的美好想象,像他们这种家庭,大富大贵根本遥不可及。
和刘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伯和刘仲两个哥哥——脚踏实地,吃苦耐劳,把田地打理得井井有条,让一家人吃穿不愁。
两位哥哥先后成了家,家里开始拥挤。加上连年战事,官府征发愈来愈紧,日子没以前宽裕了。
两位嫂子看到小叔子整天不务正业,坐吃山空,一有机会就含沙射影说些怨气话,老爷子听了十分难受。
刘煓干脆分了家,两个哥哥自立门户,刘季跟着自己,耳根子清净。
刘季不知趣,经常到两个哥哥家蹭吃蹭喝。哥哥们心善,不好意思拒绝,等刘季走后,夫妻上演全武行。
大哥刘伯突患急病,撒手人寰,剩下大嫂独自抚养幼子,生活艰难。
不知刘季是真缺心眼还是假没眼力,依然到大嫂家蹭饭,有时还带上几位兄弟。这样一来,大嫂更加厌恶。
一天中午,刘季又不打招呼带来几位朋友。
大嫂刚做完饭,远远听见刘季一行的说笑声,心里飚出一句脏话。
她看了下厨房四周,有了!她拿起一个空釜(类似于锅,陶制),用勺子使劲地刮,发出“嘎嘎嘎”的声响,好像要把釜壁上残留的汤羹一滴不剩刮到碗里。
朋友们刚进了门,听见厨房传来的声音,十分尴尬,自觉地转身离去。
看着朋友们离去,刘季十分不好意思,但也奇怪嫂子今天怎么吃这么早。他来到厨房,迎面撞见大嫂正在给小侄子盛粥,装了满满一大碗,再看釜里,还剩一大半,冒着欢腾的热气,香得让人口水直流。
大嫂见到刘季,脸色难看,给了一个白眼,一言不发。
刘季感到两眼发黑,想说但不出一句话来。他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定定看着大嫂几眼,转身就走,从此再没有踏进这家大门。
多年以后,他依然记得这一饭之“辱”,等到他登上高位,也没忘加倍回敬大嫂。
闯荡
刘季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羞辱,好多天心里都像锥心的痛。
他恨,恨大嫂,但最后他发现,最该恨的还是自己。
别人为什么这样对自己?自己总是有点逼数的。
二嫂不也一样吗?父母不也一样吗?
他可不想再看人眼色吃饭,但又能够干什么呢?巴掌大的中阳里,除了当农民还是农民。
就在这时,魏国传来了一个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