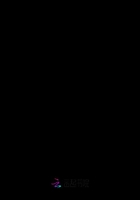天下初定的三年来,政通人和,舒哲虽为皇后,前几年也刻意学习过如何管理一家一室,但毕竟不是本行,总是事倍功半。反倒是位居妃位的清悠,名门之后,曾为前朝贵女,对掌家管理之事倒是颇为上手,舒哲倒需要常常请教,一来二去,反倒熟悉起来。
入夜,和仪殿
躺在摇椅上看书的舒哲,听到外间有人说话。“听说近来皇后惫懒很多啊?”纪珩笑着半倒下来压在舒哲身上。“啊,断气了。陛下重新寻位皇后吧。”
“嗯,朕觉得清妃当真有母仪天下之风范。”说着拉起舒哲,舒哲头自然无力地垂着。纪珩笑着继续说,“皇后不反对,朕这就下旨了。”舒哲坐直,“那我不同意呢?”两人静静看了一会。“怎么了?我脸上有花。”
“嗯,最近气色确实好了。前几天太医院院正来跟请罪,说你这两月都不给他请脉,定是他哪里伺候不周到。我就问他,那皇后可有什么不妥之表象?他说不敢妄断,但观你气色倒是好了不少。”
“嗤。并不是针对他,这两次他来得都不巧,琮舒这几天玩疯了,时间有些倒了,总是过了午休时候才困,我就陪着她那么睡了。”
“嗯。听说,最近和清悠倒走得挺近。你把内宫六司六局的账目都推给她了。”
“我发现你变了。”舒哲眼里透着狡黠。
“变了?”纪珩摸摸下巴,“且听阿哲细细道来。”
“你变得细心,从前你放下东西就忘了,今天找不着那把短刀,明天忘了那本兵书。如今坐在前朝,内宫的一动一静都瞒不过你。”越说到后面声音越小。
“这么说来倒是啊。但是,也只对你的事情上心啊。”舒哲轻轻点了点头。纪珩却拉起了她的手,把她拉近身旁,“我知道你不喜欢这四方的宫城,等临儿再大些,能亲政了,我应当带着你回平城,或者去哪里都好。”舒哲反抽出手反身躺在纪珩怀里。
“我选择跟随你平天下,守江山,早料到有这么一天。我也尝试提前做些准备。但是,我发现自己真的不喜欢那些繁琐的礼节,不喜欢规矩打点;什么平衡六宫,恩威兼施。家大业大好难打理。”纪珩刚想说什么,舒哲伸手挡住他的唇,继续说到:“不过,是我自己选择留下来,选择了解另一种人生,选择呆在这里。”纪珩闻言倒一笑。
“你说我变了,我看你也变了。想想啊,怎么说呢?变得没那么端庄了,没有了初见时那种端庄娴静,倒越来截像琮舒了。”
“阿爹。”说完两人一起笑起来,纪珩故作淡定道:“没大没小。”
世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从何时起开始变化,很难说清楚;可能从遇到那个人开始,环境变了,人也变了。
深夜,深巷偶尔传来几声犬吠,东京城郊城隍庙。
“冥衣楼金部无痕。”
“冥衣楼木部无霜”
“冥衣楼水部无声”
“冥衣楼火部无影”
“冥衣楼土部无心”五人抱拳,齐齐向一女子行李,“参见楼主。”“起吧。此番前来有两件事,一是带来公主的关切,看看你们过得好不好?二是通知你们细微处可以着手了。”当初要众人四散,一为保性命二也为壮大队伍伺机而动。但三年来,眼看战后平原两国迅速恢复与发展,一尘有些坐不住,怕再这么下去,会更难办。便拟定了一个计划,如今要来一步步施展了。“这是你们东京五部的任务,收好了。回去多加小心,别被人瞧见了。”
清晨,仪和殿
“公主,陛下和娘娘还没起呢?”门口的侍女向琮舒福了福身说到。琮舒如今被封永乐公主,不愿住在自己的宫殿,就住在仪和殿偏殿。琮舒作了一个噤声的手势,蹑手蹑脚推开门,慢慢踱至床边,看着手拉手睡觉的父母后又悄悄退出来。问门口的内侍:“阿爹今天不用上朝吗?”
“回公主的话,陛下今日沐休。”
“哦。阿爹阿娘醒了,替我回禀一声,我去找哥哥了。”离开仪和殿步行来到纪临的雨泽殿,看到纪临已经在树下读书。“哥哥。”纪临温柔地笑了,跑过来,蹲下身子与琮舒持平。“这么早舒儿怎么来?吃过早饭了吗?”
“没有,阿爹阿娘还在睡觉,我想听哥哥昨天讲的史鉴。”
“好,那我们边吃饭边说可好。”一大一小身影进了内殿,俨然一副兄友妹恭的样子。
饭过半时,上来一道点心,琮舒刚咬了一口,就打断了纪临的话。“哥哥,这糕点真好听,快尝尝。”小手伸得老长还差那么一点,纪临低下头咬了一口。“嗯,果然清爽。”看到那边琮舒已经吃第二块了。“四儿,今日这糕点是谁做的?”纪临向一旁的内侍问道。
“回殿下的话,这道糕点不是小厨房做的,是司膳局送来的。可要下官去把人叫来。”
“不必,你去打听叫什么就好。”后来送琮舒回仪和殿,便和舒哲提起那个叫暮雪的女孩儿,刚来不久的小宫女,很会做些花式点心。从此琮舒身旁便多了一个叫暮雪的陪伴。
静渊殿,清悠刚起身。贴身女官凝霜为其绾发,凝霜是她还是周朝贵女时认识的一位诗友,后来新朝招进第一批宫女就有她。清悠感念那份才情,便安排在自己身边。三年来,都是凝霜陪她渡过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
凝霜不经意叹了一声。“唉”清悠疑惑,开口询问:“怎么了?一早唉声叹气的。”
“没什么。”
“有事情就说吧,这欲语还休的样子真让人着急。”
“娘娘,凝霜昨夜一夜未睡,盘算了下。娘娘应该为自己打算一下了,北江王虽少年封王也是长子,可是陛下迟迟未册立太子……”
“住口。”还未说完就被清悠呵斥住。“什么册立太子,册立谁,那是陛下考虑的事情,何必我们操心。”
“娘娘虽为主子,但说一句大不敬的话,凝霜内心却把娘娘当成妹妹。中宫盛宠不衰,陛下是等一个嫡子。皇后娘娘是因为产永乐公主时亏了身子,但将来有一天养好了……娘娘,陛下先认识的您啊。”情急之下,竟往前挪了挪,拉起了清悠的双手。
清悠推开凝霜的手站起来。“你今日莫不是魔怔了。平日里循规蹈矩,今日这一大早疯言疯语的。你出去吧,让其他人进来伺候。”凝霜向清悠行礼之后退下。清悠看着铜镜的自己,是啊,曾经你是只属于我的,可是……可是那时的我亲手推开了你。一段往事浮上心头。
清悠才女之名一直在东京城传播,多少慕名而来的青年才俊都被清楠拒之门外。她的父亲清楠常常提醒她,平城有一个叫纪珩的人,是她的夫君。小时候倒没有什么,渐渐大了,清悠渐渐不服气,为什么她这么好的家世才学要嫁给一个一无所有的小城守将之后。在一次世家晏会上,她认识了周朝二皇子,自那之后,两人常有书信联络联诗作对。记不清哪一天了,清悠出门采买首饰,遇上大雨,而二皇子刚好路过,便送她回府。在临下车时,二皇子说他喜欢她,问她是否愿意嫁给他。两人那时是郎情妾意,清悠也想着,若能嫁给皇子,纪珩那混小子难不成还敢抢亲。那晚她就跟父亲摊牌,说自己心有他属,不想嫁给纪珩。但当清楠知道自己的女儿喜欢的是皇子后,腾地一下子站起来。“清悠,若是其他世家公子,只要身家清白品行端正,我便豁出这老脸,拒了平城的婚事。但,皇家向来就是是非之地……总之,爹爹不会同意你嫁给二皇子。”
“不同意也晚了,二皇子明天就会向皇上请婚,指我为皇子妃。难道纪叔叔还敢来替儿子抢亲不成。”
“糊涂啊!”随即回房了。那是清悠长到十五岁第一次与父亲不欢而散。那天晚上父女皆一夜未眠。一大早清楠便上朝了,不过这次上朝目的就是辞官。说自己精力不济,且小女已经长大,故乡有一桩娃娃亲需要她去履行。二皇子不敢置信地看着远去的清楠,暗念一句,老朽木。清悠知道父亲要辞官还乡之后十分生气,“清悠,二皇子并不真的喜欢。若是真的喜欢你,今天朝堂上就该为你们争取一次。但他没有。”
“他必是认为我变心了,心灰意冷了。还开口丢人现眼吗?”
“若今天是你听说了二皇子即将成婚的消息,你会认为他已经变心了吗?”
“我……”清悠一时语塞。
“二皇子与东宫势成水火,定要争个高下。二皇子常年外放,兵权能臣不乏。但东京城不比地方,有时候清流文官的一句胜过那些能臣百倍,这叫四两拨千斤。他刚回京不久,没有自己的言官,却已经吃了太子那边许多暗亏。爹这些年一直保持中立,且有了些许名望,他明里暗里暗示了我儿次,但爹爹都视而不见。这次他是想借机……”
“拉拢爹爹。爹,他对我是真心的,他……”清悠自己住了口,真心?世上最易伪装最难看清的就是人心吧。
“清悠,你是爹爹的女儿。父母之爱子,必为之计深远,爹爹怎能不为你考虑?”最后清悠跟着父亲回了平城。二皇子没有出现,但是听说常常与清楠政见的言官参了太子一本荒淫无度。
纪珩确实无趣,总有一丝呆气。平城的东西对清悠来讲都太无趣了,远不及***闹繁华。两人相敬如宾地过着日子。后来有一次去上香时,遇到许久未见的二皇子,正在诧异二皇子的出现时。清悠便被拥入一个熟悉的怀抱。两人在茶楼聊起来。二皇子说当时本想出宫阻拦她,但被母妃拦下,说他为了一个女子如此,如何能成事。这次是偷偷跑出来找她的,怎知路上遇到太子一党的追杀,受伤跌入一处深渊,顺着水流一直漂到一处谷底。向上走,才发现他来到了平城。
当时清悠感动不已。还为自己已经委身他人食言而懊悔。二皇子并没有怪她。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清悠白天总是借口各种理由出门,还将自已陪嫁田庄地契拿出去当了钱,交给二皇子。二皇子说他不想再坐以待毙,想要拼一次。清悠就自愿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为他助力。二皇子再三推托之后收下了,让清悠等他。
在二皇子离开平城的一个月后,清楠发现家中财产对不上,清悠才交待了一切。彼时,平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考验。清楠气愤难当,扬言要杀了清悠以证清明,再自杀向夫人请罪。清悠横着脖子让父亲下手,还说自己已经怀上了二皇子的孩子,让父亲一并结果这个外孙。
清楠最终下不了手,但他始终坚持不能欺骗纪珩。便主张清悠与纪珩各离,带着清悠离开平城。出了平城,清悠才隐隐有种被骗的感觉,东京城数月前已经沦陷,那追杀二皇子可能就不是太子了,而是……乱世之中,能勉强保命的,大抵只有钱了。
清悠父女去一处不知名地方,清楠开设一个学堂,清悠做些刺绣,虽乱世生计艰难但也不愁吃穿。在纪临七岁时,父亲去世,当地的恶霸看上了清悠,偏要用强。清悠在邻居的帮助下连夜逃出来,举目无亲的绝望之际,她想到了纪珩了,那个时候,她觉得也只有纪珩能够帮助她了。她费尽心力终于找到了纪珩,一路上听到不少关于纪珩的事情。为了纪临有一个安稳的环境,便对七岁的孩子说是去找爹。说过往跟他讲的爹爹已经不在都是哄他的。是她怕爹爹将他从她身边抢走,如今相通了,要让他们父子相认。她撒谎称纪临是纪珩的孩子,还在路上就准备好了明矾,在滴血认亲的水中做了手脚,终是有了安身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