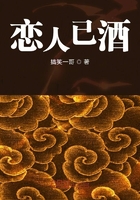闫少卿回头一看竟是穆孝先,立即大吃一惊,便问穆孝先怎么来了。
穆孝先说自己是去东北办事路过这里,想起了你,就到你这里讨杯热酒喝。说完他看了看闫少卿身旁的水井,眼珠儿转了两圈后开口问道:“大半夜天寒地冻的,你站在井边做什么,莫不是有什么想不开的事情?”
闫少卿长叹一声,将这一年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了穆孝先,而后又说若不是因为自己好赌,也不会中了屈三儿的圈套,将祖业败了个精光,落了个败家的骂名,这都是自己咎由自取,自作自受,自己觉得愧对父母,愧对祖先,所以无颜再活在世上,这便决定投井自尽了此一生。
穆孝先听罢连连摇头,直说严少卿错的离谱。他告诉严少卿:“正所谓不孝有三,生不敬顺,一不孝也、死不礼葬,二不孝也、无后绝祀,三不孝也。首先当初我明明告诉你将要大祸临头,可你却屈从于父母长辈的意思没有离开这里,以至于他们枉送了性命,此为只顺不敬一不孝也。其次你若死了,你父母的坟墓谁来管,谁来焚香祭拜,谁来除草添土,将来岂不成了荒坟野冢,此为死不礼葬二不孝也。再次你现在连个子嗣都没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若你现在一死便是无后绝祀,此三不孝也。你现在如此轻贱自己的性命,难道是想做一个大逆不孝的人吗?”
闫少卿闻言羞愧难当,直说自己一时糊涂,若不是老神仙一语点醒,险些做下蠢事。
穆孝先闻言哈哈大笑,拉起闫少卿的手说:“这就对了嘛,古语有言,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走走走,外边天寒地冻,咱们屋里说话。”
两人进屋,穆孝先抬头看了看屋顶上的大窟窿,说:“这么大的窟窿,晚上睡在这里还不得冻死。”说完把手一挥,凭空立即带起一阵强风,卷起屋里的雪花尽数飞出屋外,然后又往上一抬手,原本斜躺在地上的房梁立即缓缓升起,重新回到原位,同时散落在四周的垫草瓦片也漂浮起来,纷纷落在了屋顶之上。眨眼的工夫,房顶完好如初,直看的闫少卿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做完这一切,穆孝先又问闫少卿吃没吃饭,闫少卿摇了摇头,穆孝先立即将翻倒在地的桌椅扶正,单手轻轻一挥,尽扫其上灰尘。然后快步走出门外,轻轻一跃站上房顶,手搭凉棚举目远眺。片刻后他哈哈一笑,冲着远方招了招手,然后跃下屋顶回到屋中,拉着闫少卿桌边落座,对闫少卿笑道:“稍等片刻,菜马上就来。”
果然如他所言,不出片刻,从门外飞进来十几只盘子,呈梅花状依次落在桌上,每只盘子里都盛着美味佳肴。而后穆孝先又从怀里摸出一把酒壶置于门口,小声念了几句口诀后对着酒壶拜了三拜,然后掀开酒壶轻轻一闻,此刻壶中散出阵阵酒香。
穆孝先给闫少卿斟满酒,又神奇的从桌腿上扯出一双筷子摆到严少卿面前,而后笑着说:“来,先吃点东西,吃饱喝足才好再做打算。”
哪知道闫少卿忽然起身后退两步,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对穆孝先说道:“老神仙你本事通天,我有一事想请老神仙为我做主。虽说是我好赌,但要不是屈三儿那家伙设计害我,我也不会落得如此凄惨的境地。我心里不服,想请老神仙帮我出一口恶气,惩治了那个挨千刀的屈三儿,他若不死,实难泄我心头之恨。”
穆孝先摇了摇头说:“此话差矣,依我看此中过错你与屈三儿各占一半,不分伯仲。正因为你好赌,所以屈三儿才会盯上你,你若不好赌,那屈三儿怎会有机会加害于你。所以你是因,他是果,没有因哪有果,俗话说追根溯源,源头在你身上,又怎么怨的了别人。”
闫少卿见穆孝先不答应,心中不免失落,叹道:“本以为老神仙为人仗义,明辨是非,可以替我主持公道,可如今看来……,唉,罢了罢了,既然老神仙不愿意给我出头,那我也不强人所难,就如老神仙所言,自己种下的因,这苦果就要自己吞下。方才我说话有些失礼,还望老神仙不要介意,就当我刚才什么都没说。”说完摇头叹息不已。
见他这幅摸样,穆孝先咯咯一笑,上前拉起他说:“你先不要唉声叹气,我之所以不给你主持公道,是因为用不着我出头,将来自然会有人惩治狗三儿。”
闫少卿闻言半信半疑,只当是穆孝先在宽慰自己,于是说道:“此话可是当真?老神仙莫要安慰于我。”
穆孝先说:“当然是真,正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你且看着,不出三年那屈三儿必遭报应。再者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虽然败光了家业,但也并不一定是坏事,而且依我看,不但不是坏事,反而却是一件好事。”
“好事!?”闫少卿听得有些糊涂,于是便问:“老神仙所言何意,可否以详情告之。”
穆孝先摇了摇头说:“说不得说不得,此乃天机,泄露天机是要遭天谴的。”
闫少卿见穆孝先不肯说,只好将此事暂且放下。他举杯对穆孝先说:“我如今流离失所身无分文,承蒙老神仙不弃,以礼待之,在下感激不尽。这一杯就当是我借花献佛敬老神仙,晚辈先干为敬。”说完一杯饮下,口中虽酒香四溢,心中却苦涩异常。
放下酒杯闫少卿沉吟半晌,而后说道:“老神仙,我……我还有一事相求,还望老神仙念在旧情的份儿上,一定要答应我。”
穆孝先笑眯眯地看着闫少卿,眼中洞若深潭,似是已经猜到了他想说什么,微微点了点头。
闫少卿说:“我如今瘸了一条腿,庄稼活是干不了,再加上又无一技之长,往后的日子实在不知该怎么过,又去何处讨一口饭吃,还望老神仙救人救到底,给在下指条明路。”
穆孝先说:“此事我早已经考虑到了。”他从身上摸出一只小布包,打开放在桌上。闫少卿抬眼看去,小布包里是白花花的银元,少说也是二三十块。
穆孝先指着银元说:“这是去年临别之时你赠我的盘缠,我原封未动,现今物归原主。”
闫少卿愣了一下,而后连忙说道:“这怎么行,送出去的东西哪有收回来的道理。”
穆孝先说:“怎么不行,当初你既然送了我,那就是我的东西,现如今我再送给你,又有什么不妥的呢。”
闫少卿见穆孝先执意要给,又加上自己的确急需用钱,也就不再推辞,收下了钱。
穆孝先说:“虽然钱不多,但只要你省吃俭用,还是勉强够两年的用度。不过你也不能坐吃山空,这样吧,我这里有一本医书,其上不仅记载了寻常病灶的医治方法,还有几十个专治疑难杂症的奇术偏方,你且拿去好好钻研,以后便可以此为生。”
闫少卿颤抖着双手接过医书,而后起身再次跪倒在地:“多谢老神仙,老神仙对我有再造之恩,此情此恩我穆少卿没齿难忘。老神仙,我……我给你磕头了。”
穆孝先急忙再次拉起闫少卿,让他莫要多礼,若真想谢,那便陪我痛饮一番。
两人一直饮酒到深夜,闫少卿不胜酒力,半途便趴在桌上沉沉睡去,等转过天来鸡鸣三遍才酒醒过来,此时再找穆孝先,却早已经不见了踪影。
……
……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一年,这一年来闫少卿深居浅出,刻苦钻研穆孝先留下来的医书,渐渐小有所成,其间还治愈了几个疑难杂症的患者,慢慢有了一点小名气,找他看病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又过了半年,闫少卿家几乎每天都有人上门问诊,闫少卿索性就在村口租了一个小门脸,正式开张做起了大夫。
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闭幕后,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拉开了帷幕。转过年来的秋天,村里来了一个的土改工作队,把村里唯一的地主给抓了起来,那地主便是屈三儿。自那之后一连三个月,隔三差五就在村里的麦场上开大会批斗屈三儿。
反观闫少卿,不仅没有挨斗,反而因为大夫的身份,受到了村民的爱戴,又因为身有残疾,被工作队定为了困难户,享受额外的照顾。直到此时他才恍然大悟,明白了薛笑仙说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是什么意思。
因为屈三儿以前坏事做绝,所以每次批斗会上都会有村民痛诉他的恶行,一来二去,他便成了重点斗争的对象。渐渐地,不管是本村的批斗会还是邻村的批斗会,甚至是县里的批斗会都少不了屈三儿的身影。每次开批斗会,只要闫少卿有时间那是必去,当他看到主席台上屈三儿带着高帽被批斗的样子,心里说不出的解恨。
转年开春,天气乍暖还寒,有一天深夜工作队的黄队长领着两个同志敲开了闫少卿的家门,将他请到了村委会旁的大院。在一间四处漏风的茅草屋里,闫少卿见到了气若游丝的屈三儿。屈三儿此时已经人不人鬼不鬼,瘦的只剩下了一把骨头。
屈三儿见穆少卿来到,立即恶狠狠的瞪向他,目光中满是怨毒,但却夹杂着深深的懊悔。
闫少卿问怎么回事,工作队的黄队长义正言辞的说:“屈三儿这个反动恶霸企图逃避人民的制裁,半夜偷偷喝了卤水,想要自杀。我们怎么可以让他的邪恶计划得逞,所以请闫大夫一定救活他,让他接受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正义的审判。”
黄队长走后,屈三儿不知哪来的力气,一把拉住了闫少卿的手说道:“求你了,别救我,你不是恨死我了吗,你不是做梦都盼着我死吗,别救我,让我死。”
闫少卿摇了摇头,冷笑道:“救死扶伤是大夫的本份,你现在命在旦夕,我怎么能坐视不管呢,你放心,有我在你死不了。”说完甩开屈三儿的手,而后硬生生掰开他的嘴,将一包药面子灌了下去。
经过闫少卿医治,屈三儿又活了过来,三个月后,他被工作队押去了省城,自此闫少卿就再没有见过他,有人说他被押去了东北劳动改造,也有人说他逃跑了,还有人说他畏罪自杀了,总之众说纷纭,至于他后来到底怎么样了,谁也说不清楚。
那年初夏,闫少卿被安排到了村里的卫生所工作,他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多次受到了上级的表扬。时间一晃又过了半年,冬至后的一天上午,他坐车去县城办事,刚出客车站就看见不远处有一个熟悉的身影朝他走来。
闫少卿顿时惊喜交加,急忙迎上前去,一把拉住了穆孝先的手问道:“老神仙,您这两年可好?”
穆孝先笑道:“我能吃能喝,好的很呢,倒是你怎么样,这两年过得如何啊?”
“托您的福,很好,很好……”穆少卿喜出望外,一连说了七八个很好,而后迫不及待的把这两年来发生的事情,包括自己如何开的医馆,屈三儿又是如何挨的斗,最后自己又如何去了卫生所工作一五一十的告诉了穆孝先。
两人攀谈了好长时间,闫少卿见已是晌午,便请穆孝先吃饭。穆孝先也不推辞,满口答应,于是两人便一同来到了县里的招待所。闫少卿点了八个菜,还特意用粮票换二斤酒。两人落座后,闫少卿边给穆孝先倒酒边问道:“老神仙,你这次是去哪里办事啊?”
穆孝先笑道:“非是去哪里办事,我这次是专程给你道喜来了。”
闫少卿闻言愣了一下:“道喜!我怎么不知道,喜从何来?”
穆孝先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