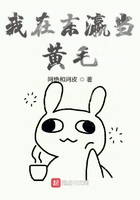在低矮的民房间穿梭着,秦飞将头上戴的斗笠拉低,觉得刚才实在是太大意了。
他是被主子派出来探听消息的,本以为听个大概就可以走人,没想到边军进了酒馆带来确凿消息。右玉城民众思维奇诡、口舌便利,一听之下他居然听住了,一时忘了掩饰,被边军注意到,不得不离开,以免惹出事端。
秦飞想着,抬头望了下天色,秋日天短,他在外转悠了大半日,已是日薄西山,不由有些担心主子一人独处会不会出事……要说也不算独处,与他同处一室的还有个半死不活的丫头。回想了一下那个丫头的武力值,秦飞决定还是回去吧,他怕回去晚了那丫头醒了,自家主子的身子骨禁不住她折腾。
做了决定,秦飞脚下一转,从八井大街拐上食宝街,快走了一盏茶的工夫,见到麻油胡同口了,他沿着破裂的青石板路走到十字路口,街边的店铺已经开始挂灯笼了,暖黄的光在天色尚亮的下午还不明显。秦飞左右张望下,远处还有不少的巡逻兵士,他所处的位置有许多木屋,这一带算是平民聚集区,稍微有点权势或者有钱的都住到城南去了,毕竟如果夔国打过来,肯定是从北边入城。
他看到不远处有兵士在来回巡逻,挨家挨户敲门问询,不过态度比城南那边要好上许多。街上稀稀落落还有几个行人,穿粗布衣服,行色匆匆,街边摆摊的已经没了,那些有门脸的店铺,也都上了一半的门板,有可能一整天都没开过张。
秦飞确定没人注意到他,穿过十字路口,走进麻油巷子,麻油巷子之所以叫这个名儿,很大原因是巷子里的店铺几乎都是卖麻油的,此刻巷子里没有行人,芝麻的香气飘在空气中,家家户户几乎都有榨油机,只有巷子口左手边第六家是个点心铺子,铺子门口挂着面鱼旗,上书盛香苑。小小的档口后摆着各色北地的点心,槽子糕、白皮儿八件跟核桃酥满满当当香气四溢。
秦飞路过档口,正要去推斜对面的院门,手忽然顿住 。
他微微侧头,眼角余光瞟向点心铺。
他刚刚……视线里好像掠过了什么违和的东西。
猛地转身,他几步跨到巷子左边,站到点心铺门口。
盛香苑点心铺的门脸挤在众多麻油摊之间显得格外不起眼,档口三尺见方,隔开店家和买主,档口旁边还开了一扇窄门,方便每日关窗收摊后店家进出。
秦飞说不上过目不忘,但也还记得昨日他带着主子和那丫头疾风一样卷进巷子时,匆匆一瞥间这档口后面站着的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妇。但此刻,秦飞皱着眉头,与档口后那十六七岁的圆脸姑娘大眼瞪小眼。
秦飞是战场上下来的,沉下脸时一身杀气根本收敛不住,再加上他脸上的那道疤,简直能止小儿夜啼。
圆脸姑娘在秦飞的注视下战战兢兢地立着,随着时间推移,脸色由红润变得苍白,不大的眼睛里渐渐弥漫起雾气,但还是强撑着半步不退,她双手在身前紧紧绞着,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大、大哥,您要点什么?”说话的时候,姑娘的嘴唇一开一合的,露出左边的一颗小虎牙。
秦飞蹙眉,他身量极高,微微弯下 身子:“你身后那是什么?”
天色已经暗了,档口内光线昏暗,圆脸姑娘身后的一片阴影里,有一个黑色的轮廓。
“啊?”圆脸姑娘一慌,往后错了半步,“没什么……您、您要是不买东西就离开吧,别挡在这里。”
秦飞愈发怀疑起来。他本来就不赞同主子来这里,进了右玉城以后简直步步危机,秦飞守在暗处,担心得觉都睡不好。被保护的人身娇体贵,还特别没有自觉,秦飞觉得头发都要愁白了。
这样高度神经紧绷着好几天,秦飞此刻不耐烦再废话,单手撑着档口,直接翻了进去!
“啊——”圆脸姑娘吓得还没喊出半声,就被秦飞一指点中哑穴,消了声。
周围邻近的店家听到点动静,探出头来的时候,巷子里已经恢复了寂静。
秦飞翻进档口刚制住圆脸姑娘,身后突然有风声袭来,他迅速回身,单手就将身后偷袭的人双手全扣住了,拎到身前。
偷袭之人是名少年,只有十二三岁,眉眼艳丽,颜如舜华,但身着衣服一片黑灰,已经看不出原本的颜色了。秦飞单手轻松将他的双腕攥得死劲,感觉自己再使点力气,就能轻松将这个少年的双腕捏折。
待他看清少年的样貌,不由诧异:“王赫?”
“放开我!”躲在档口里的正是昨夜自春风得意楼逃出的王赫,此刻他被攥住了双手,持在手中的擀面杖因为耐不住疼痛掉落地上,他咬着牙拼命挣扎,双腿蹬踹着,想将秦飞铁钳般的大掌甩开。
一旁的圆脸姑娘是跟着一起逃出的红衫,此时自一旁强忍着恐惧扑过来,因为声音被禁了,只能张着嘴无声大喊,双手死死勾住秦飞擒住王赫的右胳膊。
“能跑到这里来,算你们本事。”秦飞根本不在意这两人的挣扎,武力相差太悬殊,他抬起左手一人一掌,全都打晕了事。
将王赫扛到肩上,红衫夹在腋下,秦飞往铺子深处走去,找到被吓晕的老妇,确认没有生命危险后,将她放到椅子上,衣襟处塞了枚金叶子,随后带着两个人从窄门离开,翻出档口后迅速闪进了点心铺斜对面的院落。
院落的大门很窄,极不容易引起往来行人的注意,在门楹左上角雕着一朵小小的琼花。院中空地打扫得很干净,院子一角放着一个大缸,缸中养了两尾草鱼;另一边搭着藤架,夏日在下面乘凉一定相当惬意。房间只有两进,是青砖黑瓦的平顶房。
秦飞将手里抓着的两人先在院中找绳子捆好了,一人口中塞了一块布,确认他们一时半会醒不了,这才拎着他们往屋里去了。
穿过屋门,走进一个狭窄的正厅,正厅的高几上摆着个美人瓶,敷衍地插了几枝绢花,两旁靠墙放着一排棕色木椅。正厅很小,几步就走到通往卧室的左侧通道。秦飞穿过通道,走进光线昏暗的卧室。
卧室中还未点蜡烛,一名男子坐在床边,正侧目看着窗外的天色,手中捧着一只茶碗,热气袅袅,隔着水雾流芳,男子的面容朦胧缱绻,样貌如琼枝玉树,正是昨日保下封三宝的闻人,那静盛的气质,温文的神采,端的是风尘外物。
“主子。”秦飞将两人往地上一丢,没好气地走到桌前,“您这么闲,就不能点个蜡烛?”说着擦了下桌上放着的火石,将烛火点燃,屋中亮了起来。
融融暖光将屋中照亮,可以看到闻人身旁的那张床上,躺着一个人。
“阿飞。”闻人回眸,脸上带着浅淡的笑意,皮肤在夕阳和烛光的映照下如玉石般白皙。他轻轻呼出口气,“已经晚上啦……”语调里带着些困倦。
秦飞面无表情地走过去,将闻人手上的茶碗取出放到桌上,居高临下地凝视他,慢慢伸出手。
“呛啷”一声,走前为确保闻人安全而留下的匕首被拔了出来,闻人用一种诚惶诚恐的眼光看着雪亮的刃口。
秦飞脸上多少带出点不耐烦:“我去将院里的鱼杀了,晚上给您炖鱼汤。”
原来,到了闻人大爷的晚饭时间了。
“那个先不急。”闻人有些尴尬地轻咳,站起身,伸直胳膊用两根手指拎着被子将床上的人盖好,忧心忡忡地抬头,“阿飞啊,你说男女授受不亲,若我堂堂一个……帮她洗澡,是不是不太好?可她实在太臭了……”
床上躺着的显然是昨日被救下的封三宝,此刻少女依然昏迷着。
秦飞看了看床上的人,也有些头大。
昨日下午,秦飞隐在暗处,看着丰神如玉的闻人拖着半死不活的封三宝从城主府中走出,没走多久就吓坏了一帮人。许多胆小的看清封三宝的样子后,都吓得扭头就跑——少女纤细的手脚不自然地弯折着,头垂得很低,闻人昂贵的缂丝衣服上蹭满了少女的鲜血。
要不是秦飞在城主府内旁观了事情始末,别说路人,就连他都要怀疑自己跟着的主子是不是突然失心疯,对封三宝做了什么不轨之事。
眼见闻人身娇体贵,拖着封三宝走得呼哧带喘,几乎累瘫在路旁,秦飞等到他转过一个拐角避开众人的视线,迅速往街面上撒了几把金叶子,趁着众人都在低头抢钱,秦飞风一样掠过,一手一个,将两人拎走了。
等闻人被秦飞好生生地放到这间卧室的罗汉椅中时,闻人还没喘匀气,他瘫坐在桌边,看着秦飞将封三宝放到床上,忍不住对他挥了下拳:“这么喜欢看你家主子笑话是吧?非等我累吐了才来搭把手!”
秦飞看了眼闻人因剧烈活动而红润的面色:“是您让我别露面,以免被元庆帝和叶无尽发现的。”
“我是说了。”闻人珏恨铁不成钢,“那你刚才干嘛满街洒金子?钱多烧手是不是?!”不少人真以为凭空下金雨了,有几个人甚至为了抢金子打起来了。
“烧手啊。”秦飞翻了个白眼,右眼因为已瞎无法上翻,就变成左眼翻白右眼瞪直这么一个极其怪异可怖的表情,“那金叶子反正是别人给的,您帮他们省什么。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我这不是就帮人消灾了吗?”
闻人被自己的贴身侍卫气得好悬一口气上不来,指着他半天没说话。最终一摆手:“去,请个大夫来,小姑娘的手脚再晚治,就要受二茬罪了。”
秦飞犹豫下:“不好吧,这里不能让人知道,回头大夫请来了,我还得将他灭口。”
“……”闻人揉了把脸,“你会接骨不?”
“我试试。”
秦飞走到床前,将封三宝袖子裤腿掀开一看,不由轻啧一声,后退两步。
“怎么了?”
秦飞是从战场上下来的,能让他吃惊的事情不多,闻人被他的反应勾起兴趣,撑着桌子站起来,凑到床边。
待看清床上景色后,不由倒抽口气。
不是封三宝的伤口太狰狞,实在是所见过于匪夷所思——伤口的血已经彻底止住了,却有丝丝缕缕仿若实质的红线穿梭弥漫在封三宝的伤口处,缓慢蠕动着,好似一条条极细的线虫,正缠住断骨将其拉回归位,又遇水即化般晕染开,裹覆在破损的肌肤嫩肉上,薄薄一层,好似活物正在吞噬血肉。
见多识广如秦飞见了这一幕都头皮发麻,更别提自小琼堆玉砌养出来的闻人了。
两人惊疑不定地交换下眼神,最终还是闻人先冷静下来,垫着脚将床里的软被一拉,把封三宝整个人一盖,眼不见心不慌,转身坐回桌前。
“阿飞,时间不多了,你速去春风得意楼,现在王赫应该还没被押回去。按咱们之前说好的,你去找到冯玉将信物送回,至于她能否将王赫送出来,就看他们的本事了。”
彼时闻人刚从城主府出来,虽然对昏迷前的封三宝说出“有我在呢”这样的承诺,但对王赫最终会有什么下场,并不乐观。
“是。”秦飞拱手,“若冯玉请求咱们援手……”
“无论是什么要求,都不要答应。”闻人的表情是郑重的,“咱们守诺来到这右玉城已是冒了极大的风险,也该他们出点力了。”
秦飞心领神会,还是忍不住抱怨:“您也知道是冒了极大的风险,塘子山那场大火,要不是您为了救人拖延时间,我哪至于被烧的半个脑壳都秃了!”
“咳。”闻人面露尴尬,瞧了两眼秦飞自出了城主府一直没摘过的斗笠,“这也挺好看的么。”说罢一整神色,“快去吧!”
被压迫得不得不低头的秦飞满腹怨气地走了。
待秦飞离去,闻人重又走回封三宝床前,默念声得罪了,将被子掀开。
扑面而来的血腥味混合着汗臭,简直没法闻……
闻人屏住呼吸,嫌弃的眼神落到封三宝身上,伸出双手,小心翼翼地将少女的外衣除了,脱去外衣后,闻人看到染血的中衣下有红光在周身游走。这些红光始于封三宝的颈部,闻人伸指撩开少女散落在颈项两侧的碎发,以极轻的力道轻轻擦拭颈部的肌肤,片刻后闻人的指腹沾染了一层脂膏,将脂膏擦拭干净,闻人看见了封三宝颈上鲜红的横刀纹。
那刀纹彷如活物,正丝丝幻化成无数根血红的脉络,一缕缕蜿蜒着向四肢流去,如水上行文,不可捉摸。随着创口逐渐被修复止血,封三宝颈间的刀纹愈发淡了,闻人静静看了片刻,随着所有断骨归位,那横刀纹已变成极浅的粉红色,与肤色难解难分,如果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那是一把刀的纹路。
难道传闻是真的……
闻人收回手指,神情莫测。
屋中寂静,一角桌案一张床和几根烛火。秦飞看着床上昏迷的少女,将出鞘的匕首插回去:“您要帮她洗澡?”
“我是想给她洗洗。”闻人的表情有些惆怅,“可是男女授受不亲……”
封三宝昨日剧烈活动后昏迷,至今未醒。被秦飞带到这里往床上一扔,一身血汗就没人管了。本来闻人想着请大夫来包扎时顺手帮着清理了,但是被秦飞提醒,只好放弃这个打算。好在小姑娘可以自愈,倒是省了他们不少工夫。
秦飞心想这丫头能算女的吗?简直是个牲口。城主府里他比闻人先进正厅,藏在暗处连贺太监都没发现,封三宝各种花样作死他从头看到尾,这丫头对人对己的凶残程度是一样的,看得秦飞心惊肉跳,几乎是感同身受地替她疼。
虽然此刻封三宝安静地躺在那里,眉眼安详呼吸低微,看上去苍白柔弱,但秦飞依然无法将她与女子画上等号。
想归想,秦飞是个忠心耿耿的下属,恭敬回道:“主子您风流倜傥芝兰玉树,三宝姑娘如今落难,您为她着想,有所逾矩也是无奈之举……她不会觉得吃亏的。”
“她当然不亏,我亏啊!”
“……”秦飞再忠心也接不上话了,他深吸口气,顽强地另辟话题,“我把王赫带来了。”
“嗯?”闻人果然被吸引了注意,“哪呢?”
敢情俩大活人在地上躺半天他都没看到,秦飞对自己主子的心大程度有了全新认识,无奈地往地上一指。
“下午我回来的时候他们在对面点心铺里躲着,也不知怎么从城南跑过来的。”说着他将匕首揣进怀里,“我将他们都绑结实了,等下大概会醒,哑穴一会就解开了,您要是想问就把他们嘴里的布取出来,不想问就等我做好饭再说。”
“再等片刻。”闻人叫住他,“你昨日从春风得意楼回来,夜里那边就出事了,今日天亮后我让你去打探消息,结果如何?”
“城南兵士太多了,我的身形外貌容易引人注意,就没去那边,上午在城北的酒馆里听了半日。”秦飞看了地上还昏迷的王赫一眼,少年即使被砍晕了,也不能安稳,此刻秀气的双眉紧皱着,珠玉般的脸上透出苦意。
叹口气,秦飞看向一直等他回话的闻人:“我听到一个边军说,春风得意楼被炸毁了,哪里来的炸药还未查清,楼前湖水倒灌,住人的后院全冲毁了,现场没发现活人。”
闻人倒吸口气,正要说什么,一旁忽然传来低弱的问话:“尸体是谁都查清了吗?”
闻人与秦飞警觉地闭嘴,向床上看去,对上一双乌黑清澈的眼眸。
封三宝不知什么时候醒了,正静静地睁眼望来,见他们都望向自己,又问了一句:“尸体都有谁?冯玉和王赫他们人呢?”
秦飞看了看闻人,见他微微点头,这才开口:“王赫在这里。”想了想又补充道,“地上,晕着。”
封三宝定定盯着他,丝毫没有普通人初次见秦飞面容伤痕时的惊恐,眼神专注,似乎正在消化刚听到的消息。
她没有再追问封玉的下落,腰腹用力挣动了下,发现凭自己的力量是坐不起来的,视线转向闻人:“劳驾……扶我起来。”
闻人不知道她要做什么,劝道:“你现在起来做什么?你的四肢刚接上,别再劳累了。”
“让我起来,我看看王赫怎么样了。”
“你与他非亲非故,何必如此费心?”闻人苦劝,就是不愿意伸手。
封三宝看看他,又看看站得更远的秦飞,侧头在自己肩颈闻了下,抬起头:“你扶我一下,这么做确实是你吃亏,待日后我伤好了,一定重重谢你。”
整个房间陷入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尴尬中,好像谁强行说了个冷笑话,安静得可怕。
不该把她救回来的……
闻人的印堂比头发还黑。他脸上露出一丝尴尬,以他的教养,适才那句话说得确实轻浪了。他不知从何处摸出把扇子,大冷天地展开轻摇,用眼神示意秦飞赶紧出去。
待忠心耿耿的侍卫轻悄地走出房间,闻人合了扇子,上前将封三宝扶起来,斜靠在床头。
“三宝姑娘,这样可以了?”
“多谢。”
离得近了,闻人注意到封三宝的双眼眼波清澄,如晨星初起,但眸中的光璨黯淡,可知她武功已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