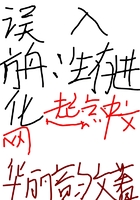我和扎西笑着把今年的青稞抬到村委会的土院里,靠墙边有一口大铁锅,是村里统一买的。我架了火,扎西把青稞舀进锅里,用大铲子翻炒着。
公公披着老羊皮袄,跟看热闹的人闲聊,那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得意。
“小孩子馋嘛。家里去年的糌粑都还没吃完,就想吃新的。这不,今天炒点尝个鲜吧!”
“你家的生活好啊,老大在外做生意挣钱,媳妇又能干。”
“能干啥呀,干活像牦牛一样,敲一下才走一步。”公公打着哈哈,话里却透着一股子老人特有的满足。
婆婆抱着桑珠站在灶边,不时抓几粒青稞尝尝,还咬碎了喂给桑珠。
桑珠咯咯地笑着,要往我怀里扑。
“你阿妈要烧火,嫫啦跟你玩啊!”婆婆从锅里抓了一把青稞,哄着桑珠往外走。
“昨天表哥回来,说咱们家又添了两头小牦牛,今年不用买了。”扎西笑眯眯的,把青稞翻炒得如浪花一样。
“过两天该轮到我们家去牧场了吧?扎西,他们都走了,你想去吗?”我塞了一把柴在灶里,抬了头看他。
“不想。这样很好,只有我们俩,嘿嘿……”
“扎西,我……”我想说对不起的,却没说出口。在我们这样的婚姻里,自古就布下的格局,命运都是注定的。如果我说对不起扎西,那么嘉措呢?其他兄弟呢?他们又会作何感想?所以,无论我心里想什么,表面上都得若无其事。
“魔女,咱们不去拉萨了好不好?”他突然说,然后又自言自语。“不行,还有天天呢,要去把天天接回来。魔女,你说他们会把天天带好吗?”
“当然会带好的。”我说,心里抽搐了一下。我的天天,分开两个多月了,他还好吗?晚上谁唱儿歌哄他睡觉?放学了谁陪他玩?尽管每周他都会打来电话,说他自己很好很好就是想阿妈,要我快点去接他。
“我还是担心。魔女,要不我下周去把天天接回来吧?”
“他要上学,怎么能说回来就回来呢?”我强笑着说。
扎西担忧地看了我一眼,说:“魔女,你如果实在想天天就去看他吧,家里的活有我呢。”
“你哥昨晚不是还打电话来了吗?说天天挺好的,唱歌比赛还得了个第一名呢。”
“我想跟天天说话,大哥说他去朋友家玩了。你说天天会去哪里玩呢?莲姐家吗?”
“不会,如果是莲那里,他会告诉我们的,可能我们不认识吧!”我说,深吸了口气,装出高兴的样子。“扎西,你去牧场的时候,把天天牦牛也带去吧。阿爸阿妈说把它放生了,就让它和咱们其他的牦牛一起放。”
“嘿嘿……”扎西点着头,把炒好的青稞铲进筐里,再倒进新的青稞翻炒。
我们吃的糌粑是把青稞炒熟后再磨成粉,吃时倒上开水捏成团就行。糌粑不是我们的主食,在半农半牧地区,只有很少量的耕地。青稞都酿酒了,平时我们仍然以肉为主。
雪山脚下的溪边有个水磨坊,上游下来的水很急,村人在溪两边安了几个转经筒,大水冲着,常年不停地转。
磨坊就在小木桥的一头,周围几个村子的人都在这里磨面。
我们到时,阿旺家的才磨完,正往毛驴背上绑糌粑袋,女人的力气不够,绑不紧。扎西见状,赶紧过去帮她绑好。女人笑着说:“卓嘎,你好福气啊,有这么好的男人帮你。”
“今晚让他找你去?”我开玩笑地说。
“好啊,你别后悔,来了我可不放人的。”
“行啊,明天你俩一起来给我干活。”我说,哈哈大笑。
“你想得倒美!”女人啐了我一口,赶着毛驴走了。
扎西笑着把毛驴背上的青稞搬下来,抱了一袋进磨坊,我抱起另一袋,还没走两步他就出来了,接过连声说:“医生让你别搬重的东西你又忘了,我来我来。”
“哪有那么严重?”我说,“搬一下腰又不会断的。”
“这是医生说的,医生说的话咱们可要记着。”他说,把三袋青稞都搬了进去。
“医生又不是佛祖。”我把毛驴拴在一边,跟着他钻进了磨坊。
磨坊有一间佛堂那么大,只有一扇小窗,光线昏暗。水磨在中间,水声隔了一层木板传到上面,“轰隆”声有些沉闷。我靠在木板上,看扎西把青稞倒在磨上,再取下水中挡着轮子的木头,木轮在水的带动下开始旋转,上面的磨盘就跟着动了起来,淡青色的青稞粒一点一点地进入磨盘里,变成细细的粉溢了出来。扎西弯着腰,拿着小扫帚不时扫一下青稞,或是扯一下盛糌粑的袋子,红红的英雄绳垂在他的额边。水哗哗地响着,小窗透进的光线照在他翻出一边的羊皮袄上,发出淡淡的荧光。
屋里有些闷热,我脱下氆氇拴在腰上。
扎西把青稞在磨上摆成一个圈后直起腰,抹了一把额头,脱下皮袄的一只袖子,我过去,扯下脖子上的头巾给他抹去汗珠。见他鼻子油亮亮的,顺手揪了一把。
“嘿嘿……”他傻笑着,搂住了我的腰。
“我看你最近很开心啊,老是嘿嘿笑个不停。”我拍了拍他的脸,笑着说。
“这样很好,嘿嘿,很好……”他的脸都笑成了一朵花。
“什么很好?”我扯了扯他的脸,“牦牛,什么很好?”
“嘿嘿,我们这样很好,只有我和你,很好,很好……”
我笑着摇了摇头,“扎西,他们都不在,也没人帮你干活,你还说很好。”
“真的很好,我不怕干活,只有……只有……”他的眼神躲躲闪闪不敢看我。
“你呀,真是头牦牛,就不能一口气把话说完啊?”我说,其实是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的,只是想故意逗逗他,喜欢看他面红耳赤着急的样子。扎西,是我的男人中最腼腆的一个。无论是私底下还是人群中,他总是默默无闻。
“只有……只有……”他吭哧着,脸憋得通红,想看我又不敢看的样子。
我笑了,忍不住踮起脚尖在他鼻尖上咬了一口,听到他在咝咝的吸气。这个男人啊,就算沉默着也能让人心软的。搂住了他的脖子,主动亲上他有些干裂的唇。
扎西愣了一下,最终还是搂紧了我的腰回应着我。
在轰隆隆的水声和吱吱嘎嘎的水磨转动声里,我听到扎西在喃喃地念,“魔女,我们一辈子就这样多好,你是我的,是我一个人的……”
我没有说话,只是更深地把自己送给他。唯一的爱,我也想要啊,只是不能。
眼前闪过嘉措的影子,他决绝地离开,虽说每周都会打电话回来,都是例行公事一般问家里老人好不好?孩子好不好?需不需要买什么让人带回?
我不知道他在怨什么,但他肯定是在怨着我的。仔细想想那一段日子,我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他突然离开还带走了天天。明知道天天是我的生命,像灵魂一样重要,嘉措却带走了他。
心里这么想的时候,眼泪情不自禁就下来了。扎西慌乱地为我抹着眼泪,“怎么啦?魔女,我今后不说那样的话了。我知道你的心,你也没办法。我下次不说了,向佛祖发誓,我下次……”
我捂住了他的嘴,咧嘴笑了。“我没有怪你,扎西,这是我们的命。下辈子吧,下辈子我只嫁你一个好不好?”
他点着头,眼里也有些湿润,然后猛地抱住了我。
我俩就这么紧紧地抱在一起,谁也不说话,水磨轰轰地响着。
嘉措的大姐嫁到了山南的浪卡子县,晚上突然回来了,浑身是伤,还带着两个幼小的女儿。她一上楼就扑到婆婆的怀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婆婆也跟着抹泪,公公在一边叹气,两个小孩子也跟着哇哇大哭。
我把桑珠递给扎西,再给大姐倒上茶,轻声说:“别伤心了,喝口茶吧!”
大姐抬起头,抽着鼻子扯下头巾抹了把泪。“爸啦,阿妈啦,我真的不能过了。他们不但打我还打孩子。”大姐说,拉过她的大女儿,掀开她的衣服给我们看,小女孩背上青一块儿紫一块儿的。
“怎么那么狠?自己的孩子都能打成这样。”我气愤地说,拉过两个小姑娘,“不回去了,就留在舅舅家,舅舅养你们。”
“卓嘎……”公公看了我一眼。
我知道公公的心思。女儿嫁出去了,就是别人家的人,有什么事也该另一个家庭去承担。如果我们留下孩子,一是负担过重,二是怕对方闹上门来。我却是顾不了这些,看着大姐脸上的伤,实在不忍心。同样是女人,得不到男人疼爱的滋味我感同身受。而且,大姐是嘉措最喜欢的姐姐,也是家里唯一能说知心话的人。“爸啦,我知道你的心思,就让大姐留下吧,她也是你的女儿啊,难道你就忍心看着她和两个孩子回去挨打啊?”
公公听我这么说,也不好再说什么。
大姐就这么留了下来。
突然之间,家里多了三口人,生活当然就得辛苦一些了。不过大姐能干,什么活都抢着做。
大姐的家长次仁是两个月后来的,当时我们正在天井里捻羊毛。次仁看到大姐,想说什么却没说出口,我冷冷地说了声:“来了?坐吧。”就转身去提了酒壶放在桌上。“自己倒吧!爸啦走亲戚去了,有事你跟扎西说。”然后扬声叫了后屋的扎西出来。
大姐躲进了佛堂。
我们这儿的习俗,嫁人之前是父母说了算,嫁人之后是家长说了算,女人自己的事,似乎永远轮不到自己做主。
扎西挠着头过来坐下,我给他倒了酒,也给大姐的男人倒了酒。原本我是该回避的,只是扎西也是个闷葫芦,我怕他没想清楚就乱点头而害了大姐,干脆坐到一边的织布机上,拿起梭子有一下没一下地织起来。
“我……”次仁喝了口酒,低了头也不敢看扎西,“我是想来接……接你姐回去。”
“这个……”扎西挠着额头,看了看我,不知怎么回答。
“你们家是不是觉得还没把人打死啊?要接回去接着打!”我放下梭子,看着次仁说。按理这样的场合是轮不到我开口的,只是扎西是个有话说不出来的人,我如果不说话,大姐就只能任他们欺负了。
“阿佳卓……卓嘎啦……”他可能没意识到我会说突然出这样的话来,怔了一下。“不是……我们……”
“是大姐不会织氆氇呢还是不会酿青稞酒呢?你们把她打成这样?是不是觉得她兄弟离得远,你们打了她也没人管啊?”
“不是不是,阿佳卓嘎啦,你误会了……”
“我可没有误会,大姐身上的伤现在还在呢。她弟弟嘉措在拉萨,这样吧,等他回来。如果他说你们应该打他大姐,我们就让你带她回去,如果他说不想他大姐去你们家挨打了,我们就把她留下来。我们的生活虽说没有你们好,但也不缺一件氆氇一点糌粑的。”我冷冷地说。
“阿佳卓嘎啦,都……都是我弟弟和姐姐不对,我也说过他们了,家里现在牲畜多,她不回去,没人管家啊!”
“你姐姐不是很能干吗?不是说你们有老婆不要她了吗?让她干啊。我家大姐不会干活,就留下来让她阿妈再好好教教,是不是啊扎西?”
扎西猛点着头。
次仁涨红着脸不知再说什么,过了一会儿看着扎西说:“二哥,爸啦,阿妈啦还好吧?”
“好……挺好……”扎西偷偷看了我一眼说。
“扎西,你把酒糟给牦牛提下去吧,该喂了。”我说,站了起来。
扎西站起来如释重负一般去厨房提了饲料出来下楼去了。次仁站起来看着佛堂有些迟疑。
我拿过捻线的工具往佛堂门口一坐,也不理他,转动着捻线的锥子,低了头捻起线来。
次仁尴尬地站了一会儿,说:“那……阿佳卓嘎啦,我去镇上找个朋友,明天再来。”
“你请吧!”我头也不抬地说。
次仁走后没一会儿,公公婆婆就回来了,看到我笑眯眯的。婆婆倒酒时,公公说:“给卓嘎倒上,今天我要敬她一杯。”
“敬我?”我吃惊地抬起头。
“今天我们家的魔女发威了,这个威发得好啊!”公公笑眯眯地端了我的酒杯走过来递给我。
我接过酒杯,看了看婆婆,婆婆笑眯眯地说:“卓嘎,今天的事谢谢你。扎西是个牦牛,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你俩这是吓我啊!”我乐了,知道他们说的是刚才次仁来的事。仰脖喝下酒,“原本这事轮不到我说话的,只是你们又不在,我就多说了几句。别怪我啊!”
“谁会怪你这个魔女啊!”婆婆笑着拿过我的酒杯放好,转身进佛堂去看她女儿了。
“卓嘎,今后家里有什么事你尽管说话。我们都老了,也管不过来这么多事。”公公说,一杯接一杯地喝酒。
“爸啦,你可不老,再说还有嘉措和扎西呢。”我抽出一条羊毛接到正在捻的线上,拨动着捻子旋转起来。
“嘉措不在家,扎西又不爱说话。我老了,你阿妈身体又不好,家里的事你就多辛苦一些。”
“爸啦,你这么说,我都不敢说话了。”我收回长长的羊毛线绕在旋转着的捻子上。
屋后的阳光暖暖的,加上酒精的作用,人变得昏昏欲睡。公公歪在卡垫上,扯过毯子盖在胸上,不一会儿就发出了鼾声。
我听着佛堂里传出嘤嘤的哭声,心里也有些酸酸的。我放下羊毛进了佛堂,见大姐俯在婆婆怀里,压抑着哭泣。记得我初嫁过来时,大姐达娃也才出嫁不久,月亮一般的女子,才几年啊,满脸皱纹,脸颊上长满太阳斑,脊柱过早地弯曲了。大姐的性格跟我不一样,她是个把什么事都放在心里的女人,整天只知道埋头干活,我不知道她婚前都经历过什么,婚后的她不快乐是真的。她嫁的兄弟俩早早就没了父母,只有一个没出嫁的姐姐,姐弟三人相依为命感情很深。弟弟们结婚后,注意力从姐姐身上转移到了老婆身上,让以阿妈自居的孤寡姐姐感受到了冷落。厨房里多了一个女人,也就多了一个敌人,家庭战争不断。
在我们的习惯里,一个新来的女人,需要经年累月才能熬成自家人,用无数的眼泪和汗水换来有朝一日的平等。大姐达娃,还没熬到那一步,就已经满身伤痕。大姐达娃经历的过程,不是一个特例。在兄弟共妻的家庭里,如果作为老大的家长没有能力,弟弟们就不会服从他的管理,加上女人不善调解,一件事情你也想做主,我也想做主,这个家还怎能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