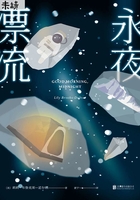“坐下。”他说,从桌子的抽屉里翻出清凉油,笨拙地打开,用食指蘸了往我脸上涂,一边说:“都肿了,魔女,别怕痛啊,我轻点。”
“扎西……”我拉着他的手腕,热泪盈眶地看他。
“是不是很痛?我再轻点啊。”他说,继续涂抹。
这时嘉措下楼来接水,看到我们,眼里闪过一丝不快。我装作没看见,闭上了眼睛。对于这两个男人的感受,我真是无法做到无动于衷。一个是我所爱的,一个是爱着我的,两个我都无法丢下。不想看到他们因我而痛苦,却时时看到他们因我而痛苦。对于朗结、边玛和宇琼,我可以一笑而过,可以做到绝对的公平合理,然而对于嘉措和扎西,公平合理却是对他们最大的伤害。
雪顿节在我们传统的节日中,是比较大的节日。“雪顿”用汉语翻译的话,“雪”是酸奶的意思,“顿”指的是宴会。也就是说,雪顿节指的是“酸奶宴”,一般是在每年的藏历六月十五日到七月三十日举行,有藏戏表演,各寺庙还会举行“展佛”活动。
以前听奶奶讲过关于雪顿的来历。说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海拔高,气候寒冷,一年中只有六月、七月两个月,天气转暖后,小虫们才会出来活动,佛祖释迦牟尼规定了不杀生的戒律,所以我们连小虫也不敢伤害。各寺里在每年的藏历六月十五日到七月三十日之间,不准僧人出寺活动,就是怕走动之间伤害小虫、小蚁。在此期间,僧人们在寺中安安静静地念经学习,直到解制才能出来。当僧人们终于可以出来活动时,当地老百姓都会拿出最好的酸奶招待他们,同时在哲蚌寺举行庆祝活动,以演藏戏为主,所以渐渐有了“哲蚌雪顿”之名。
雪顿节头一天,莲他们五点钟就到我们这儿来了,大家约好一起去哲蚌寺看展佛。
我给每个人盛了酸奶,扎西一一递给他们。
“莲姐,给我们讲讲雪顿是怎么回事好不好?”蓉捧着碗,朗结正给她放糖。家里自制的酸奶,用牦牛奶发酵而成的,特别黏稠且酸,吃时要放很多糖,搅拌均匀后放上一会儿等糖化了才能吃。
“这个啊,就是酸奶节嘛。”莲笑着,一副馋样看着洛桑给她搅奶。“史书上说,五世达赖时期,‘哲蚌雪顿’开始后就调集西藏各地的藏戏团来拉萨演出,很是热闹。那时五世达赖住在布达拉宫,不仅让藏戏团在哲蚌寺首演,还规定第二天必须到布达拉宫演出,然后才能在拉萨和各地巡回演出。罗布林卡是十八世纪建成的,是历代达赖的夏宫。一九一三年十三世达赖决定,每年的‘哲蚌雪顿’藏戏在罗布林卡首演,还允许普通老百姓观看。取消了哲蚌寺首演藏戏的特权,不过这样一来,雪顿这个原本只是宗教活动的节日开始变成了普通老百姓的娱乐活动。”
“那……展佛是怎么回事?”蓉舀了一勺酸奶放在口里,“好酸,朗结,再放点糖。”朗结又舀了两勺糖放进她碗里。“等一会,糖化了再吃。”
看着朗结和蓉,我心里挺安慰的。说实话,朗结虽说也是我的男人之一,但我们更像兄弟而不像夫妻。我希望朗结能找到一个自己所爱的女人,独立成一个家,过上安定踏实的日子,我们就像亲戚一样互相走动、关心帮忙。记得莲说过,在内地,兄弟间就是这样生活的,各自有家,有女人有孩子,不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有事的时候,兄弟姐妹都会来帮助。
女人只照顾一个男人,只照顾一个孩子,那该是多么惬意的事啊!
“展佛是各大寺庙在雪顿期间特有的一个活动。像咱们今天去的哲蚌寺,旁边的山坡上修了一个水泥台,那幅唐卡大约有20米宽30米高吧,从山坡上的水泥台上直铺下来,非常壮观。每年展佛时,都会汇集上万人去观看,信徒会往佛像上扔哈达、鲜花。还有苦修的僧人赤裸着上身磕长头。咱们要早些去,可以看到佛像从大殿抬出来的情景,上百个人啊,有僧人有老百姓抬着一个长卷走在山道上,法号齐鸣,壮观极了。咦,卓嘎、央宗怎么还不下来?”
“她呀,昨晚发疯把卓嘎……”朗结快嘴快舌地说。
“她还在睡懒觉,坐了好多天的车,累的。”我说,白了朗结一眼。
“是吗?”莲抬头看我,突然惊异地瞪大了眼,想说什么却把话咽了回去,迅速地低了头,把酸奶一勺一勺舀进嘴里。莲能为所有人喜欢,其实就在于她有一颗水晶般清澈透明的心。她从不会让人难堪,总是尽可能地为他人着想。就像现在,她低头的那一瞬间,其实已经看到了我肿胀的脸颊,也猜到发生了什么事,但她不说,给我、也给央宗保留了面子。
扎西抱了睡得迷迷糊糊的天天出来,我接过来给他洗脸、洗手,然后端了酸奶喂他,同时悄悄捅了旁边的嘉措一下,“去叫一下央宗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嘉措板着脸看着朗结。“去叫一下她。”
“怎么又是我?”朗结撇着嘴,极不情愿地上楼去,不一会儿央宗跟着他出来了。
我放下天天,让他找干妈喂去,天天就听话地到莲身边去了。我转身给央宗盛了一碗酸奶,放了糖递给她。央宗红着脸接过。
“卓嘎,你去换身衣服吧,今天别穿藏装了,山路不好走,你还要抱天天,穿轻便的衣服,把头发披着,我想拍些你散着长发随意的照片。”莲抱了天天在怀里让洛桑喂着。她说话时并没看我。
“好。”我说,眼眶一热。莲,她哪里是为了拍照啊,让我散发不过是把红肿的脸挡住而已。
临出门时,我换了一身运动服和运动鞋。这是扎西上个月发了工资为我买的,一直没好意思穿。不习惯这样的衣服,感觉一点重量都没有。莲笑我说:“铁有重量,你穿铁做的袍子吧!”
从小习惯了的东西,要改起来还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不过,天天就不一样,我给他讲草原,喝牦牛奶,却让他穿汉族人穿的服装,上城里的幼儿园。我希望他长大后是个不忘家乡,但也接受现代思想的男人。
没能上学是我的遗憾,总希望我的天天能好好读书,最好能上大学。
“别揉搓,晚上我给你带瓶红花油来,活血散淤的。”莲见我又开始摸脸,便把天天递给我抱着,小声说。
“嗯。”我没有说谢谢。对于任何人,我可能都会客气地说声谢谢。独有莲,我不用客气。她于我,就像阿妈于我、奶奶于我是一样的。别人也许会觉得我和莲仅仅是朋友,两个不同民族、不同背景里长大的女人,彼此好奇所以走得近一些。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和她,不仅是朋友,还有如亲人般无微不至的关怀。莲和奶奶之间莫名其妙的心心相惜,一直让我迷惑,也许真如奶奶所说,上辈子,我们和莲肯定是有着扯不清的关系,今生的相认是来还前世的夙愿也说不定。
小区里很安静,只有一两家亮着灯。听见响声,各家院里都会传来藏獒沉闷的吼声。雪顿节虽说是个热闹的节日,如果不去看佛像抬出殿堂的情景,倒也不用早起,如平时一样七点起床就可以了。
因为莲和一航阿哥要拍照,所以大伙都陪着他们。扎西肩上扛着一航的三脚架,手上拿着天天的外套。朗结的胸前挂着莲的相机,蓉走在他身边。洛桑背着莲的摄影包,嘉措则拿着莲的三脚架,央宗走在他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