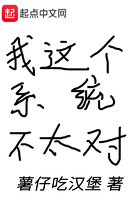“我今日替名扬前来祈福,家中只有他这么一个独苗,虽求他能早日开枝散叶,不过就在姑娘离去后,他便整日心思不定的,连生意亦处理得一塌糊涂。”
花晚晴瞪大眼,不懂易夫人所言是否有弦外之音,但此话使她困窘有增无减,即便想破头也不知要如何接下话茬。
怎办?!花晚晴咬着唇,此时离去定会让人于背后非议她得势猖狂;可若不走,她不知要如何自处。
假装忘了易名扬还是假装她仍痴恋他?过去虽不似过眼云烟能顷刻的烟消云散,但说仍执着于心,她问心有愧。
再者——
“大夫人,既易家少爷已有妻室,开枝散叶便有期可待,他们能恩爱相处就是易家福气,又哪会让少爷心思不宁呢?”
花晚晴脱言毕发觉香蓉神色更是煞白,无心之言伤了她人。这让花晚晴更沉默了,只好退缩回小小的躯壳,让易夫人的声音隔绝在躯壳外,她不想徒增烦恼,更不想再成为他人烦恼。
“夫人。”花晚晴怯生生开口,谨慎的口吻与她这身华服并不相符,倒像极她当年在易家为仆的日子,“外婆在禅房久候了,所以不便再与夫人闲谈,如有怠慢,请夫人见谅,我,我必须回去了。”她已恨不能拔腿就跑,但求自己不要显现出狼狈。
“若知今日,当初我便不阻拦了。”突然一语,是易夫人说给花晚晴听的,易夫人放下了易家当家夫人的面子,为向花晚晴示好。
那低声说道,话中带着的是种种无奈和自嘲,似嘲弄的仅为天意命数,却在不显山露水间让香蓉忽然无地自容。
一言之间,哭笑不得。
花晚晴僵住了脚,没回头。
她只愿一直向前,更不再回头去想那困扰她的事儿。
直到——
“姑娘。”
身后,不知是谁叫住了她。
一夕,在这不大的寺庙,竟让她频频的遇上相熟之人,这可比街角说戏的话本更出了奇。
她回头,有些尴尬,但仍是停下了脚步,勉强一笑,又觉这笑有些有失妥当。
来人碎步追了上,手中捧着手炉。但快走到了花晚晴跟前,被被向家丫头拦在了花晚晴三步之外,直至花晚晴轻扯了丫头的衣袖示意,丫头们才将此人放行。
“姑娘,我……我想……”
花晚晴不知所措地看着来者,嘴唇紧咬得失了颜色。
“那事儿你还没对她说?”
临近京师的丰城有处常年不结冰的河,就算岸上已白雪皑皑,但河中却依旧流水潺潺,是冬日体验垂钓之趣最好的去处,更犹在天气好的时候。
如说今日,阳光灿烂,无风所扰,只需将河岸积雪铲去再以兽皮为垫,便不会觉地上太过冰凉。
几日前,丰城下了雪,不大。岸上零零落落透着点儿灰蒙蒙的绿,交错白雪间的景致看来像是画工精心描摹的画卷。只可惜,难得的清幽却唯独被扰人的那声问询给打碎了。
“你故意不睬我?”尉迟兰馨边问边伸出了手,在皇甫寻眼前晃了晃,但他不答她。往日,她尉迟兰馨对垂钓是有几分兴趣没错,可眼下她心乱如麻,又哪能似他还守着一副好心情?尉迟兰馨心焦得厉害,无心再顾着钓竿,拍了拍身子便利索地从兽皮垫子上起身,又略微沉下了脸,安静的站到了皇甫寻身后。
一呼一吸,万物静谧,山间未传出鸟鸣。而若非鼻尖哧呼哧呼仍冒着白气,河岸一角看来就像没了生气,连河岸上的这些人似都像是被冻结在了一瞬。
要见鬼了。
尉迟兰馨愤懑地瞥了程一一眼,这唯一一位没守在远处侍卫,却似乎很享受这份安静,甚至由头至尾都未发出零丁的声响,似天生的木头桩子般。
程一虽沉默但平静的以眼神回应了尉迟兰馨的目光,见她嘴边碎碎念着什么,更强忍下了笑意。尉迟兰馨大概是不知他读得懂唇语,要不又岂会当他之面,无声的抱怨起他家主子?
“你……你……”过了好一阵,尉迟兰馨手握成拳,于皇甫寻脑袋上方挥动了几下,除见程一目光更显笑意,她希望引起注意的那人却仍岿然不动。“你就不能搭理我一声么?”
“再嚷下去,鱼就快被吓跑了。”
“我说我特意从京城赶来,可不是为看你钓鱼的。”尉迟兰馨若非迫于无奈也不想扰人兴致,只是他再如此拖拖拉拉,怕是她爹爹便就要将她许给他人了。“皇甫寻,这可是大事儿。”
尉迟兰馨绕到了皇甫寻的面前,看他沉了脸但仍不做声,她一时更是气不过了,情急之下竟就动了手。又因她的行为出其不意,让皇甫寻是措手不及,在他想要夺回杆子前,杆子已被尉迟兰馨丢入了河里。
“兰馨,你想胡闹到什么时候?”
“我胡闹?你我多年交情,且不说我求你一事儿怎么了?明明是你先前已允下的,回头怎不见你动静,我爹爹可催得紧,你再没动静的,他便要将我随便嫁给他人了。”
皇甫寻紧抿唇,眉目中隐隐含着怒气,但不像是因兰馨而起,倒像是对己不能释怀的折磨。
“我就知道,是为那姑娘吧,先前以为你不过是对她一时喜欢,后见你都躲来丰城了,我又岂不明白,可这事儿我就属意你,你不帮我,我该怎办?”
皇甫寻踱步离开岸边,程一随行。驻在远处的侍从反到了河畔帮忙收拾起这岸上的行头。尉迟兰馨步步紧跟,见皇甫寻面无表情又心绪万千的模样,忽然生出愧疚。她第一次见着皇甫寻为一个女子如此困扰,但除皇甫寻之外她便真寻不着可信之人了。
“我前日跟爹爹都快闹翻了,你可知?”林间的路不平摊,石子散乱,不留神便可能会被膈了脚。尉迟兰馨抓住皇甫寻的手臂,扯着他让他好好听她说话,“别怀疑,你我相知甚久,我知这女子对你特别,也知你不忍亏待她。你答应我的请求或许不过因被爹爹人情所累,被我恳求所扰,但我想让你知道,我真无意跟她争宠。那劳什子的名分,爹爹看重我却不会,反正你我不也是作假么?”
“兰馨,你不知你爹爹根本就不会容你这堂堂将军之女成为他人侧室么?但我若娶你为妻,我将无颜相对花晚晴。纳她为妾?或她身份也只配如此,我以往是曾想过,但现下我不忍再强迫她了,你要我如何应对?”
“皇甫寻”口吻听来惊讶,“这不像你,但你躲来丰城又能如何,若是皇命下来,你怎能对得起那姑娘?听我说——”
兰馨叹了口气,嘴角无奈地扯了扯,“名分一事儿我知道爹爹不会罢休,但我求你给我的不过也就是个名分,你若不便跟那姑娘说清,由我来解释亦可。虽之前不想让你大肆声张,所以连那姑娘也不想说明白的,可这回儿是不说也得说了不是?”
兰馨的退让是皇甫寻所料的,只是花晚晴那头岂是兰馨说得清的呢?他甚至没把握将此事告知花晚晴后,花晚晴会如何待他,他怕的是皇上此时宣召,如此一来他与花晚晴倒真没退路了。
“还有,你可让她安心,她嫁入你府上是为妾,这日子也不会太久,且我又已说服了我爹爹,他不介意你迎亲之前已有妾室。”
皇甫寻扶兰馨上了马,愣了愣,看着兰馨的勉强一笑,他忽像想透了什么。千言万语不及道,但兰馨这话又叫他知兰馨做出了最大的退让,甚至有可能已为此触怒了老将军,她——
“爹爹当然生气,可他拗不过我便只好答应了。他笑我傻丫头,天下男子怎么就唯独看上你了。”
“兰馨——”并肩而行,皇甫寻双手执着缰绳,忽抓了紧,他看她,眉头因疑惑皱在一起前,她努力地为他解开了心头之忧。
“放心,我兰馨才不是看上你呢,倒是最信得过你,或只有你会守约。和我只做那挂名的夫妻。所以嘛,你越在乎那姑娘我便越高兴,至少你不会突然转了主意,真看上我。”
“不知这天下又男人又有几个是你看得上的?”
“错,是没遇上,休得咒我。”兰馨笑笑,轻松耸了耸肩,“不过我倒是真吃惊了,你这回儿可非一般的上心呐。”
皇甫寻亦笑了笑,却不轻松。
思及花晚晴,他总措手无策。若逼迫她来到他身旁,她会怎样?虽尉迟兰馨有意为他关说,花晚晴却未必是通融之人,她甚至会不信他能一心待她,可难道将她留下的办法就只有那么做了?
“想什么,不都给了你宽心丸么,怎么又皱起眉了?”尉迟兰馨斜目问,见皇甫寻易变的神色不禁让她在意。
不懂心动是何等难受的滋味,但使皇甫寻变成这般优柔寡断的东西,她更不想触碰了。“哎呀,着急什么嘛,不过是个姑娘,带回府,说一声你是我的便就好了。怕向家不同意?可请我爹爹去说嘛。”
“兰馨,别胡闹,这事儿我得自己处理。”
“那么说好,月初你将婚书送来,有什么需要,尽管说,姑娘那头,我也可以——”尉迟兰馨再度被皇甫寻打断了嘴,愣着瞧他无比严肃的神色,她只觉好笑。
那姑娘还真如此重要了?
“这事儿你处理不得,她那方连我都不知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胡闹呗?见你整日说我胡闹,她就不胡闹了?不过是向家的姑娘,还是——”名分不定的丫头。尉迟兰馨闭了嘴,看来皇甫寻已用情至深,就连她小小的抱怨若不留神伤及那姑娘,他都会瞬间阴沉了脸,“好吧,那你想如何,若她不肯为妾,我也不能为妾不是?我爹爹先前就连你纳妾都不许呢!”
像山一样沉默着,皇甫寻安静得有些吓人。
他目光恁的沉了沉,嗓音中透着难解的情绪,似笑、似怒,并不如常日笃定。
“三日后,我会去向府,如你所说,这事儿是该了结了。”
皇甫寻试图说服的人只有他,他尽量不让自己想到花晚晴难过的表情,更希望到时他亦能无视这些而狠下心。
毕竟比起让她离开,他更不能失去他。即便她骂他,他特会痛恨这等自私的选择,但思及种种,他发现这是他唯一能做的。
三日后,他会将纳妾的事儿向向家老爷提及,若向家人不肯——
皇甫寻失笑地望着远处干枯的枝桠,他心中无法平静,他或又要变成向家或花晚晴眼中那得势不饶人的坏人了呢。
“权势也罢,手段也罢,她留在身边就好了。”
“说什么呢?就算嫁给你做妾室也不能算委屈她吧?”但说罢此言,尉迟兰馨却也不由得怔了怔。换作是她,若真心爱上别的男子后,她是否又愿意与他人分享?忽然没有底气将这话继续当作玩笑,那种心情她也许至今不明白,可细想,也许那姑娘固执之处也正是她可爱的地方。
“总之,一切都会好的,对不对?”尉迟兰馨不安反问,她想说服自己。若非她出现,那姑娘与皇甫寻间本也未必能得之善果,毕竟这皇甫寻可是天下最得势的男人之一,而那姑娘却不过只是向家失落在外,连身份都不干不净的丫头。
就算没她出现,皇甫寻也未必能娶那丫头为妻不是?
“我看不明白你。”与皇甫寻侧目相视,见兰馨迟疑许久,皇甫寻也约莫猜出她要问的事儿并不好答。
“爹爹说,天下是皇甫家的天下,但这日后或就是你皇甫寻的天下。”
随行之辈必是自家最亲信的人,而若非此故,尉迟兰馨倒不会冒险的口吐“狂言”,“可是,为儿女私情,你是不是又已弃了这念头?”
皇甫寻深吸了口气,不懂要摆出何等表情。这一问让他更显沉默。
仰头而视,那灿烂了一晌的阳光却悄悄躲进云里,像足他的心情。“我不知道。”
好像,连山更沉默了。在没有鸟鸣的空山里,一切如此萧条。滴答的,只有一溜的马队和满怀心事者,那怦怦的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