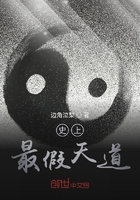夜里明月高悬,今夜心里颇不宁静。
“胡人为何有如此强军!”
“胡人!”
“胡人……”
“我不是,住口!”张晓从垫子上惊坐起,回过神后吐出一口浊气,一摸额头竟然全是汗水。
做噩梦了么?可是怎么会梦到那个人呢?
张晓摇了摇头,从垫子上起身穿好衣服,走出帐篷,看着天边尽头处漆黑一片,天上的繁星点点,夜还深沉着。
远方的老树下面有个土包,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那么的鲜艳,好奇心一点点充斥着。
守营的士卒看到张晓出来也不敢大声喧哗什么,只是点了点头,目送着她出去。
她从马背的兜篓里摸出一坛酒,大饮一口,苦笑着身不由己的命运。原本甘甜的美酒,不知为何此时喝起来也那么的苦涩。
渐渐的有些醉意上来,但是她还是要去看看,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自己该去那里,有个什么东西在那等自己。
缓缓的朝着那棵干枯老死的枯树走去。
远远看去,只是天边一个人,带着一坛苦酒,一坛苦渡。
她不曾来过此处,因为来咸阳都是从东来的,从没有由北向南过,所以这里是那么的陌生。
慢慢的,张晓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到了老树下面,看清了这个棵老树,是一颗弯曲的不成样子的树,她也不是树种专家,看不出这是什么树。
她只是愕然发现原来这个土包还有块碑文呢。
碑文经历多年的风吹日晒,岁月磨蚀后,上面的文字也看不太清楚,像是蚯蚓爬一样的字体。
张晓眯着眼睛,仔细的看着,上面写:“燕地义士庆……。”
上面的人名是看不清了,燕地义士,不过看落款也知道些大概年月,上面写着秦王政二十年!
“嗯!”张晓本来微醉的酒气一下子散开了,手颤抖的摸着那碑文说:“是么……原来你在这里呀。”说完眼角的那珠子,真的断了线绳,滴落了下来。
她将无忧放下,放在一旁,月光下暗黑的剑鞘反射着点点光芒,亦犹如天上的繁星般。
————————————————
韩国刚灭亡过几载。
燕都蓟城
“蒸饼咯,蒸饼。”
“来看看咯,上好的肉,看看。”
熙闹的蓟城似乎还没有感到来自南方的威胁,虎狼之国紧盯着北方平原,张开了它血盆大口,锋利的牙齿时刻准备。
它随时扑上来,吃下这一块美味佳肴,毕竟这可是一块肥美之地,它可是虎狼,怎么会放弃到嘴的肉食呢?
街上的人多是面黄肌瘦,人群中一阵推搡,一个格格不入的家伙挤了出来。
说是格格不入,因为他身上穿着的不是麻布头,而是丝质华服,本该华丽的衣衫,当如今却是破旧不堪了。在看年纪也不大,看上去也就十六七岁的样子。
少年玉琢水嫩的皮肤是那么的美丽,出落得十分俊美,手上拿着一把黑色像是长箫的东西,在仔细看的话,才发现原来那是一把没有剑格的宝剑。
“还真是够挤的。”张良撇了撇自己的嘴巴,整理着自己的领口,忧心忡忡道:“燕国难道还不知道秦人已经准备灭赵后下一个就是他们吗?”
“咕噜~”
“咕咕。”
肚子里传来一声怪叫。
张良郁闷地低下头摸了摸自己的肚子,她已经有三天没有吃过饭了,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身体并没有出现严重的不适,似乎还能饿很久。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她现在确实很想好好的吃上一顿,毕竟长时间不吃饭会得胃病的,读过些医术的她,自然不想冒这个险。
“咕噜~咕咕~”
又声闷响传来,登时不由得让张良尴尬起来,她正义盎然道:“等我吃饱了,就去找秦狗报仇!”
她走到一处酒馆,抬头看到上面的字,不由得面色一红,尴尬无比道:“我不认识燕国文字啊!”
“咕噜~”
五脏庙又一次的抗议,让她的脚步不在迟疑起来,她大步进入酒馆内,看了看四周,同时四周的人也都在打量着她。
不时的听到有人在说着些什么,只不过乱哄哄的听不清楚。
不过忽然听到有人在高歌拍手,又有击筑的声音,张良不由得走出酒肆,寻着声音看到不远处的一处摊位上,就见三个人在饮酒,其中一个人长得凶神恶煞,一声血腥味,而他衣着麻布,上面还有些腥臭,估计是个屠夫。
另外两个人衣着虽说不上华丽,至少干净整洁,张良慢慢走近他们,在他们一旁听着这个乐曲竟然一时之间忘记了腹中饥饿。
他们在街市上唱歌,相互娱乐,不一会儿又相互哭泣,身旁像没有人的样子。
“吾之志难平,心中恨意无可泄也!”其中一人悲恸大哭着,不知道他因何而哭泣,张良只看到他的腰间别着一把宝剑,而那个宝剑也是贵族用剑。
“咕噜~”
忽然又一声传来,那三人中的二人不由看向张良,虽说她一路走来燕国已经练就了厚脸皮可是这么尴尬的事情发生了,脸色一下子就羞红起来。
站在那不知道该干什么,三人对视许久之后,想是之前击筑的那人明白了张良此时的处境,于是他舍筑而作,起身向张良作揖道:“在下高渐离,不知道先生可否与吾等共饮?”
……
“张郎君原来是张相之子,是我等冒犯了。”那个屠夫本来憨笑着的神态忽然严谨起来。
“哪里呀,已经是亡国之人,有甚么尊贵可言?”张良苦笑着,一口饮下燕酒,不说别的,还有些甜。
张良复而放下碗,看着三人疑惑道:“对了,不知道三位兄长为何在此哭泣?”
此时四人是相见如故,只恨想见太晚了,所以互相称对方为之兄弟。
“哎,我等也是如此,如今秦王虎狼之心昭然若揭,如今秦王已经先灭韩亡魏,赵国已经危如累卵,王上却不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我等怎么不在此哭泣?”庆轲依旧是一脸伤心欲绝的表情说道。
“这我倒不认同兄长所言。”张良笑着说道:“不过几月,就有一桩功业等着兄长呢。”
“哦?张贤弟所言当真!”庆轲登时起来,握住张良的手,张良不由得面色一红,毕竟好久没有男人碰到自己,忙的从庆轲手掌挣脱开。
而握住的一瞬间庆轲心里惊叹道:好软的手。
“咳咳,是的,我怎么会骗兄长你呢。”张良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