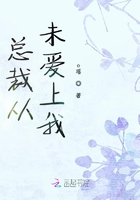随着日期的临近,使团成员正式确定了下来,除了斌椿,还有以下几人:斌椿的儿子广英;三名来自同文馆的学生——凤仪,张德彝(又名德明),彦慧,他们都是旗人。仆役七名。他们所有的费用都将由海关承担。为了他们五人坐头等舱和其他七名仆役的费用,父亲向法国邮船公司支付了四千零二十九两银子。正式出发前,朝廷为了提高斌椿作为使团高级成员的威望,决定授予他正三品衔,并指派为总理衙门副总办。但即便如此,这个一向不被人注意的满人官员仍是一个旅行生手和外交上的小人物。父亲终于发现,随他前往欧洲的这个使团,无论在总理衙门还是欧洲人眼里,都不是一个正式
[1]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美国北长老会派至中国的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六十二年,曾任北京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精通中国语言和文学,对晚清中国社会有微细的观察和独到的见解,著有《汉学菁华》(TheLoreofCathay)和《花甲忆记》(ACycleof Cathay)等。
的外交使团,而只是他此行的一个附属。他的期望打了这么大的折扣,突然觉得索然无味起来。
恭亲王觉察到了他的情绪,在一次总理衙门的例行会议之后叫住了他。亲王不经意地问他刚从上海带来的那个厨子手艺怎样,做的菜是否比北京菜要精致可口,还说他很有兴趣请那个厨子来恭王府一展手艺。亲王提前预祝他回国之行顺利,并说,使团之所以定这样一个不高的规格,是为了让这次赴欧洲考察的阻力降低到最低限度。
“你要知道,我们这个国家,传统守旧的势力向来有着极大的能量,任何一点细微的变革都可能引发一场地震,我们只能缓慢推进。”站在比自己大两岁的亲王面前,看着他坚毅的面孔,父亲为自己的短视和幼稚羞愧。
父亲和恭亲王第一次见面是在1861年6月。那是一个对他在中国的命运有着决定性影响的夏天。那年他二十六岁,身份是时任总税务司的李泰国的代理人,应英国公使卜鲁斯[1]之邀从上海来北京商议海关事宜。
上海此时尚是闷热潮湿的梅雨季节,他没想到京城要比南方燠热得多,瓦蓝的天空中成天挂着个毒太阳,稍一动弹就会出一身臭汗。在焦急等待了十天之后,他接到了去前海西街恭王府的命令。
天气虽然热得可怕,他还是决定穿上西装。临出门他又仔细检查了随身携带的文件。将要接见他的是皇上的弟弟、年初刚刚成立的负责帝国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的首席大臣,他不会轻易放过这样一次机会。在爱尔兰家乡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有个人得到了一张记载着点金石秘密的牛皮纸,牛皮纸上的文字解释说,这块点金石与这个世界上成千上万块外形酷似的普通卵石混杂在一起,辨识它们的秘密是,点金石摸上去是暖的,而普通的卵石摸上去是凉的。那个人卖掉了全部家当,在海边搭了一个帐篷,开始寻找这块神奇的石头。他捡起一块石头,如果它是凉的,就把它抛进大海,以避免重复捡起它。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就这么过去了,他还没有放弃寻找。有一天,他捡起了一块卵石,是暖的,但是在他意识到这点之前,他已经下意识地把这块点金石抛进了大海里!他可不想做那个把机遇丢进大海的蠢夫。所以他一定要非常审慎地对待他的中国上司,争取给他留下一个好印象。自己这块顽石扔到东方快十年了,如果有幸让这位关键人物的手指点中了,没准还真能成为一块金子!
穿过一座西洋建筑风格的汉白玉拱门,一脚踏进恭王府,一股润泽幽香的
[1]卜鲁斯(Frederik William Adolphus Bruce,1814—1867),1858被任命为英国驻华公使,1865年改任驻美公使。
气息裹住了他,此间的凉爽与外面的酷热简直是两个世界。他被引入专门接待客人的安善堂坐下,从敞开的扇叶门可以看到对面一座太湖石叠成的小山。后来他知道这山叫滴翠岩,岩下那个洞叫秘云洞,洞里有座福字碑,还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的。但此时的他无心观赏美景,他必须集中精力暗自准备如何用尚不熟练的中文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在一个幕僚的引导下,恭亲王由总理衙门资深大臣文祥陪同着从屏风后转了出来。亲王身材颀长,穿着一件湖蓝色的丝绸长衫,风度儒雅。他的皮肤有些黑。可能是近视的缘故,他看人时习惯把眼睛眯起来,但脸上看不出一丝浮躁、骄横之气。他觉得与其说这是一个显贵的王爷,倒不如说是一个略有些忧郁的诗人更让人可信。这使他对这位中国皇帝的弟弟一下子产生了亲近感。让他惊讶的是王爷的年轻,他看上去比自己大不了多少。他感到王爷在气质上似乎有些怯懦,但后来他会知道完全不是他想像的这回事。自前一年秋天联军攻占北京以来,皇帝北狩,躲在热河行宫还没有回来,把整个烂摊子都交给他的弟弟去收拾。所以眼下亲王顶着个“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的头衔,是督率京内百官的最高军政长官。
行礼过后,他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七件章程、两件禀呈。以父亲对帝国形势的判断,几年折腾,朝廷已经穷得没什么家当了。一年前联军进占北京城,咸丰皇帝仓皇出城时能带走的压库银只有可怜的三十万两。眼下在亲王的整饬之下,京城秩序渐渐恢复,但财政的窘迫依然没有丝毫改观。南方的太平军像一只巨大的牛蛭一样附在帝国老朽的肌体上,不把它的血吸干不会罢休,而曾国藩领导的湘军只能靠自筹的厘金、捐输和少量的地丁银维持。帝国太需要新的财源了。
眼前这个英国人描述的前景,让恭亲王激动了。
父亲估计,当年英商进口商品的货值当在一亿两千万两以上,按百分之五的关税加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即使不计鸦片额外征收的重税,岁入也应至少在九百万两左右。但因为旧海关存在着大量的走私和胥吏腐败,因此每年只达到这个收入的三分之一,所以大有潜力可挖。他提醒恭亲王和文祥大人注意,这还只是在长江这一黄金水道因战乱形同废弃时的保守估计,一待南方战乱平息,重组海关,形成以上海为纽带,连接长江和沿海各口岸城市的一条T字形长廊,关税必将为帝国输送源源不断的财富。
亲王开始时还拘谨地在这个外国人面前保持着矜持,但当他听着这个外国人用一口蹩脚的中文如数家珍地报出各条约口岸城市的进出口数字时,他的脸色舒展了开来,神态也变得从容了。他向面前的这个外国人就海关事务询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并坦率地告诉他,自己完全不了解这些专门事务,对商业贸易也不甚了了,担任目前的职务完全是出于形势的发展和帝国利益的需要,要实现这一美好前景,他需要赫德先生的帮助。
父亲清楚地知道,南方那场持续多年的叛乱正让帝国高层深感头痛,对他们来说,太平天国和捻军这两支反政府武装是比西方势力入侵更严重的军事威胁。此时的西方各国都企图抓住这一机会,以帮助清政府消灭起义军为筹码来扩大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力。比如俄国提出了派遣一支小型舰队去轰炸被太平军占领的南京的请求,法国也表示要帮助朝廷购买一支装备精良的舰队。他的这些建议都是为解决政府财政危机提出的种种增加税收的办法。为了挠到亲王的痒处,他也临时提出了一个计划,按照这个计划,购买十二艘军舰所费不到一百万两银子,这些银子可以通过增收鸦片关税和在销售时加征货物税的办法来筹取。更重要的是,他向亲王保证,这些舰艇都将由中国水手来驾驶,中国政府有着绝对的领导权。此项建议果然引起了恭亲王浓厚的兴趣。此时他不会想到,此项建议后来在实施时会离自己的初衷越来越远,以至到了无法收场的局面,并最终让他的顶头上司李泰国灰溜溜地离开了中国。
恭亲王一直在听着他说,有时也会打断他提出异议。让他诧异的是,声称不懂贸易的亲王倒是认为低税率可能更会促进贸易的繁荣,而不赞成把税率调得过高。洋药税厘并征会不会让进口药的数量锐减?对外国轮船载运土货出口征税会不会导致出口量减少?他提出的这些问题都非常专业。而经验老到的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却看不到这一点,顽固地坚持高税率。这不由让他对亲王出色的领悟能力感到钦佩。
会面将近结束时,亲王表示,这几件关于长江沿岸通商事务的禀呈都将由总理衙门送呈在热河行宫的皇帝御览,相信不久就会有好消息。他向空气中遥遥拱手一拜,好像皇帝就在眼前,“臣等谨奏请圣裁。”
会见结束时,恭亲王又重提了向英国购买炮船一事,问他谁堪当此重任。他脑中陡然灵光一闪,一句话冲到嘴边:总税务司李泰国先生正在伦敦养病,由他来办理此事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会见时在场的总理衙门大臣文祥似有话要说,看恭亲王当即同意了这一建议,也就把话咽了回去。
逗留北京的最后几天里,他与恭亲王和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已经建立起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他常常一大清早就赶往东堂子胡同的总理衙门,和文祥一起用过早餐后,两人就开始从日出到日落的长谈。文祥长他十七岁,1840年通过顺天府乡试成为举人,五年后中进士在朝廷各部被派任过各种不同工作,四十岁那年正式出任军机大臣。是他在北京陷落后作为恭亲王的助手参与了与联军的谈判,并随后与恭亲王和桂良一起奏请设立总理衙门。他还有个大胆的设想是组建一支完全由西方训练的叫“神机营”的八旗精锐部队,以做北京城的卫戍部队。父亲觉得,这位北京政坛的权威人物既是个传统的学者,又是个现代化的热心倡导者,是总理衙门诸位大臣中最开明、最好相处的一位。
亲王有时也邀请他和总理衙门的几个大员到“绿天小隐”外的平台上喝
茶。那是亲王款待亲朋好友的地方,请他这个外国人来,算是破格的礼遇了。
这里是西苑的一部分,它的萃锦园是仙鹤、鹦鹉和鹰隼的乐园。坐在浓浓的树
阴下惬意地喝着茶,看金色的、黑色的鲤鱼飞快地穿梭在池塘中和从假山流
下的微型瀑布下,谈政治,也谈些海外异闻。他心头时常会掠过一阵自豪感,“有谁知道我和帝国最显贵的亲王坐在一起喝茶?”
除了公务,亲王也会和他谈一些轻松的话题。比如,他们谈到了对肉食的
共同喜好。亲王喜喝白酒。他酷好啤酒,也喜欢喝一点在宁波时学会的绍兴黄
酒。他们还提到过一种性子很烈的高大洋马,和敏感的中国小马不同,这种马
总是昂首翘尾,却不看去向,所以总是跑着跑着就迷了路。说到这种帅气的洋
马迷路时,一向沉稳的亲王抑制不住地放声大笑起来。
一次正在恭王府喝着茶,恭亲王让他起身,撩开他穿着的西服,饶有兴趣地探究开了西装究竟是怎样缝制成的。经过一番观察,恭亲王称赞他穿在身上的西装的口袋设计确实极为实用和方便。这段相处的时间不长,亲王的好奇心、极高的悟性和接受新事物的勇气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从公使卜鲁斯先生和参赞威妥玛[1]先生那里,他也侧面听到了恭亲王对他的评价,说对他有“最佳之印象”。文祥则说他“语多近理”、“人尚雅驯”,表示总理衙门把他看做“自己人”。看来他们对他的印象不坏,都把他看做是一个有才干、因有求于帝
国而恭谨的英国人了。有一天,卜鲁斯先生亲口告诉他,亲王居然还把他叫做“我们的赫德”!
离开北京前,他得知由他提议的由海关拨款开办语言学校同文馆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