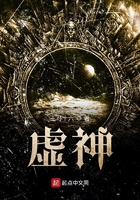接下来的十几天,赫德几乎天天都可以见到未婚妻,他们一起喝茶、闲聊、弹琴,她马上就要成为他的新娘,他有责任和义务去了解她。其他的时间,他全都泡在了家庭和朋友的活动上,日子过得简单而愉快。天气暖和的日子,他会花一整个上午陪着妹妹们玩槌球游戏,或者一种叫“草莓叶子”的游戏,然后又带她们去酿酒厂、磨坊这些他以前玩过的地方消磨时光。他是家中十个子女中的长子,他去中国两年后,最小的妹妹杰弗里才出生。现在妹妹们都长大了,除了杰弗里才十岁,夏洛蒂、卡西、吉米也都到了和他的未婚妻差不多的年龄。他陪着赫斯特·简小姐去都柏林,拜访她的两位姨妈,勃朗宁夫人和老处女布莱登小姐,还参加了当地世纪教堂的一个授圣职仪式。他们还一起去里斯本,去他大妹玛丽家喝茶,他们出席了玛丽去年出生的孩子的受洗仪式,以他的姓名命名了那个新生儿。在里斯本,他们还接受当地一个水果商的邀请去果园摘草莓和树莓。新鲜的草莓汁沾上舌尖时那种熟悉的味道一下让他回想起了在乡间度过的全部时光。那一刻,他仿佛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没有离开过家中的妹妹们,而已经逝去的十二年时光,就像是做了一个梦,醒来后,还是熟悉的乡村、熟悉的亲人。
那些社交界的活动,剧院啦,舞会啦,宴会啦,招待会啦,这段时间他都没有涉足。与前些时候在伦敦时的热衷于社交相比,他像是换了一个人,静静地待在拉弗内特和波塔当,好像在乡村刻意要保持一种内心的宁静,以便在不被打扰中享受人伦之乐。他也没有像那些在殖民地工作短暂回国述职或者度假的其他官员,趁机削尖脑袋往上流社会钻营,结识一个个高官和权威人士,以便晋升、调动或者获得十字勋章和爵位。这倒不是说他真的看淡了名利,不求闻达了,他只是不想把短暂的假期全都花到钻营上去,更受不了丢掉尊严在权力之间奔走。那些身居高官显位的人,可能表面上对你客客气气,一转身就会把你给甩了,即使通过取悦于他们获得了最低等的巴思爵士进入了所谓的上流社会,又有什么价值呢?他承认,得到十字勋章和爵位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但要是得不到这些,也没什么好不开心的。一个人不能样样东西都要到手,有所舍,才有所得,只有学会了放弃,才有可能得到更多。就像他现在,要是待在伦敦,或者和使团的人一起到处走动,那就不可能和朋友家人待在一起,享受亲情和友情带来的欢乐。
他想:我现在拥有生命、力量和健康,要不了几年,这三者都会离我而去,那么,我是为了那干瘪的面包而工作,还是为了那转瞬就被遗忘的人世间的浮名而工作?不,就把面包看成是干瘪的面包,把浮名看成是会被人遗忘的浮名,在追逐任何这样的蝴蝶时,都不要离开了正道。大胆地前进吧,你的眼睛应该盯住目标,那扇从这个世界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小门,努力工作,只有你的工作会伴随你到达彼岸。
“因此要甘于宁静,而不必闻达。”他在日记中写道,“在去中国之前,你还有好多工作要做,去做那些事,而不要为爵位或授予仪式之类的事使自己烦恼,现在去寻求它们,就像是打一局没有把握的牌,或者是一场不知敌人为何许人的战斗,却远离自己的后备力量,没有基地,只是依赖侥幸。重要的是按照桌上的明牌打好一局牌!”
什么是桌上的明牌?那就是他在中国的地位与影响,中国的海关和财政,甚至整个政府都离不开他。还有,他与这第一个来到欧洲的清国访问使团的特殊关系。他相信,这一张张的牌摆在那里,那些权威人士没有理由不知道他,他也可以轻而易举踏入他们的门户。但他不喜欢登门去寻求他们的认可,去请求授予十字勋章和绶带,那太掉价了,他要这一切不请自来,直接降临到自己头上。他试图从眼下要处理的一大堆事中理出一个头绪来。他打开桌上一封由包腊和德善共同署名的信,看了不由一阵心焦。
这是一封告状信。邮戳上盖着收到的日子是7月13日。这么说,自己这些天沉湎于温柔乡中,竟把这封重要的信件耽搁了两天?信中报告了这些日子以来使团的行程和所到各国的会见参观等情况。在参观了英格兰北部的工厂区和伯明翰棉纺厂后,使团离开英国前往荷兰,从哥本哈根又前往斯德哥尔摩。在罗列以上这些后,信中说,他们“对斌椿及其作风极感厌烦”,他不顾安排一意孤行,还尽提些无理的要求。信的末尾是包腊和德善的共同签名。
该怎么办?是支持他们,还是支持斌椿?赫德觉得自己被抛进了一个进退维谷的窘境。的确,包腊处事机敏,德善为人忠厚,在海关工作时就很得他的赏识,他当初从海关职员中选了他们两人随团出行,就是想将他们好好历练一番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去。可是斌椿真是他们说的那般不堪吗,无知、自大、自私自利又不可通融?平心而论,他对斌椿的印象还是不坏的,相处也是愉快的,尽管这人有些迂腐气,但还算是个明智之人,做事也干练。他对这两个手下老是拿使团内部的矛盾来让他裁决,越来越感到恼火。他认定,这两个人对斌椿有曲解。一个人要曲解别人是非常容易的,不管是有意还是无心,即便一个没有私心的人也会因为愤怒或自命不凡对事件作出歪曲的陈述,更何况一边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一边是六十二岁的老人。自己怎么可以偏听一面之词,把要事撇在一边?
想到下一阶段在中国的事业,他的思路越来越清晰。他拿着一支铅笔,把急着要办的事和预期目标在纸上罗列了开来:
1.由中国政府派遣官员去欧洲,这一点我已获成功;2.让欧洲各国政府接受这些官员,并且友善地对待他们,这一点上获得的成功超出了预期;3.促使欧洲人对中国人感到满意,并且对他们有更大的兴趣,这一点我也已成功;4.使中国官员带着对外国的愉快回忆离开,这一点迄今为止也已获得成功,只是使团在欧洲的时间过于短促,很难说他们得到了多少实质性的指导和帮助。还有几项目标,他觉得为期尚远,要采取必要的步骤才能达到。比如让斌椿一回到中国,就出任堂官,即外务部长,使政府在他的帮助下开始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文化;劝导中国派遣大使出国,与西方各国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系;等等。正是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几年来孜孜不倦地努力,才有了这第一次出国的使团,难道现在自己竟然成了一头蠢驴,由于狂妄、轻率和考虑不周,把事情全都弄糟了?
他继续想下去:斌椿当然也有他自身的缺点,可是谁没有缺点呢?如果拿住这一点做文章去反对斌椿,可能会成功,但这样一来,这次出访就完全失败了。要是不成功呢,与斌椿之间的仇就结下了。不管成与不成,以后的各项目标要实现起来都会更加艰难。而且凭经验,他断定如果这种冲突公开化后,北京方面只会支持斌椿而不可能来支持几个外国人。意识到这一点,他作出了一个实用主义的决定,支持斌椿。“愚蠢,实在是愚蠢!”他把包腊和德善寄来的信狠狠揉成一团丢进纸篓。他决定不去理睬他们那些琐琐碎碎的争吵,把屁股完全坐到斌椿一边来。“工厂的机器发出噪声,但是如果为了消灭噪声而将机器关闭,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得到布匹呢?”
要实现目标,使团和斌椿就是他的船,现在船已经启碇开航,航程已经过半,他如果还要继续前进,就不能放弃这条船。他的打算是,让斌椿继续保持他的品性,什么都不用改变,惟一改变的是让他在使团内部掌握尽可能大的权力,并且把这个以前的下属视作真正的朋
友与之交往。就让他先去占着上风吧,只要不像野马一样脱缰奔突不听使唤就好。至于包腊和德善,他觉得有必要腾出一只眼睛来把他们给盯紧了。“不论在需要最普通的常识还是需要机智的地方,他们都不合适:他们既不能见机知微,也不会随机应变,实在太令人失望了。”
接到赫德新的指令后,使团再无纷争。整个7月,使团在欧洲大陆继续余下的行程。他们乘坐火车,从一个城市赶往另一个城市。从斯德哥尔摩到圣彼得堡,他们坐了三天半的车。尔后,他们坐火车去了柏林。“七星期战争”已经结束,德国人忙着庆祝胜利,几乎没有留意到这些来访的东方客人。有人建议使团应该看看鲁尔的工业区,于是他们在7月24日离开柏林前往埃森。德善此时已结束假期回来,包腊终于得到了三个星期的休假。
就在使团离开柏林的同一天,赫德离家前往苏格兰东北部的阿伯丁[1]访问。本来7月初的时候他已准备去阿伯丁看几个朋友,但因那段时间刚结束东奔西跑回到乡间和未婚妻待在一起,他觉得为了聚会几分钟却要花去几天时间旅行实在是浪费,就取消了行程。此一时彼一时,当狄妥玛再度向他发出邀请时,他就向那座到处是花岗石建筑的城市出发了。
行前的晚上,他在拉弗内特的家中给未婚妻写了一张便笺,告诉她除了
“天朝”的事他要操心,还有别的一些恼人的事,为了在回中国之前把这些事都处理好,他要外出很长一段时间,可能要三个星期,也可能更长些,但最迟会在妹妹夏洛蒂的婚礼前赶回来。
他要她为下个月的婚礼做好准备。“今天我满脑子都塞满了工作,没法给你写一封情话绵绵的信,我离开后你务必写信给我,来信地址是伦敦阿尔比马尔街七号的皇家帆船俱乐部。”他告诉她,不论多忙,他的心中一定会有她。
第二天,他到了里斯本,担心赫西因前一封信里说到的“烦恼事”焦虑,又发出一信,特意说明,这“恼人的事”与婚事无关,而是一些家务事,父亲生意上的一些事需要他插手。“我亲爱的,就我来说,没有什么事能阻碍我们的结合。”他的嘴巴像抹了蜜糖似的,一会叫她“我的甜蜜的宝贝”,一会叫她
“我最爱的小姑娘”。他告诉她,和她分别是一桩多么难过的事,让他更难过的是要有三个星期看不到她。“我真的希望能够带你走,在8月22日完全拥有你。在我能够有权利带你一起到我必须去的地方之前,我不想再多待一天,亲爱的,请为那个日子准备好,我也尽力将我的事情准备好。”
一路上他发出了许多封信,向家乡的未婚妻报告行踪。
渡海到格拉斯哥[2],度过一个美丽的夜晚后,他和狄妥玛一起去阿伦桥。他们驱车去东恩宫堡看了玛丽皇太后睡过的床榻,以及哲学家休谟慌不择路逃逸时穿过的窗子。他还在城堡庭院里采了一枚“蓝绵枣儿”要送给她。阿伦桥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地方。阿伯丁这个城市看上去非常整洁,房屋高大而且宽
[1]阿伯丁(Aberdeen),英国苏格兰地区的主要城市之一,位于苏格兰东北部,北面的顿河(River Don)与南面的底河(River Dee)的河口之间,是北海海滨的主要海港。[2]格拉斯哥(Glasgow),苏格兰第一大城与第一大商港,位于苏格兰西部的克莱德河(R.Clyde)河口。
敞。他的感受是,苏格兰远远胜于英格兰。几天后,在拉格比的一家老式英国旅馆等候开往伦敦的火车时,为了挨过近两个小时,他又给“亲爱的小姑娘”写信,告诉她分手后的这一个星期里,他坐下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她。这个即将走向婚姻的男人,一路上频繁地写信发信,好像要编织一张爱情的网,把对方装进去,也把自己装进去。他这么做是出于对无爱婚姻的恐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