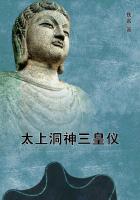她当然知道那老和尚和介东风有交情,也料定了那老和尚一定会跟介东风提起这事,故有此一问,看来这老和尚挺闲的,倒是可以让他进宫给陛下做个饭。
这介东风也是,若说他聪明,他总是这么诚实,若说他傻,平常看他,又滑得跟泥鳅似的,想抓都抓不住。
沈爰对于凶手一事,提都没提,只是笑,“昨日本宫遇刺,那就证明了本宫行踪被人知晓,可是到底是谁有这么大本事能探得本宫行踪呢?况且昨日本宫与令公子在一起竟然遇刺,那幕后黑手摆明了要把本宫行踪泄露一时嫁祸给令公子,而本宫不顾安慰护得令公子无恙,在他眼里,你们介家是不是已经和本宫站到一条线上了呢?”
这一点,介东风自然是清楚的,他也不为介渺开脱,只道:“臣愿报殿下恩德。”
听得介东风此言,沈爰笑道:“你报的不是本宫的恩德,而是陛下对你委以重任的信任。”
介东风明了,原来,是皇家和姜家的斗争要开始了。
沈爰缓缓捡起了一块地上碎裂的茶杯瓷片在手中把玩,“而今,姜家势大,朝中姜家走狗众多,就连得陛下圣眷恩宠的花家都有依附于姜家的嫌疑,陛下正是需要像介中书这般一心为国的臣子助他整顿朝野,本宫和陛下也自是相信介中书,就是不知介中书对陛下是否忠诚。”
介东风忙道:“臣对陛下之心天地可鉴,为国为君万死不辞。”
沈爰轻轻倚在身后桌子腿上,闻言,神色也无变化,依然是哪淡笑的模样,“本宫近日得闲,想在贵府居住,不知介中书意下如何?”
介东风心中盘算,这长公主出现在明月洲带回他家儿子,一来一回就需要个把月,而他因为介渺失踪昨日还去宫中试探了长公主,可见宫中那位并非长公主本人。
可是长公主本人又何尝猜不到,介渺失踪,他会怀疑这事儿是她预谋来威胁介家,进而去进宫试探她。
长公主如今出现在他面前,光明正大的告诉他,她是从明月洲回来的,等于堂而皇之的告诉他宫里那位是假的。
而她说要在介府居住,恐就是暂时不会回宫,要在宫外做些事。
可既然要做事,这京城之大,住哪不行,偏要住介家,如此定然是有一些事需要依仗介家的声威,可若真是如此,那就需要一个光明正大的身份。
如此秘事让他所窥,这也是摆明了要拉介家上她的船,还是不上也得上的那种。
恐怕他不上长公主的船,今日都不可能平安出得了这书房……想到这他悄悄看了眼沈爰手中把玩着的茶杯瓷片,瓷片锋利……
沈爰注意到介东风的目光,也只是淡笑着不言语,耐心的等着介东风把她话里的意思解读完。
半晌,介东风深深一拜,“臣记得家族旁系有一位族嫂,其丈夫已故去多年,但她曾有一子出生不久就不幸夭折,此族嫂住在偏远山村,无夫无子过得清苦,臣愿将她接回好生相待。”
听得此言,沈爰心情很是愉悦,“介中书做事,本宫自然是放心的。”
她本就是此意,如今柳行色代她待在宫里,她正好可称此机会做些事,而今她只需要一个在京城横行的身份。
这身份不能太高,太高则引人注目,当然也不能低,太低则不好办事,介家旁系子侄就是个好选择,出身不高,不会平白让人忌惮,也因背后有介家,不会有人招惹。
这也是她明明有花家玉佩,却不借助花家长孙的身份来行事的原因,花家圣眷正隆,且三房长女成了宫妃,三房定是会仗着溶妃之势和花老夫人争产业,若花家孙子忽然归家,花老夫人定是会把孙子推出去以继承家业,到时候花府之中一翻争斗,而她也会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到时候众人视线之下又如何行事。
而选择介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彻底和介家绑上,这根绳可还是根铁磨火炼都烧不断的。
沈爰放下手中把玩的碎瓷片,从此后,她又多了一个身份,介家旁系子侄,还会多一个母亲,便是介东风的旁系族嫂。
沈爰站起身,理了理不合身的衣服,“待人接来,介中书可去往来居送个信,本宫这便走了,介中书也莫要跪了,免得伤了腿脚。”
临走前沈爰又丢下一句话,“令四公子武功颇好,记得不错的话,年后好像有武试。”
到这她也没再往下说,就让介东风自己去解读吧。
出了介府,沈爰看了一眼介府对面朱红大门上鎏金镀银的花府匾额,抬手戴上了帷帽。
她骑马直接去了往来居,往来居是南陵京城一个颇是优等的酒楼。
此时,往来居二楼的一个房间里,沈爰已拿下帷帽,翻着手里最近京城发生的事,脸上却似笑非笑的,“曾凡几啊,鼻屎好吃吗?”
桌案前站着一个长身玉立的长衫男子,看起来颇有些书生的斯文气,可跟那城门口抠了鼻屎又抠牙的乞丐判若两人。
曾凡几面上很是有些不好意思,“属下也是无可奈何才会出此下策啊。”
沈爰用下巴示意他坐,等到曾凡几坐了下来,她才开口问,“说说吧,你们在搞什么名堂?”
曾凡几正了神色,“属下们是好几个月没接到主子送来的消息,担心……担心主子是不是被姜太后神不知鬼不觉的……嗯……”
沈爰气笑,“你们是觉得我有多笨,能被那太后神不知鬼不觉给的弄死了。”
曾凡几接着道,“属下听你说过,皇宫的守卫晚上要比白天严密很多,正好那日发现宫中有采买司的人出宫,属下就想着混进宫去看您。”
“你是想看看我是不是还活着吧。”沈爰接话。
曾凡几抬头望房顶,不看沈爰。
沈爰猜测,“然后呢?被发现了?”
“是,属下没见到您,就去见了皇后娘娘,结果皇后娘娘也说,她已经好几个月没见你了,等属已经走到皇宫门口的时候,忽然被姜三公子叫住,属下心里一慌,就跑了起来,本来属下还以为没命回来了,没想到居然逃了出来。”
“这么短的时间内,你是哪里找的烂衣服?”
曾凡几一笑,“自然是属下去之前就想到了这种情况啊,把衣服里穿了件破烂衣服,属下觉得若真是出了什么事情,乞丐堆里还是比较好混过去的,所以属下很有先见之明的这么穿了。”
沈爰点头,“皇后娘娘可还好?”
闻言,曾凡几忽然有些担忧的看着她“你是和皇后娘娘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了吗?为什么突然几个月都不见她了?你们不是一起长大的吗?你们不是亲如姐妹吗?你回南陵不也是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皇后娘娘吗,你……?”
“停,停,停。”沈爰制止了他的问话,这个曾凡几,别的毛病没有,就是太啰嗦。
“我跟她没事,会去见她的。”
曾凡几又想说什么,沈爰阻止了他,就怕他说起来没完没了。
“你去拿一些伤药过来,昨日我受了些伤。”沈爰总觉得伤口在揍姜践的时候出了血。
曾凡几惊得一下子站了起来,“主子你受伤了?我说我怎么闻到了一股血腥味儿,到底严重不严重?在哪受的伤啊?是谁伤的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沈爰无奈,“你在不去拿药,你主子我可就要疼死了。”
曾凡几听了赶紧跑去拿药。
两盏茶的时间不到,曾凡几就跑了回来,搬了整整一箱,还拿了身衣服。
沈爰无奈,这箱子她也认出来了,还是她用来装书的。
曾凡几一瓶一瓶的往外拿,边拿边介绍,“主子,这瓶是生肌的,这瓶是祛疤的,这瓶是美肤的,这瓶更好,是生肌带祛疤的,这瓶……”
“停,停,我又不是不知道。”沈爰听的发晕,她很怀疑如果她不阻止对面这人说下去的话,这人有可能把所有药都给她介绍一遍。
她自己挑了一瓶。
曾凡几又问,“要不要找人来帮你上药。”
“不用了,我自己来就好。”
“主子啊,你下次再出宫可要保护好自己,要是让王爷知道了,王爷会很伤心的,不仅是王爷,王妃知道了也会伤心,世子知道了也伤心,属下们也伤心,这么多人都为你担心,你下次可不要在这么不小心了。”
沈爰咬牙切齿,你能不能不要在说了,怎么她受个伤,还让她觉得,她一下子对不起了一大堆人。
她有气无力的开口道,“好了,我知道了。”
曾凡几一张嘴一直吧啦个不停,“我还没说你呢主子,你这是哪找来的衣服?这么不合身,衣摆短,袖子也短,这么难看,主子你居然就这么大摇大摆穿出来了,让王爷王妃和世子知道了你这么不会照顾自己,他们会担心的,皇后娘娘也会担心的。”
然后又拿起了他给沈爰拿来的衣服,“主子你看属下拿来的衣服,还是属下拿来的好看,主子你穿男装的时候还是穿白色最好看,皇后娘娘也这么说过,皇后娘娘说你……”
“停停停。”沈爰再听下去,很难保证自己会不会去上吊。
沈爰抓着药瓶站起身来,“好了,你先出去一下,我要去上吊……啊,不对,我要去上药。”
沈爰把上药两字加了重音。
无奈,曾凡几还是听到了那上吊两个字,他一脸惊讶的看向沈爰,“什么?主子你是不开心吗?有什么烦心事吗?发生了什么事能让你想去上吊?你可不能真去上吊啊。”
沈爰握紧手中药瓶,又重复一句,“我说我要去上药。”
曾凡几蹙眉,“难道我听错了吗?我不可能听错啊?我怎么可能听错呢?”
沈爰深吸口气,“对,你听错了,我要去上药,你还不走,是想留下帮我上药吗?”
曾凡几摸了摸头,转身往外走,嘴里还碎碎念个不停,“我听错了吗?不应该啊,我明明听到主子说要去上吊的。”
曾凡几出去关好了门,沈爰反而躺在了地上。
躺在地上歇一会儿,听他讲话累的很。
躺了一盏茶时间,沈爰站起来往里间走,轻轻解开外衣,果然,除了外衣还没浸透,里面的衣服沾的都是血。
最里面的衣服粘在了伤口上,她轻轻往下撕,扯着皮肉,疼的直皱眉。
换了药,换了衣服,沈爰拿着帷帽走出去,曾凡几还在门外等着。
“主子,你是要回宫吗?”
沈爰摇头,“先不回,我去一趟明月楼。”
曾凡几惊讶,“什么?去明月楼干嘛?”
沈爰未答,只道:“我先走了,如果我不回来也不用去找我,没事也别往那边跑,尽量别让别人知道这两家店有联系。”
曾凡几点头。
沈爰没走正门,干脆找了个窗户跳了下去,主要是懒得走下去,楼梯一层一层的也太麻烦。
明月楼。
明月楼其实就是青楼,还是京城最上等的青楼。
且明月楼只有艺伎,只卖艺不卖身,吟诗诵词,弹琴唱曲。
自来就有天下才女皆出明月楼的说法。
多为达官贵人,风流才子流连之地。
明月楼里明月在,吟诗作赋出人才。
明月楼中出好诗亦出才子。
也有不少家中无门路,但有才华的读书人会来此,大都想凭自身才华来搏个名声,以借明月楼来传扬。
而明月楼如此之盛,这么多年无论是京城地痞,还是朝中权贵,都无人敢在此生事,有传说这明月楼背后是诚王。
伊天阁怎么跟诚王有关系,她想不明白。
诚王便是当今南陵陛下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