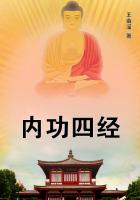容若微笑道:“我也想萨仁叔啊,尤其是萨仁叔的糖炒栗子。”
萨仁呵呵笑道:“老奴炒了好些栗子,都搁在少爷的房间里了,少爷夜里读书累了,当零嘴嚼一嚼也好。”
小福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机灵得像个小猴头似的,接过容若的包袱,朝萨仁鬼笑道:“萨仁叔,少爷刚回来,你就让他耳根子清静一下吧,省得被你唠叨得耳朵生出茧子来。”
萨仁在小福头上敲了一下,瞪眼道:“你个小家伙,少爷才不会和你一般。”说罢又转头对容若笑道:“少爷,老爷和夫人都在屋里等着您呢,夫人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的好菜,老爷也是沾了少爷您的光才能享受到这等口福呢。”
容若随着萨仁和小福入内,重门深闭的院内曲折迂回,容若穿过几扇月门庭院,忽现一片潋滟水光。临水山石玲珑,回廊蜿蜒如带,漏窗透出青竹碧枝。林荫水岸藤萝蔓伸,古树苍苍,巧妙地将水色山石连为一体,雅致古拙,衬着白墙黑瓦延绵,不知几许深远。
容若步入一处厅堂,推开朱门,就听得一个暖软的声音迎面拂来:“容若,终于回来了,让额娘好好瞧瞧。”
迎面走来一个三十中旬的女子,一身锦绣旗装,宫髻高绾,珠翠玲珑,举手投足间透着一股高贵明丽之气,岁月光阴在她的脸上似乎并未留下丝毫痕迹,她依旧美丽得犹如世外仙人。此人正是容若的额娘,爱新觉罗懿贞。
容若任由懿贞拉扯过来,仔细端详,在额娘眼中,他偏生像个长不大的孩子一般,容若只是无奈笑笑,便拉着额娘的手一同坐下,耳听额娘责怪他出门在外不懂得照顾自己,心里却十分温暖。
一旁纳兰明珠只是喝酒,连话都插不上,等娘俩谈完心,他才拈须道:“这是容若第一次出远门,对他也算是个历练,能为皇上办事,也是这小子的荣幸。”他微笑着看着儿子,眼中颇是赞许之意。
懿贞坐在容若身边,不冷不热地道:“我宁愿容若待在我身边,也不愿让他参与朝中那些是非恩怨、明争暗斗,容若是个干净的孩子,官场并不适合他。”
明珠反驳道:“妇人之见,整天待在家里能有什么出息,是男子汉大丈夫就该出去闯荡,求个功名。”
懿贞道:“我可不愿容若变得像你一样世故圆滑,朝堂上那点事,说穿了,就是掌权者的勾心斗角,容若性子纯厚,心地善良,要他与虎狼打交道,我又怎能放心。”说罢对容若露出微微一笑,给他倒酒夹菜。
容若看着额娘,正色道:“额娘,孩儿是真心想要辅佐皇上,铲除奸佞,还天下一个清明政治。”他目光灼灼,懿贞看在眼里,默默叹了口气,道:“你这孩子,从小志气就高,额娘只盼你在外凡事多留个心眼,好好保护自己。”
容若呵呵笑道:“额娘,这次出门在外,孩儿结识了一个好朋友,她也对孩儿说过这样的话。”他又想起沈宛,他出宫后天色已晚,沈宛若与自己一同回府多有不便,他便托人拜托睿琪,让沈宛在她的府上歇息一夜,打算明日便让她来家中做客。
懿贞不动声色地笑了笑,道:“容若长大了,多结识一些朋友也是应该的。”
明珠却道:“容若就是太爱交朋友了,平日里和那些汉人学子走得太近,你那些个朋友有麻烦,哪次不是你去解决。鳌少保一向最讨厌汉人蛮子,认为研究汉人那些个歪理儿,难成大器。你可倒好,对他们的学问比对老祖宗的法制研究得还透彻。”
容若不服气地道:“要是孩儿有能力的话,倒想劝劝所有的满人都来念汉学,马背上打下来的江山,不能在马背上治理,如何让国家强盛,让百姓安居乐业,答案全在书里边,皇上就和孩儿一样,也很喜欢汉人的学问。”
明珠知道自己辩不过儿子,索性喝了口酒,道:“这些话你在家里说说也就罢了,到外头可莫要乱说,听说鳌少保最近正在抓一些读书人的把柄,你可别出了风头,却犯了禁忌。”
容若知道鳌拜一心想要拉拢阿玛,阿玛虽对鳌拜恭敬,却也不敢于他走得太近,这朝里头的风浪一来,指不定哪一条船会翻,明珠深谙世故,自然知道其中利害关系,若要明哲保身,不上船则是最安全保险的法子,因此在朝廷看不见的斗争里,他一直都处于中立。
容若双目炯炯地道:“阿玛,你怕鳌拜,孩儿可不怕他,他的势力再大,也不能一手遮天,满清天下的权柄,不是握在他一个人的手里。”
明珠无奈地叹了口气:“你这小子,心气还是这么高,年轻人锋芒太露可不是什么好事,你得改改你的性子才行。”说罢摆了摆手,“今日就别谈这些话题了,你离家这么久,阿玛和额娘都想得紧,今日若不是托你的福,阿玛哪有机会吃你额娘亲手做的菜。”他笑呵呵地夹了一个四喜丸子放在嘴里,吧唧吧唧地吃了起来。
容若也只好把话吞回肚子里,乖乖吃饭,其实他心里明白,面对朝堂上那些斗争,阿玛应付起来并不轻松,他不得不同各方势力斡旋,为的也只是保全纳兰家。阿玛年纪大了,顾忌的太多,或许等自己到了他的年岁,也会磨平所有的棱角和锋芒。
然而现在,他却无法认同阿玛的做法,在他的眼睛里,是与非,黑与白,从来都是鲜明而对立的,他绝不可能将其随意混淆,或是视而不见。
第二日一早,康熙身边的贴身小太监小路子就悄悄来到了纳兰府,领容若入了宫。容若心中隐隐猜测,或许又出了什么大事。
果不出容若所料,他在养心殿等到辰时,就见康熙怒气冲冲地进了御书房,一进屋就把一方奏折撇在了地上。
容若捡起那奏折一看,才知折子是鳌拜承的,折子里说汉人学子庄廷龙、查继佐、陆健等人列明参校私刻《明史》,这些人都是前朝豪贵、江南名士,而《明史》一书中补写了前明崇祯一朝,据实记载了满洲的崛起及其入关后对汉人的屠戮。鳌拜便在《明史》一书上大做文章,说这些汉人勾结谋逆,非要将他们一并抓获,治以重罪。
康熙来回踱步,忿忿地道:“今日早朝,鳌拜联合遏必隆、班布尔善等人一起上疏,言之凿凿地说这些汉人以文字造反,要大兴文字狱。《明史》一书抄录出广者甚多,若真的兴此大案,牵连必定甚广,到时候又免不了一场流血的浩劫。大清的根基才刚刚稳固,朕实在是不想再让百姓流血了。”他的目光越来越严峻,眉间的痕迹犹如刀刻。
容若回想起昨晚阿玛的一席话,看来鳌拜最近真的在抓汉人学子的把柄,阿玛也定是事先得知了消息,才让自己少管闲事,以免惹祸上身。
康熙见容若蹙眉沉思,轻声唤道:“容若,《明史》一书朕也看了,里面本无谋反的言论,此次也是鳌拜一党无风起浪,一方面想由此打压汉人学子,一方面更是想要煞住朕的气焰。朕想要承袭皇阿玛满汉一家的思想,真的不想对汉人大开杀戒,更加不会向那几个老家伙低头服软,这一次,能帮朕的,恐怕也只有你一个人了。”
容若紧握着奏折,感觉自己的心也如同这奏折一般,被一只看不见的大手紧紧攥住,脱口道:“皇上,您尽管放心,微臣定当全力协助皇上。大清入关十多年以来,已兴了数次文字狱,江南哭庙案、奏销案、通海案,昔日这些冤案已掀起了民间百姓的怨愤,长此以往,恐非治国良策,如今皇上在位,大可以替这些无辜的汉人学子做主,将先皇满汉一家的思想发扬光大,如此才能彰显皇上的英明。”
康熙走过来,拍着容若的肩膀朗声笑道:“不愧是朕的好兄弟,朕就知道,你一定会帮朕。”
两人对望一眼,相视而笑,眼中全是默契与信任。
这时,门口忽然传来了小路子惴惴不安的声音,透过御书房的大门直传了过来:“鳌少保,皇上他正在御书房看书,外人不便打扰,还请鳌少保留步……”话未说完,小路子便哎呦地惨叫了一声。
只听一个粗犷的声音如平地惊雷,炸裂开来:“你一个狗奴才,居然敢阻挡我,滚开。”
下一刻,御书房的大门应声而开,门口出现了一个铁塔般的身影,迈开大步径自走了进来,只是几步就来到康熙身边,微微行礼打了个千。
来人正是鳌拜。
一脸浓密的络腮胡子装点修饰出他刚劲突出的长方下巴,有棱有角轮廓鲜明的面庞上满是煞气,一双威严的鹰眼里光芒沉沉,隐隐露出一份睥睨天下的傲气。
康熙背过手去,俊颜一沉,也没给鳌拜好脸色,道:“鳌少保来御书房所为何事,今日朕有一些累了,若鳌少保有事,就留着明日早朝再议吧。”
鳌拜对康熙的不耐烦却全然不予理睬,昂头道:“皇上,骂我们祖宗的书不烧,骂我们祖宗的人不杀,我们还哪里有脸活在这世上?那些不识好歹的蛮子,得让他们知道厉害才行,先帝对他们实在是太宽大仁慈了,就连响应正郑成功攻金陵的叛臣叛民都不肯问罪……如今这天下已是皇上的了,皇上万万不可放任这些蛮子胡作非为,否则大清的江山,迟早有一天要毁在他们手里。”
康熙极力克制心里的愤怒,脸上却不动声色地笑道:“鳌少保言重了吧,区区一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能成什么大患?若真与他们计较,倒显得我满人小家子气了,岂不让他们平白笑话?”
鳌拜眼神里一抹寒意无声地掠过,刚要开口反驳,突然瞧见了康熙身边的容若,纵声笑道:“这不是明珠家的小子吗?果然是一表人才、英俊不凡,久闻纳兰公子是我们满人的第一才子,我一直以为你是个病弱书生,今日一看,身子骨倒还挺结实的吗。”
容若眉头一轩,斜眼朝鳌拜看去,满脸的倔强不服,冷冷地道:“鳌少保过奖了。《明史》一案皇上自有定夺,鳌少保是辅政大臣之首,要忙的事一定很多,何必为了区区一桩《明史》案劳神费心,若因此累坏了身体,又有谁来辅佐皇上料理政事?”
接到容若挑衅的目光,听到他言语中的讥讽,鳌拜不悦,他权倾天下,满朝文武谁人不对他毕恭毕敬,就连小皇帝都要敬他三分,谁知这毛头小子竟敢对他如此无礼,心里念道:“好你个臭小子,破坏了我一手策划的武林大会,又抓了我的侄子,你老子尚且不敢在我面前放肆,今日我倒要看看你有几条命!”于是冷哼一声:“纳兰公子才名远播,却不知武艺如何?可否让我见识一番?”
康熙心里一寒,唯恐鳌拜借机伤害容若,刚要制止,谁知容若已爽快地答应了。
鳌拜眼中凶光一闪,右手掌形如刀,向容若劈面打去,同时左手指节屈伸,巧施擒拿之术,拿向容若腰际。
容若眉目一凛,纵步上前,他知道鳌拜乃是满洲第一勇士,力大无比,在武学一道上的造诣更是非同一般,不敢直撄锋芒,于是使出一招星罗散手,长拳短打,将鳌拜那一拳给逼了回去,同时飘身而上,绕过他的擒拿手,在他周身旋转呼啸,抢先发招。
刹那之间,容若与鳌拜已然交上了手,拳来脚往,斗得难解难分。康熙在一旁观战,起初还暗暗为容若捏一把冷汗,但看容若的动作轻灵无方,游刃有余,反倒为他鼓起了劲,暗暗希望容若快些胜过鳌拜,好杀一杀他的威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