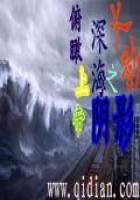青霭起身自斟一杯茶,一饮而尽,又斟一杯递送到沈冲天手中。
沈冲天低头闻一下,苦笑道:“此事堪配酒。茶,太清淡,不对味。”接着他听见青霭不发一言,脚步渐远出了屋子,关上门。屋子里寂静一时,终于出现开门声,青霭复又进来递到他手中一件东西,是一个酒盏。沈冲天道:“多谢!”举起一饮而尽。
青霭这才讲述道:“我住的客房靠近西院墙,最先知晓颖园状况。那日我在内间调息打坐,下人疾跑进来说颖园起火。我还只当你们不小心,急忙出来一看,竟是天火!颖园不会无缘无故自行燃起天火,定是出事了。我赶紧让人去云烟那里传信,自己来不及走大门,直接先翻墙过去。就看见三三两两的下人朝大门方向跑,老幼妇孺都有。我拦住她们询问,这些人七嘴八舌地说,她们被火和烟逼迫出来,园子中间你的卧房位置火势最大,所有精壮下人全部赶去里面救火。我担心凡人扛不住天火,忙向里冲进去,遇到救火的下人,团团围住你的住处,将一桶桶的水泼向火,却如同浇油,火越烧越旺。我让他们快去逃命,自己靠着避火诀进入屋子。”
青霭回忆着当日情形,沈冲天听着,黑茫一片的眼前,景象倏忽闪过:“当时慌乱成一片,我没注意纵火行凶之人,也许早离开了。半空中弥漫着浓重的黑烟,遮天蔽日。还记得莫牢山的白雾吗?一样遮蔽着四围,看不见两步远的地方,分辨不出日夜。颖园当时就是那种感觉,只不过白色变成黑色,夹杂着四迸的火星,飘舞的浓灰。园子里每一棵树,每一处房舍都在着火,亮白色,闪电一般的火,晃着眼,燎熏着身体。人在这种亮与暗交杂的地方行走,鼻子里、喉咙里呛满浓烟,掩盖住人们嘈杂的哭号喊叫声,只剩悠悠一丝飘荡在呼啸的风声和巨大的“噼啪”燃烧之声中间。我不知道酆都地府是什么样,想来也不过如此吧。”
“天火应当是从你的卧房里开始燃烧的,屋子已经被火围城一个密实的牢笼,里面的火势已渐小,烟势却更浓,烧的也比外面更干净,明显是要灭迹。屋门内外横七竖八有几摊人形的黑灰,就像一个人身体蜷曲的形状,依稀可见几件首饰夹杂在灰里,至于其他的,什么年纪、男女、模样,哪还有模样,全看不出来了。你在最里面,离你最近的三个女子,明显都受过重伤,诧异的是,连同你,身上全都没有火……”
“是丹药……”沈冲天喃喃低语:“我给他们服过除病避灾的丹药。”
“这就对了。”青霭继续说:“我逐一检查,两个还有心跳,一个什么都没有了。你面朝下伏在地上,人事不知,触不到气息,倒还有微弱的脉搏。你身上有神识残留的痕迹,就如踏雪留痕,人已去,痕迹不肯去。肯定不是你的,我急忙开天眼寻找,魂魄已散,只剩比火星还小的些许,没用了。哦,对了,你的枕下……”
青霭边说着边起身,走到沈冲天床头,在枕头下面摸了摸,找出个东西攥在手里,另一只手握住沈冲天的手,摊开他的手指,将手里东西放到沈冲天手中,又将他的手指轻送回蜷,莫使掉落。这才轻声言道:“我见你伏在地上,将你身体反转时,掉出来的。原谅我自作主张将它藏在你枕下,这东西,给他们看也无用,不如留给你吧,抱歉只找到这一个。”
沈冲天摸索着,是一只耳坠,形状十分熟悉。他将耳坠轻握于手心,放在唇边轻吻。
青霭歪头注视着沈冲天的表情,复又到桌前,斟了第二杯酒递给沈冲天。
沈冲天不说话,一饮而尽,却被呛到,朦胧的双眼滚下热泪。
青霭惋惜道:“可惜我修为不高,只会调用凡间河海之水,浇不灭天火。后来云烟带人过来,但是她也无能为力,我两个眼睁睁看着颖园被天火夷为平地。”
“几天前,那个叫绛纹的丫头先一步醒过来,说事发当日,忽然就闯进一个白衣男子,上来就将方馨儿和凝香抓在身边,应当就是冷翼。后来你回到家,与冷翼对质,说了一堆奇奇怪怪的话,冷翼放了你的妻妾,你将她们都关在门外,还让大家回到府里来,说这里安全。可是事发突然,所有人一下都慌了神,等大家都反应过来,想到你独自在屋子里对付冷翼,又放心不下,正犹豫间,就觉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
说完,青霭看着沈冲天,他忽然变得很平静,眼泪没有了,表情也没有了,满脸平静地让人害怕。这个时候,难道不应该悲切、哀伤、愤怒、无措……反正不应该是平静。
沈冲天终于说话,语气十分平缓低沉:“九公主,多谢你当日及时赶到。我房中还找到什么东西没有?”
青霭惋惜道:“烧得差不多了。只寻回来一只黑色的螺钿匣子,一柄剑,一只乌金耳环,一条软鞭,一只萧,再没有了。”
沈冲天嘴角一翘:“匣子是无怨大哥送我的,竟能避天火,看来也不是俗物。足够了,该有的都有了!剩下身外物,烧就烧了吧。”
青霭顿觉诧异:“啊?!”
沈冲天平静地说:“多谢你告诉我这些话。我心里舒服多了。”
青霭忙接话:“你,你千万别灰心,人死不复生,物去还能再来,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啊!是你说的,身负大恩与大仇,如今好容易得了命,要完成更重要的事情。”
沈冲天循着声音扭头:“你觉得我心死了,要去寻短见是吗?”
青霭越来越不放心:“不是吗?不行,我还是叫人来,日夜看着你吧。”
沈冲天摇摇头:“我既已活过来,为何还要去死?”
青霭望着沈冲天,胆怯道:“你这反应太吓人,不正常!我不相信,出这么大事,就凭听几句话就能释怀?”
沈冲天反问:“谁说我释怀了?终此一生,我都不会释怀,只是事情告一段落之前,实在不适合消沉。眼下既然不用死了,就先恢复体力、增加修为,把家安顿好,把自己安顿好。至于最后,命抵命,家换家,冷翼这笔账,我终会清算。”
停顿一时,沈冲天接着说道:“九公主,我要见我的管家。我还有田庄、店铺和其他几宗生意,不能因为我出事就凋零下去,这些大部分都是馨儿留下的,不能毁在我手上。”
青霭有些犹豫:“实在不是我打击你,一来你的身体太过虚弱,不宜操劳;二来,就算你有什么生意之类的帐啊、簿子啊、契约啊的,都烧得一纸不存了,确实没抢出东西来。”
沈冲天缓缓抬起右手,指指左胸,自信地说道:“我能过目不忘,过耳不忘,所有帐啊、簿子啊、契约啊的,都一字不错地收在这里。”
青霭突然问道:“那你不是过得很累、很辛苦?”
沈冲天半天没回话。
青霭小心地问道:“我是不是又说错了?”
沈冲天摇摇头:“别人都会说我很厉害,你是第一个觉得我辛苦的,多谢。”
青霭只得应着:“还有什么需要我去做。”
沈冲天摇头:“足够了,你为我做了太多。剩下的事,你别再打听,知道越少,越安全。”
一时唤过管家,安排两人见面。青霭终是不放心,放沈冲天和管家两人在屋里说话,自己在外面关注着动静,半天只听见里面两个声音叽里咕噜的说着,一字听不懂。待里面声渐悄,房门打开,管家出来,朝着青霭深深俯首叩头,口中说着蹩脚的汉话:“多谢!”青霭忙扶起来,管家再无他话,低头出去。
自这日之后,沈冲天就如换了个人一样,话愈少,整日将自己闷在房中,名为调养,实则无人知道他在做什么。日常只有一两个南鹰神府仙侍在屋外随侍着,准备传话,传饭,其实主要是传话。沈冲天本就食量小,这回更是不把吃饭作为一桩事情,时常一天不碰一粒米。除此之外,就是每三两日传唤他的管家,两人在房中商量事情,一待半日。据随侍的仙侍说,沈冲天的身体倒是日渐好转,气血越来越充实,伤病也不见发作。
经过十多日,南鹰神夫妇和夏云烟终于回到家,见垂死之人忽而痊愈,惊怖之情无以复加。问及原因,沈冲天只轻描淡写地说,是自己导气调养时,误打误撞,伤毒上行双目,害得双目失明,心里倒没事了。众人对于这个回答自然将信将疑,待问青霭,更是摇头三不知,众人怀疑是两人做鬼,看在保下沈冲天性命的份上,也不好多说什么。
除了至亲、青霭和老管家,沈冲天一概外人不见。人们看他遭受如此打击,又成了这副模样,只得万般迁就,替他挡下一应探视问询,任由他随心所欲在房中。这样一直持续三月有余,一切都很安稳。忽然一天早上,门房传来消息,小沈公子一人骑着马,背着剑出门,说是奉外公之命去武林城办事。
夏卿拍案大惊:“我在武林城能有什么事!就是办事也不会派个瞎子!谁让他去的!”众人得知消息,担心沈冲天双目不能视,别出什么事,忙追出去,四下寻找,哪里还有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