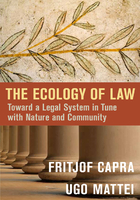和毛有雨会合后,他说他姑姑告诉他,按我们第一次去宝禄潭的路线,到六角湖后,离黄泥巴冲只有不到十里路。
于是我们又折返回去,走我家门前经过。我没看见家里人,只看见对面小溪边我家苎麻地里的苎麻在拨动着。
我知道,我的爹妈此刻正匍匐着身子,在苎麻地里扯苎麻,汗水和着苎麻叶上的尖刺与灰尘在脸上流淌。
晚上,他们又要连夜在月光下去刮掉苎麻的外壳,不当晚去皮,皮和肉就干在一起很难去除,晒干后就黑乎乎的,卖不出好价钱。去掉皮后的苎麻趁太阳晒干之后,储存起来再卖掉。
我掉过头,趁着下坡,快速的冲了下去,滑行好远好远,一路凉风,也顺便掩盖了我的悲伤。
我们边骑行边聊,我告诉毛有雨,施扬兵来找过我,他才从广州回来的事。
毛有雨问:“那他到底会不会去呢?”
我说:“不知道。我们还没去黄泥巴冲,说不定去看了之后,我也呆不了几天。”
毛有雨也感叹到:“好多小学同学没读书了,十三四岁就到广东打工去了,过年时候回来,光鲜亮丽,花枝招展的,一个月有大几百块,走亲访友都大方得很,我们,穷教书的,读的书还多些,不知道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他光顾着说话,前方一个大坑,待他发现时,已来不及了,只听他“哎呦”一声,晃悠了一下,前轮躲过去了,后轮陷到坑里,把他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棉被衣物散落一地,挡泥板歪在一边,卡住了轮胎,好像一只豁了牙的大嘴,歪斜着在嘲笑我们。
望着这狼藉的一片,他揉着摔疼的屁股,索性坐在一边哽咽了起来。我也找不出合适的语言来安慰他,因为我也好不到哪儿去,只好停下车,默默地收拾好地上的东西,用绳子将行李重新捆扎好,又将自行车的挡泥板扳正。忙完这一切,毛有雨低沉着头默默接过车把,又蹬上踏板,继续我们的路。
天有些阴沉,公路两边都扎着稻草垛,散发着清新的泥土味,稻田里,禾苗早已开始分蘖,一片翠绿,不时有鸭子在公路上踱步,追逐嬉戏。天空越来越沉重,乌云疾走,我和毛有雨不敢懈怠,在平坦的水泥路上将车子蹬得飞快。
紧赶慢赶,还是没躲过这场雨,就在刚进沙子路时,天再也托不住那大块的云,索性趁着大风,将自己彻底释放。这是一条长约三公里的堤坝,左边是浩浩荡荡的外湖,直连洞庭湖,右边是围湖形成的内湖,堤上除了堆积的乱石和遍生的蒿草,连根树也找不到。
我和毛有雨低着头,用身子伏在车把上,用头顶和背抵抗着砸过来的雨点,很多时候,我们用尽力气才能和迎面而来的风打个平手,更不要谈能前进了。雨,不用两分钟就将我们浇了个透,沙石路更滑,稍不留神,就偏离轨道,连人带车往斜刺里摆横。
毛有雨的行李早吸满了水,沉重无比,终于卡在碎石的凹槽里,动弹不得。我和毛有雨干脆将车放倒,跑到右边堤坝一蓬高大的蒿草边,坐下来,将外衣拉起盖住头,任雨点冲刷。
这一场雨下得酣畅淋漓,将天空堤坝湖面洗刷得干净利落,清新透亮。雨停了,阳光出来,湖面恢复了平静,堤坝上有了夏虫的啁啾,略带腥咸的湖风荡漾过来。
毛有雨抬起头,我们俩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看到对方湿淋淋的,头发一络一绺伏在脑袋上,小集团似的闹起了分裂,雨水顺着鼻尖、下巴往下滴,整个一落汤鸡的样子,不知是哭好还是笑好。
许是雨水,许是泪水,我俩用手把脸上的水一抹,甩在地上,向上爬,先把毛有雨的自行车撑起来,然后用身子压在被褥上,另一个人再使劲向下按,将被褥里的水挤出来。如此交替进行了三四次,自行车也叽叽咕咕地抗议了好几次,才把自行车的负重减轻了许多。
因了塑料的包裹,我的行李还完好无损。于是,我们又推着自行车,一步一滑,伴随着自行车痛苦的吱嘎声,艰难地走着。又上了水泥路,上坡,再上坡,不多久,就看见一圈围墙,围着一栋两层楼房,一字儿排开,足有二十来米长,肯定就是这里了。
走近,围墙门上竖贴着一块木板,木板边缘有些翘起,上面刻着“宝禄潭乡黄泥巴村小学”字样,有几块经年日久的泥巴在木板上安了家,很是契合这木板上的名字。铁门生了锈,有一根钢筋不辞而别,露出了一扇门,门脸上便写满了欢迎。
操场左边有两棵大樟树,一棵小的桂花树,树皮有些脱落。看了操场,我们更加确信这里的特产了,也是黄泥巴,真是名实相符。
有些地方有一堆堆的泥卷起,从旁边四孔的脚印来看,应该是有猪来这里光顾过,它一时兴起肯定还找这三棵树撒过欢,我想如果没有人驱赶它,它会很欢快地把整个操场不辞辛劳地耕作一遍。
抬起头,左边西头有一排低矮的房子,有根烟囱从后檐探出头来,那应该是学校的厨房,这倒是让我们冷却的心有些许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