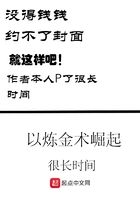第二天上午,我正在看《基督山伯爵》,出卖和污蔑邓蒂斯的邓格拉斯窃取了济贫机构的500万法郎逃往意大利,落在了基督山伯爵的强盗朋友手中。
这精彩的情节让我着了迷,连禾场上来了一个人我也没发现,直到他拍我的肩,将我从书本中唤醒时我才发现。坚毅的脸庞,锐利的目光,高高的个子,帅气的外表,眼神中有着比我们更多的成熟与忧郁,让我觉得似曾相识。
“是你!丁一粟。”
我还是有些迷惑。
“吴萃民,我是吴萃民的同学,我叫施扬兵。我们学校那次停水放假三天,我到你们寝室找吴萃民,还睡了一晚上,见过你的。”
哦,我记起来了,是有这回事,吴萃民是我的室友,我和施扬兵当时没有交谈,是他近1米8的个头给我留下了印象,让我们班女同学念叨了好久,但不知道他的名字,更没有说起竟然是老乡,他的家在隔壁双泉乡,离我家也只有二十来里。
“哦,请坐请坐,稀客,那天怎么没去开会?”我将施扬兵请到堂屋,便急切地问道。
“不瞒你说,我才从广州回来。宝禄潭太远了,这几天我想请我叔叔去走走关系,结果没有成功。听说你也分到那里,找你打探消息。”
他的眼神中又充满着真诚与恳切。
“是蛮远的,很不方便,而且还是黄泥巴冲小学,离镇上都有二十几里。”
“哦,那里很偏很穷,那就是发配边疆了。哎!”
“我们都开了会了,你做什么打算?我们29号下午两点去黄泥巴冲村。”
“那,你们先去,我还是不太想去那里。”施扬兵说完,站起身,就告辞了。
我也没有挽留,继续欣赏基督山伯爵对邓格拉斯的惩罚。
第三天,我便在家整理行李,说是整理行李,其实也没什么东西,一床棉絮,一床被子,几件换洗衣服而已。妈在供销分社买了几米布,用针线连了一床盖被,晚上把门板卸下来,就着月光,摆在禾场上给我订被子。
先把棉质柔和的里子平铺在门板上,再铺棉絮,然后是铺上稍窄稍小大红牡丹绸质的填心,把里子四面超出棉絮的部分翻卷过来,和填心面子重叠好后,便用搓好的粗线和大号针开始订。走线也有技巧,下一针脚要从上一针脚处开始重叠一次,这样才紧密结实,蹬也蹬不破。
妈每走一针,就用针在头皮上刮一下,我曾问过她为什么这样做,她说头皮上的油脂让针尖更顺滑,用的力就更小。
银色的月光洒在妈的头上身上,妈的灰白头发更加亮眼,弯曲的背也更加明显,和在旁边拉扯推搡捣乱的弟弟,一刹那间,我觉得自己真的需要一双坚实的肩膀了。
29号上午,我把两床被子叠在一起,中间夹上衣物,捆在了自行车后座。被褥很厚,捆在后面像座小山似的。
爹抬抬头,看了看天,从猪栏边扯下一块塑料,把我捆的行李松开,先用塑料包住,再用绳索捆紧,有用力使劲推了推,确信不会松动了,才罢手。
吃过饭,爹又推过自行车,把把手提起,晃动几下,点点头,觉得还结实,就放心地递给了我。
娘在后头叮嘱我说:“隔得比较远,你要忙,星期六就不要回家了,省得赶来赶去的。”
而我,却没有将这一切放在心里,只是脚一蹬,踏上了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