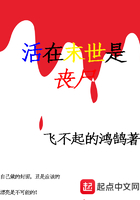第22章
老太太年纪大了,身体不是很好,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
夜里十点,舞台上有人在弹着吉他唱陈楚生的有没有人告诉你。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有没有曾在你日记里哭泣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
听着这首歌的时候我有些恍惚,所以当鸽子的声音在电话里面响起来的时候,我发出的惊讶都很有些恍惚起来。
鸽子爽朗地笑,“格格,你猜我现在在哪?”
我有些反应不过来地问,“你在哪?”
“龙塔的旋转餐厅。”
“龙塔?哪个龙塔?”
他不快,我猜他这个时候肯定很想狠狠敲我的脑袋,“中国还有几个龙塔?”
我询问地看了李明一眼,李明张了张嘴,无声地说了三个字,哈尔滨。
我第一个反应是差点跳起来,“你来了哈尔滨?”
“Bingo!”
我第二个反应是,“你怎么那么闲?”
他这回是彻底的不乐意了,“怎么叫我那么闲?我从来都没见过冰灯,过来看看难道不成?”
“成啊。”我拖长了声音,“反正你有钱,到哪儿还不是跟回家似的。”
“那你还不赶快来看我?”
“看你?我怎么去看你?我又不在哈尔滨。”
“你家不是哈尔滨?”
“大哥,我好像只是告诉你我家在黑龙江,黑龙江好像不只有一个哈尔滨。”
他似乎很迷惑,“是吗?我一直以为黑龙江就是哈尔滨呢。”
“老兄,你真的是大学毕业?”
“当然了,你不信?我有文凭。”
我哭笑不得,“恩,我信。”
他开始耍赖,“我不管那么多,反正我在哈尔滨了,你来不来看我吧你就说。”
我叹气,“我现在在沈阳。”
他嗤笑,“你小子真有良心,有时间去沈阳就是死都没时间过武汉,你还说你不是厚此薄彼?”
“哥哥,我要吃饭,沈阳有我的米。”
“武汉也产大米。”
“我生在北方长在北方,南方的米吃不惯。”
“放屁,广州的米你还不是吃了好几年?别整那么多没用的,你就给句准话,过不过来看我?”
“来,来,不过最早也要明天。”
“搭飞机还是坐火车?”
“飞机票买不起,我坐火车。”
“那好,你几点到,我去火车站接你。”
我笑,“你?你知道哈尔滨的火车站门在哪儿吗?”
“要你管,鼻子下面有张嘴,不用你大小姐操心,说吧,几点?”
我看了看表,又看了看身边的李明,“估计得下午一两点,具体时间等买到票再说。”
挂了电话,李明就一连声地问,谁啊谁啊。
“鸽子,读书的时候你也见过的。”
她若有所思地点头,“哦,记得,就那个没事老拿篮球砸你的。”
“对,那时候没少挨他欺负。”
“你和他们又有联系了?”
“小常结婚前我去过武汉,找他喝了酒。”
她看我一眼,“也见到,苏迟了?”
我低着头喝了口酒,“恩,见到了,鸽子把他拉上了。”
她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有些欲言又止。
我瞄她一眼,“想说什么?”
她突然笑,“受刺激没?”
我冷笑,“我现在这小心脏跟铁打的似的,哪还那么容易受刺激?”
李明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要不要现在去买票?”
我神色淡淡的,“用不着,明天睡到自然醒,到车站买到哪趟是哪趟。”
她揶揄我,“我以为你的心情会很迫切。”
我握着酒瓶子,望着台上唱歌的小伙子弹吉他的手,“迫切?别说是鸽子,现在就是我姨姥姥在等我,我也不可能有什么迫切。”
“你有姨姥姥吗?”
“没有。”
走出哈站的时候,已经差不多四点半。
我还真是睡到自然醒才去北站买的票上车。
我背着书包,黑色大衣裹得紧紧的,冻得有点哆嗦。这个时侯如果能有杯热咖啡就好了,每次走出车站我都会习惯性的想喝一杯热咖啡。
这时候收到小山短信,他说格格,今天营业额七百多,还不错。
我笑了下,多少找到点安慰的感觉。
鸽子在出站口等我,见我出来,扔了罐蓝山经典给我。
还是热的。
我笑嘻嘻的,“还是您老哥儿够体贴。”
“就你那点毛病,我还不知道吗?”
用咖啡罐暖了暖手,扯开拉环喝一口,有点甜。
我皱着眉,“甜了吧唧的,还是黑咖好。”
他没好气地瞪我一眼,“要饭你还嫌馊?”
我赔着笑脸,“是不是打算请我吃饭?”
“这是到了你的一亩三分地好不好?”
“扯淡,我认识哈尔滨,可哈尔滨不认识我。”
他哭笑不得地看着我,“我说格格,你什么才能有点出息?”
“有出息我早成李嘉诚了,还在这拼了命地的瑟?”
他苦着张脸,“你说我怎么就认识你这么个家伙呢?”
“现在后悔似乎有点来不及了。”
他拍我的脑袋,“走吧,先吃点东西,然后带你去听个讲座。”
我下巴差点掉下来,“你?听讲座?那么高雅的东西不合适你吧?”
“你找抽是不?”
“不是,不是。”
这小子忒不是个东西,就给我买了个汉堡,说是时间来不及,听完讲座再去东北王吃饺子。
我咂着嘴被他连拖带扯地弄上了车。
是新东方的全国交流课,地点在哈工大主楼报告厅。
宣传海报上面大张旗鼓地写着,新东方全国优秀教师巡回交流。
我狐疑地看着鸽子,“你什么时候对新东方发生兴趣了?想出国?”
鸽子不屑地撇嘴,“出个鸟国,蕾蕾倒是出去镀了金的,也没见他就成了如来佛。”
我笑,“她是去伦敦,不信你让他去印度试试?”
“去巴基斯坦该啥样也还啥样,我就不信,去阿富汗就能变成本拉登?顶多也就混回来一穿白袍的阿凡提。”
我正喝水,险些没笑喷出去,“小伙子这可不对啊,你这典型就一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还别说,我真就不喜欢吃葡萄。”
我一本正经地点头,“恩,知道,你吃的都是提子,美国产的。”
讲座是六点开始。
不知道鸽子是打哪儿弄来的票,居然坐到了中间第三排,那可是正经的雅座儿。
我看着周围一张张年轻张扬青春的脸孔,无可自拔地自惭形秽。
靠,和他们比,我就一上了年纪的老太太。
然后掌声突然热烈起来,我拧紧矿泉水瓶的盖子,跟着一群人一本正经地往台上看。一溜儿的西装革履,有男有女,领口刷齐的惨白。
啧啧,我拐了下旁边的鸽子,“瞧见没,全他妈白领儿,看这帮小学生,眼睛都直了。”
鸽子没搭理我,样子非常兴奋地对着台上拼命招手。
我不可思议地看着他,感情这孩子是有熟人啊,难怪混到这么好的位子。
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我听到自己的心呼嗵了一下。
我居然,看到了,苏迟!
他优雅地笑,风度翩翩地躬身,左手自然地顺了顺西装的衣襟,款款落座。
我紧抿嘴唇,脸色苍白。
鸽子撞我一下,笑眯眯的,“怎样,还是那么帅吧?我就整不明白了,怎么这小子就能一直都这么优雅这么帅呢?你瞧我,都奔三了,还是脱不掉流氓习气。”
我白他一眼,脸色已经和缓下来,“你那叫自然流露好不好?不信你拍拍自己的胸脯子好好问问,您老什么时候不流氓了?”
“嘿,嘿,苏迟往咱们这边儿看呢,这票是他给的,他知道我老哥儿坐这儿呢。”
我若无其事地看了眼主席台,苏迟平静地笑着,目光正是落在这里。
鸽子再次挥了挥手,这混蛋,比周围那些学生还兴奋。
我揉揉太阳穴,“他也知道我来?”
“知道啊,昨天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他也在。”
“我说你跟着凑什么热闹啊,人家来巡回交流,你也跟着交流?不对,你是踅摸着到这儿找个大户准备和亲吧?”
他把我的耳朵拧了一大圈儿,“和亲我去西藏好不好?干嘛来你们哈尔滨?哈尔滨有松赞干布吗?”
我疼得龇牙咧嘴,拍开他的手,“什么我们哈尔滨?我跟党中央说哈尔滨是我的人家答应不?你当我是****喇嘛?我说你******下手怎么这么狠?想拧死我?这儿没什么松赞干布,红头拖布就一堆。”
鸽子笑着拍了我的脑袋一下。
我抬眼看了下主席台,苏迟抿着嘴唇,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我好像看到他看着我们的时候,轻轻皱了皱眉。
两个小时的讲座,鸽子似乎听的津津有味,我却很有些如坐针毡。
中间的时候实在忍不住了,跑出去到操场上抽烟。
操场上静悄悄的,这么大冷的天儿,依然挡不住那些年轻的小情侣们亲亲我我地散步约会。
远处篮球场上传来砰砰运球的声音,路灯那么暗,昏黄地拉长我的影子,我不自觉地缩了缩脖子,裹紧大衣。
烟头上的火星忽明忽灭,我盯着飘渺的烟雾,思绪也有点飘忽起来。
我仿佛又站在了教五综合楼的大门口,身后透明的大玻璃门来回不停地晃,透出明晃晃的光。
一楼窗口那么明亮,抬眼就能看到自习室里黑压压的人。
那时候冬天只有教五的自习室和新图书馆有空调,所以大家基本都是挤在那里。我们学校的学生似乎勤奋好学的尤其多,每天一大早就急惶惶地跑到这两个地方的门口排着队等开门,来的晚了,自习室座位上不是坐了人就是已经放了书被占了地方。那时候上自习真的就跟网上流行的那首歌唱的差不多惨,好容易捞到个空地儿,乐颠颠跑上去,椅子上肯定没了木板。
我不是什么勤奋的好孩子,不写生的时候基本都是泡在图书馆,因为那里有很多我喜欢的小说和画册。
但是安心看书的时候并不多,基本每次都是刚看个开头手机就开始震,鸽子红中蕾蕾,轮着班儿地折腾我。
那时候鸽子他们住的是学校里最好的公寓,四人一个房间,条件好的几乎可以开火过日子,不像我和蕾蕾,住的地方古旧斑驳,老的像文物,基本上凑合凑合就能拖走直接送进博物馆。
鸽子还嫌不好,哥几个摊钱买了个空调,冬暖夏凉,过得那叫一个舒服,一个爽。
无聊的时候他就把我们一群人招呼过去,打牌,扯淡,什么杀人游戏,斗地主,喝血,捷克,我都是那时候学会的。当然,我的酒量,也是拜这帮大哥所赐,愣是从滴酒不沾的小娃娃给练成了无酒不欢的酒鬼。
那时候我一直奇怪的是,为什么明明是他们练的我,可到最后变成烂酒鬼的就只有我和鸽子两个呢?
毕业的时候我喝到吐,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看到红中在外面等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大着舌头这么问了他。
当时他笑眯眯地说了一句让我恍然大悟的话,他说,没法子,你和鸽子牌技烂。
抽到第三根烟的时候,口袋里手机震,进来条短信息,鸽子找我。
他说你死哪去了?被外星人劫持了?
我看看表,差不多该结束了,于是回他,抽烟呢,在门口等你。
差不多十分钟后,开始有大批的人从主楼门口涌出来。
人群里叽叽喳喳的声音不停的议论。
一个说,“哎,刚才那些老师里面数苏迟最帅了,听说是武汉的,还有个绰号呢,叫海洋之心。”
我嗤笑,还泰坦尼克呢。
另一个无限遐思地说,“对呀对呀,当他的学生可真幸福,不只帅,还幽默,刚才他说什么来着?英语就好比人生,陷进去的时候纠结,陷不进去的,更纠结。哈哈,我怎么看着他那么纠结呢?真有趣。”
然后又一个开始叹息,“唉,他要是在哈尔滨就好了,我保证报他的课。”
我叹息着又点了支烟,我发现这个时候,我比谁都纠结。
鸽子真不是个东西,明知道我最怕的就是这些,偏偏怕什么他就跟我玩什么。
都过去了这么些年,我也安安静静地生活了这么些年,怎么他就这么喜欢跟我过不去?
难道让我要死要活是他的乐趣?
什么时候这孩子能学着厚道一些?
人太多,我往旁边让了让,站到门口那株孤孤单单的小树下面,烟头的光闪闪烁烁。
手机这个时候响起来,鸽子扯着脖子喊,“你在哪呢?我们出来了,没看见你啊。”
我的声音有些无精打采的,“你在哪了?”
“大门口啊,台阶上呢,我这么玉树临风你会看不见?”
我抬头看了上面一眼,人群后面高高的台阶上,站着我熟悉的那两个人,“看到了,我在你右前方那棵歪脖树上挂着呢。”
他眼睛开始朝这边瞄,好像一下就看到我,关掉电话笑着拐了下旁边的苏迟,朝我的方向努了努嘴,然后飞奔下来,我听到他大几号的嗓门,“你这体格,人家那么小的歪脖树挂得住你吗?”
我听到苏迟笑了一声,也跟了过来。
“格格,来啦。”
我嗯了一声,可有可无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