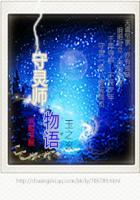宛陵若有所失地坐在玫瑰椅上发愣,韫姜欣喜不迭地从明间穿堂过来:“宛陵。”宛陵怅然回首,赶忙起身迎她:“姐姐。”
韫姜见她眼中少喜色、多怅惘,于是拉着她冰凉的手挨着软榻坐下,问:“可是身上的病还没有好,所以才这般愁眉苦脸的?怎么看着不高兴呢?”
“还没有多谢姐姐费心打点,我之前在无华殿抱病,本以为是要等死了,谁知姐姐特地安排了颜太医来,我能好,尽是托赖姐姐的福气。”说到“颜太医”二字时,宛陵不知怎的神色更落寞了些。
她垂下头去:“……高不高兴的,我听说苏姐姐仍旧不愿出来,连位份也求去了,还是要她的宝林之位,她想必是伤透了心,所以我心里也难过。而且出来了还是无尽的勾心斗角,能有什么好高兴的呢。”她反握住韫姜保养得宜的手,宛陵的手还留着暗褐色的创痕,与之鲜明对比。
“既然出来了,必得好好过才是,你若是累了,我会护着你好好将养的。如今沉冤得雪,你也好过些。皇上那我都替你说明白了,你当初是不得已为之,确实不是你做下的。皇上体谅你的一番苦心,提了你做九嫔之首的昭仪,也是一种造化了。——以后日子会好起来的。”韫姜见她憔悴消瘦,眉宇间的抑郁之气久久萦绕,不禁心如刀绞,眼中蕴泪。
她自责道:“对不住,当年我若替你们打点好,或多上心,或许一切不会如此……”
“姐姐千万别说这个……害人之人其心狠毒无比、防不胜防……或许是难免的。”宛陵慌忙扯出丝帕来给韫姜揾泪,紧拉着她的手,“宛陵必定好生振作起来,我们姊妹彼此相互依靠,怎么能怪姐姐?姐姐别这样。”
韫姜撑出笑来,抬手扫去淌到香腮上的一行清泪,颔首道:“你别多想,好好保养身子,我们来日方长。”她屏住泪意,“苏姐姐那我业已去过,她……她确实不愿再出来了,求了皇上的恩典,但愿伴于佛龛前为大楚祈福。皇上、皇上是允了的。”
宛陵有刹那的失神,眼神迷离到遥远不知处的空谷中去,似乎在留念何物,她落寞地回过神来,相对无言。
韫姜坐在螺钿铜镜前取下石榴石耳珰,愈宁帮衬着卸妆,小声道:“如此,主子也算成全了自己了。”
韫姜神情淡漠地取下一支錾刻赤金步摇,摩-挲过金光流溢的如意镂纹:“不算什么成全不成全的,我不过是推波助澜的罢了。我不过是做我该做的,把蒋妈妈给盛家,又把文淑夫人的绝笔放给孟氏。——孟妃,她当年要是没有诬陷阳儿推她小产,我也不会下这个狠心,要沿儿下狠手。不过孟母的事,倒是蹊跷,皇后大费周章地害她母亲做什么?这不是把孟妃往死路上逼么?”
愈宁将韫姜髻子上的金簪稳稳妥妥收入妆奁中,一面说:“多半不是皇后娘娘的手笔,她病得难以自全,还能抽出这个手去干这个?皇后娘娘造的孽可够多了,怎么敢再做这个。”
韫姜似乎心内了然:“孟母无辜,不到非不得已的,我也不想去伤及无辜。不过别人就说不准了……”
她起身接过簪桃递来的袖炉,在垫了软褥子的躺椅上歪好了,说:“皇后是自作孽不可活,也怪不得旁人。”
簪桃跪在脚搭旁,给韫姜垫了两个暖脚的炉子过来,一壁帮韫姜剥橘子,惑然道:“奴婢蠢钝,之前听娘娘说,佟主子大概是贵妃娘娘安插去皇后身边的人,所以佟主子小月的事应该是贵妃娘娘安排的。可见今日情形,只需要助推孟妃之事,继而托出蒋妈妈即可了,何苦伤了孩子?”
韫姜接过簪桃递来的橘子,不疾不徐吃了两瓤,才开口:“一是要丈量皇后在皇上心里的分量,若是皇上听了还要彻查,那就不是时机,若是信而不疑,那就可以。那个时候孟妃来的这么即时,说不是刻意安排的,本宫是绝对不信的。二则是要皇上相信皇后已经有了心魔,信她的狠毒,好叫皇上觉得皇后切切实实是个会弑子的毒妇。——你要知道,扳倒皇后,主要还是看皇上。只要皇上有一份不信,对皇后还留着一份感情,这件事就走不下去。”
簪桃的动作凝滞下来,若有所思道:“环环相扣,蒋妈妈谁推出来都要惹一身臊,不如叫已经恨毒了皇后的孟妃来,她倒是不怕这些的,将死之人,还怕皇上的多心?再说了,当初孟妃娘娘和皇后走得近,满宫里都知道,她说的话,皇上才能都信,才会彻底厌弃皇后,使之没有翻身的余地。”
“是呵。”韫姜摩-挲过新染的蔻丹,流光濯濯,如花绽指尖,娇艳鲜嫩,“孟妃心太狠,若非逼到绝境,绝不断了自己的后路。她肯和盘托出,一定是瞧得出皇后日薄西山,大势将去,当然多半是因为她的孝心、她的母亲。不过瞧她应该为自己留了一手,当时密谈,或许将自己说得被逼无奈,可怜至极,不过是至纯至孝,为母屈就的可怜人罢了。”
愈宁将沏好的茶稳当当放在榻几上,恭敬站定:“不过那药下得烈,大罗神仙来也难救,就在这几日了。”
韫姜轻轻嗟叹:“她是个至孝至善的好女儿,当年她不构陷阳儿,我也不至如此待她。”
簪桃想起已去了的簪堇,不忍红了眼眶,凄哽道:“可恨皇后,皇上为了保全皇家颜面秘而不宣,她还住着颐华宫吊着性命!”
“她现在生不如死,比痛快死了愈发悲惨。”韫姜侧首远眺向被窗棂剪碎的天末霞云,晚霞一片一片渐次而来,逐渐灰蒙压抑,四角的天隔成云泥之别的两端,想是一块锦缎、一块葛布,真叫人感慨万千。
入颐华宫凤寰殿时,里头空寂一片,凄凉如寒窖,尘灰零落四下,无边萧索。
韫姜问领路的宫娥:“天凉了,不上炭么?”
那宫娥小心翼翼地应答:“回德妃娘娘,内侍监得了令,这里除了一日三餐,其余的一概不给……连药也不给吃。主子娘娘撑了两日,后头连饭菜也不肯吃了,饿到如今。今早起来,奴婢们入内看,只见她穿好了凤冠霞帔坐在那儿,要我们去请德妃娘娘您来。”
韫姜应了一声没有再问。
韫姜拢紧大氅,款款迈步进去,莲步轻缓无声,只有髻上钗的银鎏金坠猫睛石步摇玎玲作响,回响在空荡的内寝,穿山过云而来似的。
她在宫娥备好的圈椅上坐定,离铜镜前的歆珩一射之地开外。
歆珩平静地开口:“你来了。”
韫姜微微笑,似乎在同她闲话一般:“皇后娘娘贵安。”口中说着却不起身,单是安定坐着。
歆珩缓缓转过身来,似枯萎惨败的牡丹一般,一整个儿骨瘦如柴地馁在华美瑰丽的凤冠霞帔之下:“贵安么?恐怕是不能够了。”她停了几日的药,反而渐渐地清醒过来,她此刻无端的十分清醒,平静地说:“你们赢了,本宫快要死了,只怕没有人为本宫哭,只有人喜不自胜的。——想必你也是吧。”
“没有你儿子那件事,或许彼此相安无事,我一辈子在未央宫,你便好好当你的皇后。只可惜天不遂人愿。这是你自己造孽,是你养的儿子造孽。”韫姜冷下脸来,冷然凝睇她,“有什么高兴不高兴的,簪堇回不来了,本宫失去的终究是失去了,也不论输赢。”
歆珩阵阵冷笑:“既然如此,当初就该叫彦儿更狠心肠些!”
韫姜没有愠怒,扬起温和与阴毒交错的微笑:“想来你不知道镇国公还有你兄长被弹劾了,上官家出了你这么一个女儿,又行出不堪之事,皇上震怒呢——墙倒众人推。”
“什么——”歆珩扶着妆台,摇摇晃晃勉力站起,大为震骇,良久,她才纵声而笑,“罢了,我都要死了,何须再去牵挂?论起来,正是上官家害了我一辈子。为的我是上官家的嫡长女,所以母亲自幼训导我要成为一家主母,当初我嫁入王府成了正妃,头一段时间过得还是快乐的。可是母亲见皇上成了东宫太子,又要叫我当个好皇后。就像盛家的皇后一样,我也要成为上官家最荣耀的皇后。可是我不是那样的人,我做不到德仁皇后的样子,真正爱慕皇上,怎耐得住他宠爱旁人,与旁人生儿育女?真正要成为中宫之主,又怎能受得住大权旁落,有人分权?真正要有人敬服,怎忍得住旁人挑衅?”
她仰面哭泣:“可是每个人都说我是上官家的女儿啊,我是皇后,我得日日忍耐,可还是与他们的期望渐行渐远了。我终究不是那样的。”她失魂落魄地迈了两步,吃力地扶着床沿坐下,弓着背虚弱地垂着头,如垂垂老去的暮年老人一般。
韫姜下意识敛了一气,胸腔内泛起一股酸楚与无可奈何来,她有些不适地躲开歆珩婆娑而恍如死灰的目光,物伤其类,到底凄怆。
她何尝不是傅家的女儿,明城的德妃?
她说:“这不是你伤我阳儿的缘由。”
“因为我恨你,我恨毒了你和贵妃。可是我也艳羡你们……一个恣意潇洒,一个备受爱护……”她的床褥上发出滴答的轻声,是她唇边滑落的鲜血,她笑着抬起头:“傅韫姜,你信不信,你的下场不会好过我的。我叫你来,就是要你亲眼见我的下场,来日你必也如此。”
“或许,我并不怕的。人世荣宠光耀我已经享尽,人间悲欢离合我也品尝过,死而无憾。”韫姜平静地勾起一个微笑,她还是歆珩熟悉的模样,瑰姿艳逸,佳人如新月。
歆珩咬牙挺直了背脊,一下一下把大珠点翠嵌八宝赤金凤冠、金钗卸下,把霞帔华装卸下,徒留素发素衣,孑然一身坐在那儿,她伏倒下去,虚弱无力地说:“斗了一辈子了,一点儿都不快活……我已经没有牵挂了,我也不想再为上官家活了。我爱皇上,也恨皇上。我爱皇后的权势,也恨皇后的枷锁。到头来,我爱的、恨的,全都离我而去了。现在我只是上官歆珩,来世不愿再入皇家。”她合上眼,良久无言。
她的绝句在韫姜耳畔久久盘桓不去,她禁不住抿唇蹙眉,从逸出一丝悲哀来。她茫然地四下环顾,企图散去眼中的濛雾,殿内阒静,韫姜迟疑着起身走近她,颤着手贴近她的鼻尖,无有气息。
她抿唇仰头,止住眼中的泪,面颊不住顶了顶,她后退一步没有行礼,濡氵显着双瞳说:“也许我将来也会如此,也是我咎由自取的,怨不得旁人。”
她拂去逸出的泪,她静静地立了许久。她恨歆珩也恨自己,可是如今她心中徒留空落落的虚无与寂寥。
她有些不知道该怎样了,她坐回圈椅上,对歆珩说:“日后为着阳儿,我不知还会做出什么。在旁人看来,兴许同我你没有分别,人终究活得身不由己。”
呈乾六年十一月廿二日,皇后上官氏薨逝,追封谥号颐贤皇后,享年廿八岁,葬入昭陵。呈乾六年十一月廿三日,孟妃孟氏病逝,葬入妃陵。
呈乾七年三月廿日,顺毓夫人晋升为淑妃,景宜夫人晋升为贤妃,贵德贤淑四妃同掌六宫事宜,以贵德二妃为尊,协理六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