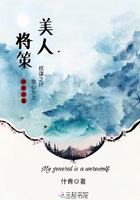太平宫,景妃莲步入内时,只见韫姜与皇后都在,皇后与徽予分坐在黑檀九龙云海长榻的两端,韫姜则端坐在皇后身边的一个酸枝木雕纹的圆凳上,半垂着头,眼睑低垂,目若含烟。
景妃看到徽予正静默地喝着茶,温柔的眼神轻若飘絮一般落在韫姜身上,韫姜眼波一动,对上徽予的视线,二人默契地相视一笑,彼此无言。一旁端着架子的皇后反而显得格格不入,是个局外人一样。
景妃进来缓缓施了礼,君悦立时上来奉了圆凳,待徽予颔首后,景妃才端坐下了。
徽予扬脸示意皇后开口,皇后这才道:“想必景妃对宫中流言亦有耳闻,本宫奉皇上之命彻查婉容华和柳美人中毒之事,自然不可忽视此等传言。经调查过后,其中确有文章。”她将头转向徽予,“故特来向皇上禀告,因事关德妃与景妃,因才将两位妹妹请来的。”
韫姜淡然自若的神情只在一瞬间微变,她露一个了然于心的哂笑,但很快好整以暇地平静下来,等待皇后继续。
皇后继续缓缓道:“传言说柳美人惹恼了景妃,才招致了景妃的痛下杀手,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一道连累了婉容华。”她一字一顿说出,刻意留心着徽予的动静,又说,“流言亦并非空穴来风,查探后得知,是德妃散布了这些谣言。”
她抬手示意,容德会意,即击掌命人领奴才进来佐证。韫姜与景妃皆微转过身子,去看进来的人,只见鱼贯而入两个宫闱局宫女与两个掖庭局洒扫奴才,卑微地弓着身子,畏畏缩缩进来磕头请了安。
为首的一个健壮奴才听了徽予的问话,噗通一声跪下,膝行上前,怯生生瞟了眼韫姜,才回:“回皇上的话,那日奴才们散了班子一处说话,没得听到远处有人在说宫里头的事儿。奴才们下贱,耳根子软,就爱听些奇闻轶事,故上前去听。只听那人说得正是景妃娘娘戕害柳美人之事。奴才记得,那说话之人是穿着未央宫服制的,因与咱们这些粗使的奴才们不同,奴才才格外留了心。事后奴才也不过是当桩奇事,才跑去宫闱局说了。”
韫姜短笑两声,又端正坐好了,慢条斯理地说:“漫说未央宫的人嘴没那般碎,就是爱嚼舌根,也必不去掖庭局这等地方。再者说了,嚼景妃的舌根,于未央宫有何好处?”
景妃浅笑,声音清冷,带着她独有的孤冷,像云雾中高耸山巅上的一座富丽堂皇的殿宇:“若是未央宫的人,若无人授意,只怕也不会说出那些话来。是否有益处,自然娘娘心里也门清。只是如今也不能凭此几人的一面之词,就断定是未央宫人所言,或许有人意在一石二鸟,也未可知。”
皇后泰然坐着,韫姜从她脸上窥探不出一丝得逞或是动摇的神色,仿佛谣言之事她不过是旁观之人。
徽予开口替韫姜解围:“事涉未央宫,还是上心为好。带人下去,仔细查问,切忌不可冤枉了人,也不可姑息了幕后主使。”
显然,徽予是在刻意截断这段争执,他心中信任韫姜不是做这种事的人。但也没托付给皇后彻查,反而是命太平宫的人领人下去,可见对皇后不是十分放心的。
皇后心一紧,露出一丝慌乱,像被风吹散无序的枯叶:“臣妾失责,未查探彻底就将事情禀告给皇上……实在是……”
徽予抬手制止她,语气还算温和:“事关德妃与景妃,你来禀告一声也是应当的,不必自责。”他对着韫姜说,“既然事关与你,待水落石出之前,还是在未央宫中自省罢。”
她从他的眼中看不到一丝苛责,还是平日里的静谧与温柔,静得像一泓水,浸润着无声的爱护与信任。
韫姜施施然起身称“喏”,没有一丝怨言。景妃亦懂察言观色,又将柳美人之事说与徽予,并自请照顾柳美人来赎罪,言之恳切,颇叫人动容。徽予沉思片刻,才许她在钟粹宫照料。
两日后,太平宫养性阁。
错金博山炉中腾起袅袅氤氲的乳白烟气,散发出瑞龙脑香的气息。
徽予盘腿坐在长榻上,低头看着折子。
君悦在一旁无声地转动着风轮,风经过从冰窖中取出的冰块,变换成清凉的轻抚。徽予的鬓发梳整得“一丝不苟”,风只轻轻牵扯动他的衣襟与宽袖。徽予的侧脸显出精致分明的轮廓,高挺的鼻梁将俊逸的脸修饰得更为俊美,皎如玉树临风前。
安姑姑悄无声息地缓步进来,徽予却警觉地感知到了这细微的动静,抬起头来望向安姑姑的方向,一边双眸一动,示意君悦退下,君悦会意,跪下行了礼退下走了。
安姑姑便自然上前行了礼后,继续伺候着转动风轮。徽予问她:“查清楚了?”
安姑姑低眉顺眼着,慢条斯理地回复:“回皇上,查清楚了,他们起初咬定了是未央宫的人散布的谣传,精奇嬷嬷们使了些手段,过了两日有人招架不住就招了,说是……”
她须臾间抬起眼睑观察了一下徽予的神情。他漂亮的桃花眼中寄宿着惯常存在的冷漠与沉静,不急不躁,仿佛对事情已尽了然。安姑姑没得想,他的眼角,笑起来的时刻最为温柔勾人,可惜徽予平常是很少笑的。
她不自觉地停了停,方才继续,“宫闱局陶春招认,是颐华宫的人收买了她,要她去掖庭局找一个人,散布事关景妃娘娘的流言,若东窗事发,便一口咬定是未央宫的人是始作俑者。掖庭局的金钟见陶春招认,便也吐了真话,说是受了打点,若是皇上跟前问起,由他来打诳语。”
徽予端起晾好的茶抿了一口,凝望着碧绿澄澈的茶水,淡淡问:“果真是皇后?”
安姑姑的声音轻了些,但语气平静地仿佛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闲事:“咬死了是颐华宫,流水的刑上去,还是颐华宫。”
她只见徽予沉默着颔首了下,仅有刹那的怒气,但很快湮灭下去,他没有再问,只是吩咐压住消息,对外只说是奴才们眼拙,看错了人,不过是普通地恶意揣测罢了。
但安姑姑在一阵骇人的死寂中,明确地听到了沉思着的徽予低声呢喃了一声“她终究是不如德仁”。
那不是什么惋惜与失望,而是纯粹的、简单的,像是评价一件瓷器的优劣一样的语气。像那样的,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宛如砸碎了一个胎薄如纸、晶莹透影的美人觚,看着替代的略带瑕疵的元青花瓷,叹息了一声“终究是不如啊”。
不包含情感的,对上官歆珩身为皇后极其失职而冷漠地对其价值进行了否认。
安姑姑听到此言,背后一寒,心也冷了下来。他竟然冷漠到不肯把上官歆珩当作妻子,残忍地拿着皇后的身份进行了残酷地对比。
安姑姑呆滞而木然地转动着风轮,纵然德仁皇后知道皇帝以这样的方式肯定了她的价值,恐怕也不会有任何一丝欢愉。
正是无言间,忽有趵趵脚步声而来,虽略有急促,但仍旧有序不乱,勉力坚持着太平宫的肃穆规矩。
安姑姑毕恭毕敬站着,不曾转头,她拿眼一瞥,见是君悦过来了,他顺溜着下跪行了礼,以极快的速度平复了气息,道:“禀皇上,婉容华身边的烟紫招了,是婉容华亲自下了毒。她说道是,婉容华自幼对柳美人及其主母怀恨在心,所以想寻机要取柳美人的性命,自食胡藤蔓不过是转移嫌疑的苦肉计,嫁祸景妃娘娘也是临时起意为之的。”
徽予抬起眼睑,君悦即时低头,开口道:“婉容华余毒未清,虽已醒转,但仍在毓庆宫广阳堂里。皇后娘娘因顾虑到婉容华尚在病中,贸然打入牢狱未免寡幸,故才来通报,又要请一请皇上的意。”
“寡幸?”徽予短促地讥笑,俊美清冷的脸上露出讽刺的神情,“戕害妃御乃是死罪,这时候轮得到谈什么情谊吗?”这同时包含着对柳薄秋的厌弃与对皇后的嘲讽,君悦怯怯不敢接话,胆战心惊地偷偷儿拿眼瞟安姑姑,安姑姑默然摆手,示意他按捺住,只等徽予继续说话。
“该照规矩的就按规矩。”徽予露出嫌恶的表情,语气中糅杂了不耐烦的意味,“若事事讲一个‘情’字,朕也不必当这皇帝了。”后一句话他留着未说,却一切尽在不言之中,君悦颤巍巍答应了一个“是”,起身就要退下,徽予吩咐安姑姑去请韫姜过来,安姑姑便也跟着退了。
二人甫一出了养性阁,君悦就咂嘴长叹:“只怕是生了大气了。”
安姑姑沉默地颔首,少顷,又开口:“事关德妃娘娘不说,还……只是皇上到底顾忌颜面,何况现在后宫中一如前朝,局势不稳,贸然……只会引起混乱罢了。”她不知为何,反而对皇后生出一丝可怜之意。
她记得曾经的上官氏,无助地活在德仁皇后的盛名之下,犹如被参天大树遮去光明的草芥,卑微地渴望后来居上,却与之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