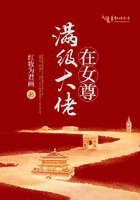夏云骇得脸色煞白,狠狠磕头:“贵妃娘娘明鉴!奴婢待美人忠心无二,绝无此害人之心!”
景妃蓦然想到什么,立时说:“皇上,臣妾若想谋害,自当两样糕点皆下了毒物才好周全,否则臣妾岂知柳美人将会食用何物,是否会有差错?那婢女贴-身,更是方便,怎独独只有一样被下了胡藤蔓?”
“胡藤蔓乃剧毒之物,下毒之人选用此物可见其心可诛,狠辣无比,想是要不留柳美人性命的。若是景妃娘娘或是近身侍女,必是每一样都要下了十足十的量,又怎会只下一样?若是美人不喜这一味,岂不无用?”玲良人审时度势开口说了话。
恪贵妃闻言打量了其片刻,冷冷笑道:“若依如此……并非景妃,并非侍女,难不成是柳美人或是婉容华自己下了毒,做了戏?”
在座诸人听了这话皆是一惊,韫姜一直默然,她其实更比贵妃清楚柳美人与婉容华的过往。
婉容华曾经的自怨自艾与卑微,无不与她这位嫡妹还有家中的主母息息相关。她在听了来龙去脉之后,就在一刹那怀疑过这位以“婉”冠以为封号的、看似娇柔其实不然的女子。
徽予似有不豫,但语气仍算平稳,淡然往恪贵妃处一斜,心里却记下了这话:“贵妃。”
恪贵妃锋利的锐气登时偃旗息鼓,楚楚望向徽予,徽予轻叹气,道:“不要妄议。”
恪贵妃脸面上也有些下不来台,徽予就又说:“此时不可就此定论,淑越既说是你送的,就好好审一审,连同婉容华、柳美人身边的人都审一遍……”他缓缓凝睇住皇后,“皇后,想必应当能水落石出吧。”
皇后嘴角一抽搐,不知是笑还是肃穆,只觉那一声“皇后”寓意颇深,让她不能等闲视之,于是低头回应:“臣妾自当命人彻查,不会冤枉了诸位妹妹,也不会叫那凶手逍遥。”
“此事,”徽予缓慢扫视了韫姜、恪贵妃二人一眼,沉思片刻,道,“贵妃,由你从旁协助罢。”
恪贵妃一愣,与韫姜对视一眼,霎时间彼此心中了然,恪贵妃起身福了福,道:“并非臣妾不愿替皇后娘娘分忧,实在是勋儿入了夏,总吃不好睡不好的,臣妾只怕分-身乏术,反而误了皇后娘娘调查此事。”
韫姜随声附和:“臣妾见贵妃姐姐清减了好些,想是劳累挂心四皇子的缘故。”
徽予听了也不恼,随了她:“那便罢了。你自己也该顾着自己的身子。”徽予转而伸手拍了一拍皇后端放在膝上的玉手,他的手是冰凉不温热的,皇后的手同样也是。二人相顾,唯余落寞。
徽予起驾走后,余下的人陆陆续续也尽散了,因婉容华所食较少,见势有好转,就传了软轿给抬回去了。
这厢景妃怎样都不肯走,自求留下照拂,皇后道:“瓜田李下,景妃这些日子还是自居宫中,自省自警为妙。”
“臣妾无罪,心中坦荡。如若臣妾有罪,也必不敢再出差池。如今照顾美人最心切的,论情论理都应该是臣妾。既然事发,美人若在臣妾的照料下……臣妾自然是万般脱不开干系了。无论如何,似乎都不违背娘娘恩贤待下的美名。”景妃不卑不亢,大有强硬不屈之态,一字一句,句句铿锵不肯退让。
她往前一步,草草屈膝行了礼,又起身凝视住皇后的双眼,皇后总是在平静的目光下暗藏着污-秽而又卑劣的情感。
景妃听过德仁皇后的贤名,德仁皇后人如其号,德行过人,仁爱惠下,她是完美的贤良淑德的缩影。但显然眼前的这位皇后,没有那一位的品行,也没有对这四个字的践行。
皇后果然有一瞬的不悦,仍旧在顽强坚持她的威严,景妃便说:“皇后娘娘若不允,臣妾只好去恳求皇上允准了。”她若去徽予跟前求情,卑躬屈膝的,只怕更让徽予信她无辜。
皇后神色阴暗,表情还犹自强撑出气定神闲的模样:“妹妹若坚持如此,本宫自不该拒绝。只是既然妹妹愿担这风险,就好生祈祷,两位柳妹妹无恙罢。”说毕,面如寒霜地起先一步离开了。
景妃等候她离开,方才将紧绷的神情松下来,她提裙疾步往里走去,只见柳美人惨白了一张鹅蛋小脸,气若游丝地躺在乌木平安如意雕纹的架子床-上。
一见到如此场景,景妃的眼泪就涌了出来,她低头揩去泪水,问柳美人身边留下的侍女:“柳美人怎样?”
侍女战战兢兢回复:“回景妃娘娘的话,太医说主子食用葫蔓藤粉末过多,虽则催了吐,将毒物呕了出来,但业已毒发。好在美人年轻体健,故还留有性命,只还岌岌可危,若挨不过明日,只怕……”她惶恐地低下了头,不敢直视景妃似要吃人的目光。
景妃眼眶殷红,眼中布满血丝,她摆手命人尽数退下,呆呆地转过头来凝视着柳美人了无人色的面庞。
她轻微弓着背,无助地坐在床沿,夏衣单薄,贴服在肌肤上,勾勒出她纤瘦的身躯轮廓。阳光照射不到床的边缘,她孤寂地坐在一片阴暗之中。
聆雎记忆犹新,曾经也是这样,在床边痴痴坐了两日两夜,求神拜佛,求医问药,还是没能留住懿妘。懿妘是磕破了皮也会哭得厉害的娇生惯养的公主啊,临走前,拉着聆雎的手,却一滴眼泪也不流,含糊不清说着呓语,聆雎还没有听清,她就静静地走了。她仿佛不愿聆雎难受,可聆雎却终生难忘。
景妃颤抖着拉住柳美人的手,冰冰凉的,只有手心有些微的温暖,她的眉目痛苦地扭曲在一起,哽噎难语:“好盼儿……你听听我说话。我在这里,我会一直陪着你,我不会让你走的。等你醒了,我亲自做糕点给你吃,等你生辰,陪你放纸鸢、放花灯还有点孔明灯……你醒了,叫我一声姐姐好不好?我、我一直……一直在这里……”她伏倒在床-上,痛哭失声,“我求求你不要走……我一点也不喜欢这里,我讨厌这里所有的人,可是我不能没有你……”
回宫后不久,?诗就同方采女一道来造访了。韫姜命人摆了茶和果子,方采女只是恬淡微笑,静静-坐在一旁,有外人在,?诗也只唤韫姜作德妃娘娘,三人谈说,终究绕不开柳美人之结。
?诗显然是心有余悸,脸都有些许苍白:“不知道柳美人能不能熬过这一劫。都是一起入宫的姐妹,才这些日子……”她一面是有怜悯之心,一面也是唇亡齿寒,无比悲哀。
那是鲜活的生命,柳美人是个眼瞧着极纯良活泼的少女,此刻竟躺在床上,生死未卜,岂不叫人心寒。宫中险恶,如此凶狠,?诗禁不住怯怯看向座上的韫姜,她仿佛对这样的事,已然是习惯了的,虽有可怜之意,却已无惊惧之色了。
“是啊……妾身去给太后娘娘请安,因太妃娘娘在与太后娘娘吃糕点、闲话,瞧起来还不知道的样子,妾身一面怕心中惶恐、说漏了嘴,一面也是不敢打搅,故而随同季姐姐来德妃娘娘这儿坐坐,求个心安的。”方采女垂头叹气,捧着建盏茶碗,热气业已消散殆尽了,也没有兴致抬起来喝上一口。
“是了,为着太后娘娘安心养身子,有些子乌糟事就不往慈宁宫传的。”韫姜回应,看此二人垂头惊惧的模样,轻轻喟叹,“你们初入宫闱,一无所知。外头都说宫里的娘娘们多少荣华富贵享不尽,可这泼天的富贵也是要争、要抢的,那漫天的宠爱,也是要夺、要算计的。甚至结下梁子,就是攸关性命的了。更为凄苦的,去了无华殿,再无所望。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端的是痛不欲生。所以你们,纵然有鸿鹄之志,但也该揣明白,命要紧还是光鲜要紧。”
方采女见气氛愈加凝重,于是转了话,笑道:“多谢娘娘教导,妾身等谨记在心……快别说这些了,妾身去太后娘娘宫里请平安,就见太妃娘娘也在,瞧她们桌上摆的糕点虽看着家常,但也馋人呢。”说着捂嘴笑,二人也被逗笑了,?诗杏眼弯弯,轻柔一戳方采女的额头,嗔道:“这会子来贫嘴呢!是什么好东西?”
“是甜合锦、双色玫瑰馅豆卷、菡萏莲子酥和一碟绿豆饼。太后娘娘还念呢,说这几道果子点心贤懿太妃娘娘做的最好,只是她倒想着玫瑰栗子糕,不知怎的今日没有……”因着提到栗子糕,氛围又僵了些,她就赶忙去说韫姜这儿的糕点来,这才又融洽些。?诗也很识时务地说起御膳房的点心哪些可口、哪些腻味。
韫姜一壁微笑,一壁却闪过一个念头。她低头凝思起来,但也觉不过一切是巧合,这念头来得过于无稽,也就打消了作罢,不过是蜻蜓点水,水过无痕。
她静神看着眼前两位韶华正好、青春年少的少艾,此刻的她们“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远。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是最美好的年华,有恐惧、也有纯粹的喜悦,她却已然有一丝诡异的麻木与冷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