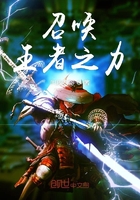钟粹宫揽星堂。二人到时里头的纷乱已略略止住了,所有人皆神色凝重,摒弃敛息,或站或立,乌泱泱挤了一堂。
内室以屏风隔成两处,安置着柳美人与婉容华。皇后坐在堂中央的交椅上,一见徽予协同韫姜来了,忙站起身来见礼,韫姜便就退后两步不敢受礼,再行问了安。
韫姜抬头扫了一眼,却见顺妃盛挽蕴也在,她那双鹿眼似的灵动的杏眼,却因过于瘦削的面颊而显得硕-大而恐怖,她惨白的脸泛着病态的青色,此时正捻帕捂唇站在一旁。
韫姜静静听皇后将事情捡着要紧说了,徽予听完就欲入内去瞧上一眼,临走时回头示意韫姜一瞬,韫姜就只好留在外屋梢间等候而不入内。
外头嫔御众多,是非也多,徽予甫一走了,窃窃的话语就旋即响起来了。
方采女怯怯对琳宝林说:“听到消息时可将我吓得丢了魂……都说宫里头不比外边,虽不见硝烟,却犹比战场,才入宫没几日,就给见识了。”
琳宝林小声道:“也不知是得罪了谁了。景妃娘娘不是还挺瞧得上柳妹妹的么?”
方采女悄悄儿去瞟面带忧郁之色、坐立不安的景妃,不敢随意接话。
桑柔小声道:“止不住差错就在这儿呢。景娘娘妃若孤立无援,旁人或许也更松快些。”
琳宝林眼波轻微一动,低语道:“她们的心思,我们自然是猜不透的。只是往后要小心些,你以为那上面坐着的哪一位器重了你是好事,殊不知福祸相依,要大难临头了。”
“都说咱们这些入了宫的新嫔御,如若不能站稳脚跟,必得寻一位稳当的靠山才是正经。否则是前途忐忑,步步惊心。”方采女往后挪了两步,更将声音压低了,“我倒不想着多少泼天的福贵与荣华,平安才是头一等要紧事。我私心觉得那话是诳语,自己个儿安分着,娘娘们也懒怠来收拾。”
琳宝林轻哂,声音低得唯有自个儿听得着:“或许自个儿争气,不怕她们,将来和她们一样风光。”
那厢韫姜在顺妃身边坐了,问她:“你怎么来了?皇上才和我说起你这几日身子不好呢。”
“这样大的事,我是不好不来的,其实不过是咳嗽,力气和精神还在呢。”顺妃捂嘴苦笑了下,干瘦的手垂下去,便露出原被遮住的唇来,虽搽了殷红的口脂,却还提不起她整张脸的气色,她艰涩撤了下唇角,笑得很勉强。
“你若累,千万别撑着,与皇后娘娘说一声,她没有不答应你走的道理。”韫姜看着她的病容,将心比心,也是苦涩。
顺妃虽不至形容枯槁,却也远比在座的诸位妃御来得憔悴枯瘦,如一把枯木病树,在光鲜亮丽的妃御前显得黯然失色。
“这个是自然的,我三日小病五日大病的,晨昏定省都是得了恩赐能免则免,这会儿,皇后娘娘岂有不放之理呢。”她说着又侧过头去咳嗽了几声,喘了喘气,“这事儿又是怎样呢?只待皇上出来了,才好定夺。”
“无缘无故,脏东西也去不了她们嘴里头。只怕是有人刻意了。只是,不知是否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韫姜侧目往里头看。
顺妃轻声道:“焉知不是如此。我虽长久卧病在榻,却也知道些。那容华也不是顶扎眼的,更遑论那位柳美人了,温温吞吞的恩宠。怎样也想不到有谁该对她们下毒手呢。”
韫姜淡淡:“旁人心思我们怎么会知道?只待皇上出来罢。”
顺妃理了理淡牵牛紫金丝祥云纹的褙子襟,一壁抬头望向皇后,淡然说:“实在奇怪。我怎样也想不到,会是柳氏姊妹,难不成是有人怕她们姐妹同心而坐大,误了自己的前程?”
韫姜对柳氏姊妹的感情是知情的,因而闻言单是摇头,却也不好随意置喙点评,只说:“不大会。后宫之地,姊妹反目成仇,也是寻常。我想不会有人甘愿冒这个风险。何况婉容华前来是巧事,千算万算也算不到这层来。怎样看,这毒下得都过于诡异了。”
顺妃微微笑,清瘦的面颊浅浅凹下去些,显得很是疲累:“如若能以之行诬陷之事且坐实,也算是值得。”
韫姜侧目视之,轻声道:“不知如何,且静观其变罢。”
外头坐了不过半盏茶功夫,徽予就出来了。
那时韫姜正捧着茶盏凝神静思,林初尚在礼佛,而宛陵也因要照顾发了热症的昭临所以没来,她就独自个安静-坐着。原和顺妃说着话,韫姜因怕她体力不支,就叫她好好静着,自己另寻了他处静-坐。
?诗本欲与她说话,又怕众目睽睽惹人注目,也就忍着与瑃小仪站在另一处。众人见皇帝出来,皆起身请安,徽予示意众人免礼,才都又或站或立。
徽予才发觉顺妃也在,顺口问了一句安泰与否,顺妃浅笑安然,静如池水:“多谢皇上关怀,妾身一切安好。”脸色却还是奇差,整个人弱不禁风一样,说话也是细弱无力的。
恪贵妃蔑然将眉一挑,石榴红的蔻丹缓缓划过白皙的面颊,对韫姜嗤道:“也就你好心眼去与她说话,病恹恹的就安生在寝宫里歪着,别出来撒晦气。非要拿腔作调,叫皇上关心,还要佯作一幅体贴样子。”
韫姜知道恪贵妃就是这样口中含刃的性子,倒也不是一定厌恶毒了顺妃,不过是一时瞧不上眼,顺口就吐露出来,于是淡淡然说:“她也是难过的,终日病症缠身的,姐姐与她计较些什么。”
恪贵妃眼一斜,轻视道:“你就会拿捏贤良德性。”韫姜也不恼,只悄悄儿的:“姐姐别置这个气,只看看眼下什么最要紧呢。”
恪贵妃支颐托腮,飞扬的眼角泛过一瞬的凌厉,转而又懒懒的:“我只瞧谁这样鼠目寸光,大费周章只为些蝼蚁。”话一落,二人却不约而同地将视线移到了景妃身上。
此时的景妃魂不守舍,面无人色,一改往日冷冷天上月之风,宛如要枯萎的玫瑰,带着倔强的刺,花瓣却已几近飘零殆尽。
她目光呆滞地凝视着地上的罽子,上头有寿桃万福的绣纹,繁复累缀,看在她眼里不过是一团乌糟。
“妘儿走了……她们还要把盼儿夺走吗……”景妃的声音沙哑而颤抖,融进了深深的恐惧与哀泣,她此刻之心境可真的是“天寒色青苍,北风叫枯桑”,悲痛难忍。
她怨毒的愤怒隐藏在心底,狠狠将堂下诸人扫了一遍,咬牙道:“我要是知道是谁要害了盼儿,必要她生不如死。”
这厢皇后将查过的结果又给徽予叙述了一番,她道:“臣妾业已命人去彻查了,太医察验出一碟子玫瑰糖蒸栗粉糕上撒有胡藤蔓粉末,那脏东西叫人吃了肝肠寸断,腹疼不止……若非两位妹妹福大命大,只怕……可怜柳美人吃得多些,还不知是否挨得过这横祸天劫……”
徽予剑眉一蹙,目光沉沉,乍如万壑惊雷在眼中霹雳:“胡藤蔓,断肠草,这样的脏东西进了朕的嫔御的嘴里,险些要了二人性命。”他隐忍住怒气,脸却是硬冷的,发出的声音犹如凶兽的嘶吼,“这糕点是哪里来的?”
夏云吓得立时跪在地上,她的双目哭肿得恍如熟透的蜜-桃,一开口,眼泪就汩汩涌出:“启禀皇上,今日主子得了景妃娘娘赏赐的点心,其中就有那一份的玫瑰糖蒸栗粉糕。景妃娘娘厚爱,主子就邀了容华主子同享,谁知竟出了这样的事!”
景妃闻言起身,屈膝跪下,声音哽咽道:“皇上明鉴……臣妾疼爱柳美人,若说是臣妾要害了……”柳美人如今尚在弥留之际,不知是否能够渡过这一劫难,景妃只觉心疼难忍,眼泪便涌了出来。
如此自矜自重的人此刻这样沉痛,无人不生怜意。她细长的倒晕眉痛苦地拧结在一起,眼眶红得宛然淬了血,嘴唇都在不住地颤抖,她生生将泪意压回,悲戚道:“皇上……臣妾敢以齐国褔祚起誓,绝无害柳美人之心!”她抬起头来,露出素日里的坚毅来,徽予竟有一瞬的震动。
他将语气放缓:“你敢以齐国之名起誓,情深意切……先起来罢。”
“皇上,若说毒誓,其实都是虚妄之词,空口白牙地赌咒,谁也不知这因果报应。”谢贵嫔骤然开口,她本不想来,怕沾染了晦气,但又按捺不住心里奇怪,这才又来了坐坐。
全修容沉住气,拿眼瞟了瞬皇后的脸色,终是没有贸然开口。
韫姜适时出来说:“以母国起誓,可算是坦荡。谢贵嫔想必是谨慎,但因果报应之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如今咄咄逼人,不知将来折了谁的福祉。还是少说为妙罢。”
谢贵嫔脸色一沉,下意识捂住隆起的小-腹,脸色晦暗,沉默不语了。
顺妃嗽了两声,哑着嗓子说:“确实,也都是说口说无凭。景妃也不曾否认了那糕点出自自己之手,如若要教众人信服,还是要拿出真凭实据的。”
淑越连忙站出来:“启禀皇上,糕点是奴婢亲手送的,奴婢敢以性命作保,此糕点绝没有被动过手脚。何况……”她噤了声,尚不敢贸然将太妃托出。景妃也是眼波一动,犹豫着不知如何开口。
“臣妾疑惑,纵然是景妃动手,只不知道有何深仇大恨,要将柳美人置于死地呢?何况这所谓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之法,上一回景妃是吃过教训的,如今可还要故技重施么?只怕是不能。”韫姜看事清明,瞧出了景妃对柳美人的一片真情实意,也就泰然为她开脱,然而也有些略微的别扭与芥蒂,把话说得带了些讽刺之意。
恪贵妃短笑两声:“德妃不说,本宫也忘了。”她斜睨皇后一眼,又把视线缓缓投向景妃,“只是话虽如此,却也实在难以洗脱这污名。淑越要是保证一路上安全,那自然是入了揽星堂后出的岔子,难不成是祸起萧墙,叫自己奴才给暗害了不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