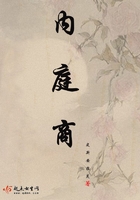皇上回去没多久,皇后便也叫众人跪安了。
人稀稀散散、成群结队地出去,韩、荀二人皆黑着脸,还是一道走着,出了颐华宫,婉容华过来,她身边跟着柳美人,婉容华假惺惺道:“二位妹妹可别吃心,这样的情分,可是我和亲妹子还求不来的。”笑声却有些尖锐刺耳。
柳美人讪讪的,越过婉容华的肩头,望了一眼景妃,无奈地福了个礼,跟着婉容华走了。
荀、韩二人还是默了一路,一众奴才敛声屏息地离开几步远,亦步亦趋地跟着。
玲良人一腔求和之情付之东水,又丢了脸,更是火上浇油。她的脾气更比瑃小仪的爆些,终究忍不住,疾步走向一个少有人来的亭子,瑃小仪迟疑了一下,跟上去。
“我自诩同你是知心的手帕交姊妹,你就这样要现眼,要显出你越过我去?《高山流水》,好一个《高山流水》!”玲良人气得面颊涨红,胸口剧烈的起伏着,两眼放着精光,仿佛有熊熊烈火。她踱着步,转了两个来回,又咬牙切齿:“你不妨把话撩开了说,别跟我阴阳怪气的。”
瑃小仪按捺许久,终于忍不住,双目赤红,活像洇了血一样:“说我阴阳怪气?你是在闺阁里就听我倾诉衷肠的了,如今你得宠风光,快活潇洒,怎不想着我的凄苦?”她水葱一样泛着的蔻丹嵌入掌心,妒火烈烈,让她不能自已。她忍不住落泪,想起徽予似有厌弃的目光,恨得浑身发冷。
玲良人发狠,拉住她粉藕似的手腕,啐道:“我待你掏心窝子,你就这样不信我?为这些个就与我生分?”她连连冷笑,扔开手,瑃小仪抹泪:“你真心待我好,就不该这样……”
“怎样?!”玲良人声音提了几个高度,尖锐起来,“谁不是身不由己,谁不是要为家族门楣拼命的!偏你不一般,带着几分情谊就颐指气使了,皇上可曾真心待你?你自己明白!你有情就配获宠,我偏不能,入宫了,一切都不同,我若为了你避宠,我还要活不要活?我算是看明白了,什么劳什子的姐妹情深,还抵不过皇上一言一动来的重。”
她一啐,面容狰狞扭曲得宛如猛兽,“你自视甚高,自以为一定能获得宠爱,我早看穿你了,你以为你远比我好,所以才更加愤愤不平,我竟然比你得宠。我告诉你,你是庶女,我不过瞧得上你给你些脸面,你别蹬鼻子上脸。当初闺阁千金堆里,没有我带着你各处说话,哪里来有你立足之地!呸!”
韩令是个轰烈的,爱之深也恨之切,她起初是付出了一颗赤心待瑃小仪的,明白了一些事也兀自吞了、忍了,一旦全捅破开来,恨意便一波涌上来,弥漫全身,没有退散的道理了。她失望至极,恨得极深,说话口不择言,极为难听。
瑃小仪气得浑身战栗,眼瞪得硕大,泪被一股涌来的浊气给堵了回去,她只觉两眼发黑,往后踉跄两步,扶着厅里的高桌站定了。
她定定喘了两口气,脸色煞白,目光发直,僵了一口气,猛然剜过去,恨声:“你不过是托生在大房太太肚子里,空有个嫡女的名头罢了!算什么东西!我样貌才情样样远胜于你,没有被你踩在地下的道理!轮不着你来可怜我!你给我脸子?呸!你可不知道那群长舌妇背后说你妄自尊大罢!哈哈哈!你也不过如此,绣花枕头罢了!”阴骘狠辣在她的脸上不断回旋,玲良人气急败坏掴了一掌去。
电光火石,瑃小仪没有防备,生生挨了一记,跌坐在地。
玲良人没有眼泪,居高临下地睥睨着恍惚的瑃小仪,冷冷道:“你且看着,皇上珍视你吗?在德妃等辈眼里,你就是个笑柄,是她们茶余饭后拿来取笑的。”说着重重甩袖,疾步离去。瑃小仪恨不得放声嘶喊,直直捶地,难以纾解心中郁愤。
后来?诗来韫姜处谈天,说听到瑃小仪房中隐隐传来玉瓷破碎之声,叮当“掷地有声”。韫姜只是笑笑。出了那事后韩、荀二人都受了冷落,倒是?诗一直乖顺和婉,一直有着细水流长的恩宠。
这日午睡后起身,韫姜闲来无事,坐在临窗的炕上,抵着炕几看窗格外宫女们侍弄花草。愈宁进来奉了茶,后脚跟进来簪桃,说:“琳宝林过来给娘娘请安呢。”
韫姜本也百无聊赖,就叫请进来说话,愈宁同簪桃下去备茶备糕点。
琳宝林一身杏黄羽纱双福长比甲并雪绫百褶裙,是一通晏居的装束,清雅有味,颇有情致。她上来盈盈拜倒了福礼,韫姜让了礼,请她上炕来坐,琳宝林却礼不敢,韫姜于是命人搬来一个直背交椅垫了靠背、褥子,金钱蟒纹的一色褥子,加了鹅绒鸭绒进去,十分舒适温软,比略微发硬的纯棉更令人舒适。
坐了后,琳宝林说:“路经未央宫,嫔妾想着,还是要进来请个安才不失礼,所以冒昧进来叨扰了。”韫姜温和:“正无聊没打发呢,恰好你来了,若不着急,一道说说话也很好。”
二人随意拣了些没要紧的说,期间泷儿进来奉了茶水糕点,琳宝林只客气地用了一星半点儿。
正说话,韫姜抬头见愈宁打起帘子进来了,有话要说的模样。她以目询问愈宁,愈宁神色轻松,看似是不打紧的事,于是顺口就问了:“何事?”
愈宁上来先给琳宝林福礼,琳宝林颔首。愈宁方才回复:“是傅大人传话过来,族中表亲嫁女,嫁了白石潭国子司业曹家,傅大人说附礼过去,问娘娘可要赏赐了恩惠,若有意,傅大人便封一份去,也算是一份祝愿了。成人之美,也是积德的好事。”
韫姜颔首:“不消父亲备了,你自领了人去挑备些礼,回了颐华宫、太平宫,若得了允准,就赐下去,也算尽心了。”
琳宝林的脸色乍然一变,腾的站起身来,韫姜一惊,瞬息往后靠了一下,愕然道:“怎么了?”
琳宝林恍然之间面无人色,愣怔少顷,木头似的坐下,摇摇头又点点头,端起茶盏来送到嘴边又放下,行止奇诡,韫姜连唤三声,她才猛然回神,讪讪道:“适才听闻白石潭,才想到白石潭一件奇诡的民间逸闻,故而吓着了。”
韫姜思索片刻,想起琳宝林祖籍是白石潭的,因而颔首:“本宫记得你出身白石潭。”她看着她惨白的面色,隐约揣测到些猫腻,微笑着,“可认得白石潭国子司业曹家?”
“白石潭不比京城繁华广阔,官宦人家间颇有往来,自然是知道些的……不过多是闺阁女儿们一道在内房里头说话的,我也只不过是与曹公子的二妹有些交情在。……端的白云苍狗,转瞬曹公子也要娶亲了。”她眼底微红,好似强压着泪意与委屈,话音也有些颤抖。她低着头,歪曲着一个纠结的笑。愈宁机敏,察觉到一丝暧-昧,忙的领了人退下去了。
韫姜只做蠢钝不知状,煦煦与她岔开话题,说了些白石潭的人文景色,琳宝林却是霜打了的花,蔫了泰半,纵然极力端着寻常的态度,但依然看得出快僵持不住了。
韫姜适时说了要去慈宁宫请安,放了她回去。琳宝林脚下生风,粗粗行了礼就跌跌撞撞出去了。愈宁踅回来,韫姜轻声吩咐:“当做什么也不知道罢。”愈宁颔首。
琳宝林疾步走在宫道上,迎着风,觉得浑身生疼,她半捂着脸,泪水从指间溢出,桑柔扶着她,眼尖瞧见一处歇脚的亭子,扶着她朝那边去。琳宝林颓唐坐下,伏桌大哭。
桑柔眼角渗出泪来,哽咽道:“小姐入宫前就一直哭,入了宫才好些了,别再哭了。木已成舟,不能回首。皇上到底还是英雄豪杰、千年难得的天之骄子,不比曹公子好些?”
春日的风是极温柔和煦的,带着温暖与清幽的花香,分明是让人安宁的气息,琳宝林却无法感知到,只觉天昏地暗,浑身战栗,泣涕不止。
桑柔狠下心来,道:“主子!到底看开些罢,您入宫做了嫔御,还要曹公子终身不娶不成?他是曹家嫡长子,去岁秋闱中了进士,白石潭前来求亲的几乎要踏破门槛了。是曹老太公不愿咱们家,实在是有缘无分的。”
琳宝林连连摇头:“他说非我不娶的。我中了选侍,他还传信来叫我宽心,休得郁结伤了身子,他实在是父母之命难违,也是我们家眼高于顶,一听宫里有选侍的风声,就万万不肯结亲了。他叫我千万记得他,他也必不忘我。”她的泪水无止尽一般滑落,哽咽艰涩,“可他转头就娶了亲,我活像是个笑话。”
桑柔叹息,一转眼,狠心咬牙道:“姑娘您就是太掏心窝子信那负心人了。海誓山盟,还是成了寒盟背信。他若肯争一争,姑娘也不必今年来选秀了。说得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底是他软弱没主见的。既然彼此有了着落,就该断的干干净净的,要小姐您记得他,还不是盼着小姐若得宠,也好给皇上提一提他,让他官运亨通些。啐!”
琳宝林打了个激灵,嚎啕:“可他待我那样好啊!”
桑柔千恨万恨,一腔子怒火想宣泄,碍着奴才的身份只好忍着,可又心疼、又怨恨自己主子迷途不知返,入了歧途,被猪油蒙了心,还掉在蜜糖罐子里出不来。
她气道:“我冷眼瞧着曹公子当初与主子好,也是盯着咱们大少爷有出息的缘故。如今来了个与德妃娘娘、太师大人结着七拐八绕亲的姑娘,就巴巴儿定了亲。清流官家们最忌讳名声受污,就是出了五服的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来打秋风也没有冷了的。我看曹家就是吃定这一点,才要这样呢!这不是就拐着弯地能沾了德妃娘娘的光!”
琳宝林双眼通红,双目布满了血丝,仿佛要喷射出火焰来,她狠狠剜了眼桑柔,桑柔一下噤声不语了。
琳宝林的眼泪还在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不断抽噎着,心里却缓缓平静下来了。她无神地呆视前方,摇摇头:“不是……”她想着许多事,头嘶呖呖发着疼涨。
她哭得眼睛酸疼,于是合上双眸,沙哑着说:“不是这样的……”脚下仿佛踩了棉絮,她摇摇晃晃、立不定地站了起来,忽觉喉中腥甜,她弯腰“哇”的一声呕出一滩污血来。
桑柔吓得魂惊魄惕,仓皇扯出帕子来给她擦拭,又四下看人,想要喊人来。琳宝林却重重抓紧了她的手腕,几乎要生生折断她的腕子一样,桑柔疼得咝咝抽冷气,却不敢喊疼。
她一张脸变得灰白,木然点点头,凝望着一滩腥臭的污血:“前事了了,都了了。他娶亲了,我也成嫔御了。都一了百了的了,没甚好怀念的,都是一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