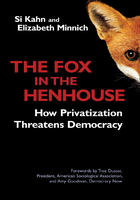景妃站在悬挂在宫门口的大红宫灯下,明黄带红的光散落在她身上,像挤过云层的缝隙溜来的阳光铺在一块,显得她是秀颀冶丽、丰标不凡。
她有一双清寒的眼眸,极美。她的瞳色不是点漆般的墨色,而是微棕灰,仿如点了水,虽有熠熠明光,可是不纯净,是掺杂了浑浊的欲-望与城府的。韫姜喜欢她的眼睛,同样也厌恶她的眼睛。
景妃规矩地问了安:“臣妾恭请德妃娘娘安。”
“景妃无须多礼。”韫姜伸手扶她一把,顺势瞟了景妃一眼,这齐国崇尚丰-腴富态之美,景妃却是纤若杨柳,令人不禁浮想联翩。
客套结了,一同领了人往英华殿去,韫姜同她讲道:“这如今宫里最大的礼佛之地是英华殿,英华殿地处僻静之所,周遭梧桐、菩提树蓊蓊郁郁,四季常青,是最好的静心修禅之地。本宫想齐国是奉佛教为国教的,对我佛无比尊崇,景妃必也是一位信女,所以才特地邀请妹妹前去祈福。”
“德妃娘娘善意,臣妾自然应约。只是娘娘体弱,为什么选在夜深天凉之际?”她们并肩而行,却相隔几拳之远,尽显的疏远,景妃询问的声音很平静,似乎是随意提的一句。
“心诚则灵,吃些苦,更显诚意。”韫姜不咸不淡地回应,望向领路宫女手提的羊角宫灯,上头绘了仕女美人图,婀娜小蛮的丽人,在透出的朦胧灯光下焕然生姿。
“原来如此,德妃娘娘想得是周到。”景妃敷衍却又礼敬地应和着。
韫姜付之一笑,不多议论。二人一路默默,只有钗环铮铮的脆响在耳边吟唱。今夜没有月色,黑得深,月黑风高夜,总让人生出不祥的预感。
到了英华殿,二人一同入内敬香磕了头,双手合十,默念彼此所愿。
待到韫姜起身时,她无意间瞥见侍香的宫女总在瞟自己,于是暗中留了心,等景妃不留意之际,走至那宫女身边,那宫女果不其然开口,细如蚊声:“英华殿后有一条竹苑小径,德妃娘娘走那条路再转入小门,就能入苏妃娘娘房中。”
韫姜颔首,不动声色地转身走开了。
真是如有神助,她正思索着如何哄骗景妃一同去时,恰瞧见外头的黑云渐渐散开,露出半个硕-大清冷的月盘来。
她徐徐走至景妃身旁,温文道:“天公作美,清风半夜,明月别枝惊鹊。景妃可有雅兴同本宫一起往英华殿后竹苑去散散心,也赏月一回?”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望月思乡,景妃亦有愁思在,索性答应了,与她同去。
韫姜半捂着嘴,虚虚咳嗽两声,以目示意愈宁。愈宁何等聪敏,立时会意。等转入后院,方走了不两步,离竹苑近了,愈宁忽的惊声唉呀:“主子发髻上簪的那支烧蓝比翼鸟玫瑰金簪怎么不见了?”
韫姜忙的伸手去摸发髻,一下子惊色乍现:“真没了!旁的倒罢了,可那支簪子是皇上在本宫及笄时亲自给本宫簪的,丢了可不是要了本宫的命?!”说着即刻转回身来,满面歉意道,“景妃妹妹前头石凳上稍坐片刻,这簪子不是十分奢美,但里头的情谊是断断舍不得的,本宫不找着了心中不踏实,还是要踅回去寻了才好。”
景妃淡淡道:“既如此,臣妾帮着娘娘一同找就是了。”
韫姜推辞:“怎么好劳烦妹妹的,好像是落在殿内了,本宫去去就回,若殿内没有,就传妹妹一声,今夜赏月怕是不能了。”
景妃面上波澜不惊,四下扫视一眼,是一派安静,只不远处是苏妃礼佛之地。她暗中想着了什么,于是顺着答应了。
恭送走了韫姜,景妃吩咐淑越:“你去悄悄儿盯着,看德妃是不是去密会苏妃了。”
她自己在圆凳上铺了帕子闲坐了,仍觉不妥,可一时之间也揣摩不出什么。
神游之间,突然有急促的脚步声传来,是踏着竹叶的脆声,景妃乍然吓了一跳,猛回头时,只见一个身影闪出。
景妃尚未回神,就直直撞进一个陌生的怀抱,是个男子!
她吓得几乎要尖叫出声,却被一支强有力的宽大的手掌捂住,慎今本要高声喊人,可被当心窝子踹了一脚,一下吃疼,跌坐在地,口中不能出声。
那男子搂着景妃,口中不干不净,吓得景妃也顾不得什么大家闺秀的仪态,又咬又啃地狠狠挣脱起来。
不知是谁高喊了一声“来人”!登时乱作一团,不少时灯火通明,英华殿内伺候的宫人、奴才鱼贯而出,那男子见势脱手要走,赶来的顾诚身手敏捷,一个箭步冲上去飞踹一脚就将他捉拿在地。
那头的景妃钗散鬓乱,吓得面无人色、涕泗横流,韫姜提裙过来抱住她,抽出帕子给她擦泪,口中问:“这是怎么?本宫才走一回子怎么变了天了!”
心中却暗叹,还好她觉得此事不简单,所以以静制动、按兵不动,还派簪堇去暗中盯着有没有变故,万一她莽撞地只身前来,那可真是清誉尽毁了!
景妃身抖不止,不肯奴才们跟前失了尊贵,她死命咬唇,忍着惊惧与委屈,竟生生把唇咬出血来!
韫姜镇定下来,让归来的淑越护住自家主子,一面差人将狂徒羁押到最近的广陵宫去,一面又教人去请皇上、皇后与贵妃。
簪堇过来偷偷说:“娘娘,那声不是奴婢叫喊的,是有人在这儿守株待兔。”
韫姜眉心微动,腹诽不妙。外头动静大,林初拨了人出来问是怎么了,见韫姜在,惊喜地问了安。
韫姜思虑少顷,只说无碍,叫林初不必挂心,让在场的人闭紧嘴巴,一面陪同景妃一径去了广陵宫。
徽予等人是待景妃浣面,重新梳妆罢了才到的。
景妃心有余悸,喝着热茶暖身,面无人色、默然不语。韫姜愁眉不展,坐在她身旁,宛陵哄着昭临睡了才赶来,韫姜拣着要紧的同她说了,宛陵直捂着胸口咋舌。
韫姜讲完后不久,三人陆续到来,待到人齐后,韫姜才命缓过神的慎今把所见所闻说了。徽予听了脸色铁青,喝道:“把那没命的畜-生拖进来!”
慎今突然膝行上前,恐惧万分:“有一事……奴婢不知该不该说……”
她被徽予射来的目光吓得往后推了一下,徽予缓了口气,才说:“你说,朕不治你的罪。”
慎今这才重重磕了头,泪眼婆娑道:“那没命没臊的登徒子口中不干净,可喊得不是我家主子,奴婢依稀听他叫的是德妃娘娘的闺名!”
登时众人皆是惊诧,韫姜的脸陡然变得通红,尚未发作,徽予就先斥责:“那是什么下作的东西,德妃能与他有何干系!”
正是雷霆之怒,两个御前侍卫押解着那登徒子来了,皇后定睛看了,愕然道:“这不是给彦儿作画像的岑画师么……”皇后的声音渐渐低微下去,她觑着徽予的脸色,那真是黑紫转换,阴沉至极,于是不敢多言了。
岑画师别着脸,左半边脸又是擦伤又是混着泥土,原是之前吃了顾诚一脚,跌在地上所致。恪贵妃开口责问他:“你既然是如意馆的画师,为何在英华殿后竹苑里欲行不轨?”
岑画师低头不语,看似下定了决心闭口不语。
韫姜镇静,忍着羞臊:“慎今说他唤了本宫的闺名,想来是本宫与他有私,既然如此,我必悄悄儿去了,为什么带上你们家主子惹嫌?再说了,英华殿是佛祖圣地,本宫再愚笨,也断不会亵渎神明,惹佛降罪。”
慎今鬼祟的眼一转,颞颥道:“这事儿本该问德妃娘娘自个儿,奴婢是据实相告。德妃娘娘若觉得奴婢空口白牙地诬陷娘娘,大可问景妃主子。”
景妃还颤着倒在淑越怀中,木讷颔首,道:“定神想,确实耳闻了两声德妃的闺名。”
徽予拧眉,暂且不予理会。
不顾他与德妃怎样,轻薄了景妃是实在的,心里的气自不打一处来,他狠狠给御前侍卫使了眼色,侍卫便会意,照着他两肩就是两下痛击,岑画师吃痛,低呼两声,往前冲倒在地,头贴着福字麂皮罽子,黏糊糊的血粘着发丝,洇在罽子上。
他粗粗喘着气,咬牙道:“奴才是冲着景妃娘娘去的,左右同德妃娘娘绝无干系。”这可是欲盖弥彰了,在座的人都不蠢笨,一听即明了。
韫姜气得双手发抖,脸色不佳,恨恨忍着不言语,但被这样攀诬,败坏清誉,叫她这种清流世族出身的小姐无地自容,恨不得一头撞死得好。
徽予同样是气急败坏的,脸上狰狞的表情像呼啸的风雪,让人不寒而栗,不敢直视。
恪贵妃啐道:“你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话一出就被徽予狠狠挖了一眼,恪贵妃吓得不敢再则声。
当下人们-大气都不敢出,针掉落的声音也犹如雷霆万钧,霹雳当空。
不知过了多久,真真度日如年,难捱难熬,宛陵攥紧丝帕,只敢盯着翘头履上的木兰花纹。徽予终是出声:“押下去命慎刑司拷问调查,让他嘴放干净。”他像是冷静下来的语气,没有震怒的迹象留存,韫姜最怕他这般,一时也不知所措起来。
皇后见他起身要走,忙说:“景妃受了极大的惊吓,皇上要不要……”徽予无情地乜了景妃一瞬,流露出了一瞬的不悦,只说:“会有太医。”
韫姜一同起身送他,但因气极了浑身无力,脚下不稳,竟滑下了脚踏,徽予一闪身过去扶住她,韫姜倒在他的怀里,却更加惊恐,她怕徽予一样生了厌恶之心,那会让她更加痛苦。
徽予却用力搂住她,说:“别怕,我信你。”
韫姜听到的刹那间簌簌泪下,她掩面死死忍住,这就足够了,于她而言,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