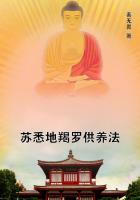出了咸福宫宫门,江鹤迎上来说:“启禀皇上,刚才静王府差人送了一对长白山野山参来,听说补身子最佳,可归脾、肺、心、肾经,大补元气,安神益智的。”
徽予不假思索:“那姜儿用了最好,快送了去未央宫。”说着不自觉就迈步去未央宫,“可带着吗?若没有就取了。”
江鹤跟上,笑嘻嘻说:“奴才私心想着可不是德妃娘娘用了最好吗?皇上心疼娘娘得紧,一定要送去未央宫的,所以刚听了消息,就忙教人取了来备着。”
徽予解颐,拿过他手中的拂尘敲了他的脑袋,笑道:“鬼灵精,谁准许你揣测朕的意思?”话里却没一丝要追究怪罪的意思。
江鹤不躲,伸手摸了摸脑袋,满面堆笑:“皇上教训的是。只是皇上对德妃娘娘的情谊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奴才心里门清呢。”
徽予笑着将佛尘掷向江鹤,负手身后,心情大好,踱步就往未央宫去。
君悦追上,道:“皇上,未央宫离得咸福宫远,不妨传了轿辇来得好。”他见徽予兴致勃勃没有要乘轿辇的意思,又怕徽予因此染了风寒,要遭慈宁宫太后训斥,于是劝,“皇上且看一路上大氅沾了寒气,一则有损龙体,二则近了德妃娘娘身,怕要不好呢。”
“这倒是。”徽予四下望了一圈,瞧不远不近处有歇脚处,于是说,“快传了,别耽搁。再打发人去未央宫传一声,只是一件,别叫她等急了,缓缓说,叫德妃切莫候在门口。若受了风,朕可再不去她未央宫里了。”
君悦听了不觉低头嗤笑一声,又怕惹恼了他,憋着笑说:“奴才谨记。”说罢了,一溜烟跑了。
江鹤则于一边伺候着徽予去歇脚的避风亭屋里坐了。
此屋乃先帝时所修,日常只有逛园子的嫔妃累了来稍坐片刻,一应物件备得并不齐全,椅子上的椅褡被靠只有三四成新的样子,却没积灰,可还能一用。
徽予随意拣了一个靠着窗棱子的地方坐了,本欲赏窗外纯明的雪景,却遥遥见了隐在一丛丛树桠子后陈旧寂寞的雨花阁。
那飞檐上的铃铛声在空寂中模糊不清地传来,比阒静无声更有惨意,仿佛一派热闹中萧索的孤者,反衬之下,愈发孤寂。
徽予眼中晦暗不明,江鹤知他在看雨花阁,却不敢则声。
徽予看了良久,回过头来,说:“韫姜跟朕说起过雨花阁那位的事罢。”
江鹤应声回答:“德妃娘娘心善,有日天极冷的时候,请过皇上的意,说想给雨花阁小主递些物什,皇上允了的。”
“哦……”徽予颔首,“韫姜是说过,朕记得当时天气极寒,她便说起雨花阁那位,那时朕与她聊得畅快,她又求告得殷切,朕就准了。”他拍了拍沾了雪的衣袍边角,掸掉了雪渍,露出银丝绣的灵鹤。
徽予佯装无意说:“别叫韫姜多操劳这些,你悄悄打发人日常送些去就成了。”
江鹤眼睛打了个转,心里门清,连声答应了,说:“奴才记下了。”揣着手,犹豫着怯怯说,“当日那事其实蹊跷,只是事涉昭章皇太后与德妃娘娘,雨花阁小主性子又烈,才……”说着闭了嘴,不敢说下去了。不见徽予愠怒,他这才松了口气。
徽予记得清欢的好,冷静下来回想当日,确实有冲动之处,只不知依清欢的性子,是否还肯示好。
胡乱想着,早有君悦过来等徽予上轿,徽予于是起身上了轿子一路逶迤平坦去了未央宫。
这般韫姜得了通传,知道徽予心疼自己心疼得紧,于是乖乖候在正殿明堂等徽予来。稍候片刻,又忍不住想出门去,陪着的御前小奴才霄华急忙要拦住:“娘娘使不得,若要这样,奴才可要遭了皇上和师傅骂了。”
韫姜朝着他恬静微笑:“不为难你就是了,瞧着你很年轻也眼生,是不是新到皇上跟前伺候的?”
“回德妃娘娘话,奴才是太后送到太平宫的,现在跟着江公公学着伺候皇上,一同的还有小城子,我们才到太平宫不过月余的。所以娘娘看着奴才眼生,不大认得。”霄华低头拱手回答。
韫姜听了,点头说:“应当的,皇上爱静,从前太平宫人少,现在事多,少不得要多些人手伺候。老些的奴才公公虽然稳重,却不敏捷机巧,不比你们这些年轻的灵清,记得牢办事快。只是你们还不稳重,诸事都要注意些。江鹤年纪不算大,办事却极其好的,你多多学着,以后或跟着皇上,或派送到哪宫里,总有你的好前程。”
霄华见韫姜温柔可亲,话也是贴心的,心中暖暖的,笑着答应下。
说话耗时辰,才说了几句,就有连声的击掌声,可知是徽予的仪仗来了。
韫姜登时眉开眼笑,转出去等候徽予,只见徽予快步了进来,飞扬的墨蓝色衣袍飞溅起些许雪水,韫姜忙伸手迎接,说:“予郎小心。”
徽予一把将她拢入怀中,韫姜见人都在,羞得急忙挣开了,徽予于是含着笑,扬手打发人都下去,搂着她进了熏暖的内阁。
入内是扑面的梅香,韫姜说:“掷了许多落梅花瓣进熏炉里,清香不闷人。予郎闻着觉着如何?”
徽予扶着她坐下,笑容冁然:“若是春和之际,有满园的梅色香气,就该是这种模样。”
韫姜温静噙笑,问他:“予郎托人说有好物什送来,是甚么稀罕物?”
“是对长白山野山参,适才路上打开瞧了一眼,是极好的品样。老七送来的,朕想着岂不是你送了最好?于是片刻不留就要送给你用。”徽予一招手,江鹤立刻会意,捧了盒子上来打开了给韫姜过目。
“哦……”韫姜听到徽延的名号,眉心一跳,声音低幽了下来,心不知为何惶惶的颤着,极不自在地将鬓边的一支点翠红玉簪取下来,捅开了盛有绿萼梅花的萱草漆画小箧子,开了后取了两三朵掷入不远处的小炭火盆里,才又缓缓说,“合该谢一谢静王殿下的,不过也不大方便,哪日韫姒能入宫来,臣妾带一句谢就是了,只怕静王爷怒臣妾不懂礼数呢。”
“何须这样?哪里徽延入了太平宫议事,朕提一句就是了。何况徽延人如其号,是个静的人,不计较这些。”他也随性抛了两朵进去,看着花瓣儿在银骨炭的熏燃下渐渐没了影子
他忽然想起从前那讳莫如深的密事来,竟有些惧怕的意味在心里打转,他的心发紧一般抽了一下。
徽予收敛了笑意,想了想,说,“唔……不过或许有些大补了,怕一个猛劲受不住的,不如存着,等开春养得大好了再开了用罢。朕教人送高句丽贡奉来的红参给你,稍微温些。”
“红参么?华太医才说要求上好红参来配一味药,今儿可就送来了。”韫姜也顺着抛开那烦恼,说起另一事来。
“如此甚好,时常听你提华惠允配出新药来,而且效果奇佳,可见他真真是心思新颖、医术高明。就连太后那头也夸赞,说有他一旁协助开方子,太后的病也大有起色,好了甚多。”他往后倚靠一把,拍着手边一个莲纹圆枕,说:“可见新起之秀,后来居上。”
“还是那句话,太医院的老太医们除了那几个德高望重的,剩下的不过是倚老卖老,医不好人也医不坏,甚至还有些迂阔,实在没大用处。听说予郎已经命了六部的人安排新的一批太医入了宫内,不知可安排得怎样了?太医院不属于内宫,臣妾现下也不管事,所以也不大知道怎么样了。”
韫姜凑近他,抚着他袖口的玄狐毛,那玄狐裘软而水滑,抚着舒服得很,她不禁就磋磨起来,徽予被她这小孩子气的动作逗得发笑,取下脖颈中围着的玄狐毛围脖递给韫姜耍完,一面回她:“安排他们跟着几个老的学学规矩,渐渐地分派到各个宫里跟着请脉记档了。”
韫姜听了点点头,眼角渗出的目光沉静却蕴含深意。
她正想着杂碎的一些事,徽予却迟疑着开口:“雨花阁……”又觉有些尬意,放不下脸面,说到关键处又不说了。
韫姜与他朝夕相处,心意相通,早已清楚,于是说:“臣妾自予郎准允后,亲去送过一次东西,留下了与清欢妹妹促膝长谈,从言语中,还是看得出她对予郎的情分的。女儿情长,尤其清欢她是真性情的女儿,虽是刚烈,但也情深,仍旧是对予郎念念不忘的。只是臣妾顾及予郎,恐予郎心有芥蒂,触怒了反而不好,所以迟迟没有提过。臣妾想着,再不久元旦新年,万象更新,要不要请了皇太后的意,接了清欢妹妹回来罢。予郎若觉得有些生疏了,臣妾请命从中斡旋可好吗?”
韫姜觑他脸色,瞅得出他有动摇之意,于是殷殷说:“予郎若怕与太后说,太后忌讳,不如臣妾去缓缓提一次,太后疼臣妾,臣妾又是年轻的女儿家又是带着病,太后或许更疼爱些,不会责怪臣妾年轻嘴上说错了话。”
“姜儿……”徽予长叹一气,情到深处不知如何抒发,喃喃唤一声,道,“不如罢了,谁也没有你好,朕不想你受委屈。那件事关乎朕的母后,也是件大忌讳的事,说了,太后再疼你,也不免要训斥你两句。朕知道你其实心思细,再不痛不痒你也会有些难过,朕不想那样。清欢很好,吟风弄月,谈诗论词,与她最妙,却也不是非她不可。她爱慕朕,朕就差人把她安顿好,雨花阁陈旧,但尚有好的屋子,阁内挪动,不惊动了太后,也不会怎样。”
韫姜又感动又愧疚,说起来是答应了清欢的,何况当初又是自己去周旋说得情,哪有这样放了的道理,岂不是食言无情?
她只好说:“可清欢妹妹一片赤心,实在不能辜负。臣妾有予郎这样的情分在,受些委屈又怎样?而且臣妾也心疼予郎身边没有个极致风雅的,实在可惜可叹。”
徽予深深凝睇着她,恨不能糅她入眼入心入命,他紧紧握住韫姜的手,久久不语,最后说:“也好,你执意如此,或许有你的主意。只一样,受了委屈不许偷偷掉眼泪,出了慈宁宫就来太平宫。”
“这岂不是要嚼太后的舌根?”韫姜掩嘴“嗤”地笑,媚眼闪闪,情谊郎朗。
徽予也跟着笑:“夫妻小两口说些密语而已,悄悄儿的,不是嚼舌根说坏话。”说着两相吃吃地笑,浓情蜜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