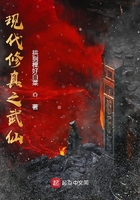那胖道士狞笑着抬手,肆内的空气便似横流涌动,在老朽的梁柱上刮出飞溅的木屑,周围的碗碟儿噼里啪啦的摔在地上。
修士踏入御气境后,气海与天地相通,灵力亦可幻化出万千妙用。江逸趔趄一下,连忙身体弓低,脚趾抓地,抓起身边一只桌腿,尽力甩向道士,灵力悄悄向右拳汇聚。
只听“嘭”的一声,桌子在空中化作无数木屑,飘散在肆内。
江逸的身子也失去平衡,但此时,灵力已蓄在拳中,他索性用力一蹬,向胖道士掠去,心中喝到:“破邪还真。”
这“破邪还真”乃是拳法中的后招,需提前蓄力才能挥出,此次对手修为奇高,只能打个出其不意,才有一丝胜算。
“啪——”
江逸忽感手腕传来一阵剧痛,这一拳竟被胖道士捏在手中。
“你那悲......”胖道士一边喝骂,一边揪住江逸脖颈,把他提起。再看向接拳的那手,掌心已通红。
江逸被抓住命脉,一丝力气也使不出来,急从袖中翻出一张道符,贴在道士手腕上,口中喝到:“五雷符,爆。”
“五......雷符。”胖道士目次欲裂,忽见那符爆出烟火,忙伸手去摘掉,一阵闪光照亮肆内,刺得他眼睛微疼,待看清时,江逸已然挣脱了。
他赶忙看向手腕,只见袖袍被烧得只剩下几缕布条,皮肤被烟熏黑,却并未受伤。
“师弟,你给他骗了,这哪是甚么五雷符,连黄符也算不上......”
店内烟雾缭散,他掀舞了几下袖袍,只见瘦道士冷笑着站在门口,一手抓着正要跑出肆外的江逸。
“真是好手段啊,师兄你莫动手,让我来剐了他。”胖道士满脸阴沉。
江逸脑子转的飞快,却无任何办法,又听他狞笑道:“本来只想扇你几个耳刮子,谁叫你本事那么大,连我的袖袍都给烧了......嘿嘿,师兄,我是不是得扯断他一只手,才说得过去。”
正说着,胖道士已经接近,一手如鹰爪般固住江逸的脖子,一手扣在手肘处,好似准备要撕开。
瘦道士一双鼠眼眯起:“你只要留他一条小命,怎么做都不算过分。”
江逸感到关节渐渐着力,胖道士那张布满横肉的脸近在眼前,呼出的粗气触在自己领上,心里蔓延上一丝恐惧。
忽见一柄飞剑自窗户掠进,只一瞬便抢至江逸与道士之间,剑芒宛如风车一般绞动,似要把那一双胖手绞成肉泥。
“啊。”胖道士大惊失色,松开江逸后退两步。
江逸忽被一股巨力拎起后领,退至肆门前。
“祝兄、候兄,还望得饶人处且饶人。”
江逸缓过气来,回头望去,只见墨崖竟站在身后,素白的脸布满凝重,那柄剑早已收入鞘中。
他松开江逸,用剑鞘将他别向身后,顺带抱了一拳。
瘦道士冷笑道:“我们二位兄弟来到贵地,一向对御灵胄礼敬有佳,墨老弟此举,倒是不把雁荡山放在眼里了。”
墨崖道:“候兄配合我们的工作,墨崖自是感激万分,只是候兄有所不知,这人是家师新收的弟子,与御灵胄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以晚辈着急出手,还望两位道兄莫怪。”
瘦道士皱眉道:“他是绿竹居士的弟子?你可莫要唬我。”
墨崖道:“此事在江宁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候兄尽管去打听。”
胖道士抢骂道:“管他是谁的弟子,你那悲......老子这只手怎么算。”
墨崖冷笑道:“嘿,御灵胄于四海九州皆设有分部,你若是想算,随便找一家,最好把贵派掌门带上,咱们细细理论......”
江逸靠在他身后,只觉得那道肩膀说不出的安心,渐渐把惊骇吞回肚中,听到二人的谈话,寻思道:
“这瘦道士忒不要脸,在镇上打砸抢掠,还敢说甚么礼敬有佳。不过墨兄为何叫他们把掌门带上?啊,是了,这是在劝他们掂量一番,掌门会不会应允他们和御灵胄叫板。”
此话一出,那两人果然迟疑一阵。
胖道士又说道:“你莫要混淆视听,我只要与他算账,可不是和御灵胄算账,墨崖,你再护着他,可是要与雁荡山交恶吗?”
墨崖咬牙道:“久闻雁荡山人才辈出,晚辈怎敢造次,只是这人......”
江逸忽然站出:“这事自我而起,与墨兄无关,你不就是想要我这手臂吗,我给你便是。”
方才他手臂将要被扯断,心中又骇又悔,此时却觉得少一只手臂也没什么,只是不能让墨崖为难了。
“逸师弟,你......”墨崖忙拦住江逸肩膀。
“哈哈,说得好,你快过来让我撕了。”胖道士狞笑着,踏步走过来。
瘦道士忽然喝到:“祝师弟,退下!”
“可是他......”
“我叫你退下!”他嗓音大了几分。
胖道士脸色憋得酱紫,不甘心的后退两步。
瘦道士向墨崖问道:“这人真是绿竹居士的弟子?”
墨崖松了口气:“千真万确,晚辈不敢欺骗候兄。”
“既是这样......”瘦道士沉吟道:“我们虽吃了天大的亏,却素仰绿竹居士大名,不敢再计较......”
墨崖喜道:“多谢了候兄成全,晚辈定会把这番话禀告家师,择日带着逸师弟,亲自上雁荡山赔罪。”说罢,又做了一揖。
那瘦道士微微摆了摆手,胖道士立在后面,仍做愤愤之色,却不敢多言。
墨崖遂领着江逸退出酒肆,帘后仍传来骂声......
——————
两人掠到灵市东边一座小衙,这儿门前连御灵胄的牌儿也没挂,只有一个小院,七、八间房子。
墨崖领他进了一处大厅坐下,笑道:“易师弟,你喝酒吗?”
江逸忙道:“我喝些白水就好......”
又拱手抱拳:“今日多谢......墨兄出手相助了。”他本想叫墨师兄,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墨崖笑了笑,给他倒了一杯茶,自己却拿出酒壶:“你的事情,易师妹已和我说过了。咱们师父有旧交,你若是不嫌弃,咱们以师门相称亦可。”
江逸只觉一股暖流淌过心间,正襟站起,恭恭敬敬的鞠了一躬:“师兄!”
墨崖亦站起,笑着受了这一礼,两人一齐坐下。
墨崖笑道:“你不在江宁待着,跑来这旮旯作甚,莫不是知道师兄在这受苦,特地来探望我的。”
江逸真诚相告:“我这次是与师父一起来的,因我修炼的法门有些奇异,准备去蛮域求些妖兽精血。”
“甚么法门如此邪门,竟要妖兽精血......”墨崖刚说到一半,蓦然醒悟:“莫非是正气涅槃经?”
江逸苦笑道:“师兄真是见多识广,正是那部经书。”
墨崖沉吟道:“我也只听闻它的名声,师弟,这经书可不好练啊,听说江修诀也练了它一年,待凝练气海后,便也弃了。”
江逸沉吟道:“他也练过这经书么?怪不得前两日见面时,说对此有些研究,原来不是托大。”
墨崖摇晃酒壶:“此人极其自负,但功夫却不赖,我倒想与他讨教几招,只是一直没有机会......”
江逸忽然想起:“对了师兄,你说在这儿受苦,却是何意?”
“唉——”墨崖慢慢押了口酒,愁着脸说:“逸师弟你有所不知,家师的那一片竹林里,养了一只灵猴,说起来也养有七八年了,可它野性难驯,经常偷跑出来,每次都要我来寻它。”
江逸哑然:“还有这等奇事?那为何不直接关在笼子里?”
墨崖叹道:“我早想如此了,可师父不让,说甚么‘此猴是我的叔叔,哪有把叔叔关起来的道理。’哦,师弟,这是我师父的胡话,你可不用当真。”
江逸失笑:“居士是真高人,说的话也不是我等参得透的。”
墨崖道:“谁说不是呢。”
天色逐渐昏暗,两只寒鸦飞来老枝上,嘎嘎的叫着。
“难得喝口酒,尽来聒噪!”墨崖听得烦躁,虚手一指,它们便再也叫不出来了,扑哧了几下便向东飞去。
江逸笑着摇了摇头,问道:“对了师兄,酒肆里那两位修士是从何而来啊,我见他们倒是霸道得紧。”
墨崖哼了一声:“他们是雁荡山的道士。说起来,这几年雁荡山不断派人驻扎在蛮域边,要说意欲何为,却是他门中的机密了。”
江逸呷了口茶,见墨崖那壶酒已喝过一半,又笑道:“这片山脉广袤无边,师兄你要在其中找只猴子,可有得受了。”
墨崖神秘一笑:“嘿嘿,你不知,山人自有妙计。”
江逸奇道:“哦,你待怎么找?”
墨崖思索了会儿:“我与你说了,却不许去告我的状。”
江逸摇头道:“自然不敢。”
墨崖又道:“连易师妹也说不得,她是师父的小跟班,说于她听,便等于说于师父听,那我便惨了。”
江逸忍住笑:“我谁也不说,只烂在肚里好了。”
“好兄弟......”墨崖道:“哼,师父不让我把那猴子关起来,我也不能任由它将我满山戏耍。前两月我趁它睡着,偷偷在它体内埋下一道禁忌,嘿嘿,不仅对它行踪了如指掌,而且只需在它面前叫一声:‘还不快向墨师兄磕头’。它便再也动不了,任由你把它逮回来。”
江逸捧腹大笑:“师兄,你这禁忌也忒好笑,是谁教你的?”
墨崖微笑道:“这是我去贵州办案时,当地的土人教我的法子,唤作甚么蛊术,咒语却是我自己想的,你休要觉得好笑,当时我也斟酌了许久。”
江逸问道:“你斟酌什么?”
墨崖把酒壶仰头喝尽,笑道:“你想,在师门里,只有我向师父磕头,从来不会有人向我墨崖磕头,那这句咒语,便是谁也触不到了。”
“妙极......”江逸说着,忍不住捧腹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