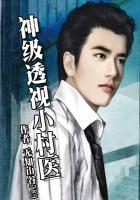早上起来,打开电脑,写译者序,一肚子话,择不清,拥挤着,向上涌,想起荣格的话,每一个有创造力的人本身都是一个分裂的存在,面对毛姆这个既严肃又活泼,既刻薄又宽容,既害羞又勇敢,既自卑又狂傲,既睿智又偏执,在读者那里成功,在智识功利者那里不成功的作家,四分之三正常,四分之一同性恋,或者四分之三同性恋,四分之一正常,终生用异性恋视角写作的“分裂分子”,我一时不知如何排列拼接词语也情有可原。
通常,一个“分裂分子”,倘若恰好有自省的习惯和自赎的意愿,那么周遭的一切人或物,人与人的集合体——社会,物与物的集合体——世界,尤其是最不可或缺及舍弃的自身都是可用来研究、思考和给予启发的名与实。毛姆八岁丧母,十岁丧父,出生于法国,成长于英国,个子矮小,口吃严重,还有点“地包天”,这些早期经验和身体属性不可能不对他的人格产生影响。毛姆说,“身体的偶有属性会影响灵魂的构成,假如我不口吃,假如我的个子能高出四五英寸,我的灵魂会很不一样。”然而,人生没有假设,前提不同,结果自然不同,但不同在哪里,是否以符合心意的形式不同,没有一个全知全能者能为我们一次性解答所有的困惑,而拥有一个全知全能的精神指引者,一本全知全能的书,正是我辈痴人终生的奢念,毛姆也不例外。看似早早就接受了唯物主义,放弃基督教信仰的毛姆,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个更好的替代品。在这本创作时间跨度超过半个世纪的《作家笔记》里,我们时常会看到毛姆关于基督教和上帝的言论,乍看,他背弃信仰的态度是决绝的,甚至和渎神沾边,但细看之下,并非如此,他给自己留了余地和退路,他和被谈论对象保持着一定的体面的距离,原来,他是一个看似轻率的审慎者。1894年,他这样写道,“信仰上帝无关常识、逻辑或推理,只关乎情感。证明上帝存在和证明他不存在都是不可能的。我不信上帝。有来世这个说法对我而言不可思议。我确信,等我死了,我的生命将完全停止,来于尘土,归于尘土。不过,我能想象,将来有一天,我或许会信上帝,但仍会和现在我不信上帝时一样,认为信仰上帝无关推理或观察,只关乎情感。”五十年后的1944年,他又写道,“我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任何用来证明他存在的论点都不具说服力,就像伊壁鸠鲁很久以前说过的那样,信仰必须凭借直觉。我从未有过此类直觉,也从未有人就邪恶与全能至善的上帝如何相容给出令我满意的解释。”断章取义地看,他不信上帝。前后联系着看,他仍有信上帝的可能。他的“不信”只能理解为彼时彼地的困惑不解。毛姆五十多岁时,人家批评他犬儒,他还真不是狄奥根尼那种“我希望你闪到旁边,让我可以晒到太阳”的犬儒法,他顾虑和在乎的东西太多了。他不相信有来生,但最令他难以接受的是,不期望来生意味着再也见不到母亲了,母亲的生,给了他这辈子唯一相互的爱;母亲的死,是他这辈子最化不开的痛。1922年的笔记中,他详细描述了他与他深情怀念的哈克斯顿在婆罗洲的实哥浪河上的一次溺水经历。此前,1917年的笔记中,他也谈到一次溺水经历,那次是在海上,“我感觉死亡迫在眉睫,恳求上帝的话脱口而出,这是被我遗忘的儿时信仰的残留物,抑制住它们,并冷静地面对可能要发生的事需要一定的意志力。那一刻,我差点儿就信了上帝,强烈的荒唐感使我得以免于向恐惧屈服。”毛姆还描述过一次奇异的显灵,显灵、神迹之类的故事,这种话通常由笃诚的信徒讲出,有一回,毛姆去威尼斯,照常去学院美术馆看画,感觉累了,他就坐在委罗内塞那幅《利未家的宴会》前。画中的耶稣坐在一张长桌的中央主持宴会,侧着头和他左边的施洗约翰交谈。毛姆凝视着这幅画,突然,他看见耶稣扭过头来盯着他的脸,他后来解释说,这大概是视错觉,但这件事仍使他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触动。翻回头看,毛姆说“信仰上帝只关乎情感”,是吗?显然不是,如果只关乎情感,这些关键时刻足以让他重新拥抱儿时的信仰,而他没有,依我看,总体上,他的理性占了感性的上风。
如果可以把毛姆称作哲理小说家,那么毛姆对哲学的探索并不止于宗教这一点,对宗教的探索也不止于基督教这一点。中年的毛姆说,“尽管我是具象思维,面对抽象概念,思维并不活跃,我却酷爱玄学,看哲学家们像走钢丝一样研究难懂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一大乐事。”晚年的毛姆依然乐此不疲,“我很高兴自己活得够久,仍有一个学科让我一如既往地兴奋,那就是哲学,不是爱争论且枯燥的哲学——‘哲学家们的论证若无法有效治疗人类的苦难,这样的论证是没有价值的。’——而是探讨我们所有人都会面对的问题的哲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提诺、斯宾诺莎,还有很多现代哲学家,如布拉德利,他们一直都能给我带来快乐,引我深思。毕竟,他们和古希腊悲剧作家只谈论对人类重要的问题。他们给人喜悦,让人平静。”毛姆是个好奇的人,无论是在英国、法国、美国、西班牙,还是南太平洋诸岛和印度,他总是在寻找并渴望找到一种生活模式,毛姆是一个智慧的追问者,一个思想的记录者,困扰我们的问题也同样困扰着他,生命的价值是什么,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到底该怎样活着,宇宙的意义在哪里。不相信这个,那又该相信什么。唯物主义、自然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唯美主义、神秘主义、现实主义、功利主义,这些主义的痕迹,毛姆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有。善于以讽刺揭开虚伪面具的毛姆,善于一针见血、指点迷津的毛姆,身为二十世纪最畅销作家,身边不是美人就是名流的毛姆,是否找到了他渴求一生的圣杯呢——灵魂的慰藉与解脱,那个大写的PEACE(安宁)?《毛姆传——毛姆的秘密生活》的作者赛琳娜·黑斯廷斯这样写道:“晚年的毛姆会陷入几乎无法自拔的痛苦之中。他时常从噩梦中惊醒,艾伦(毛姆的最后一任秘书和情人)现在睡在毛姆的卧室里,以便在他醒来时安慰他,有时,他起夜多达六次;白天,万念俱灰的他会愣愣地坐上几个小时,控制不住地哭泣,拒绝得到安慰。”
赵文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