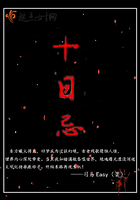第二天清晨,宿醉后的月演带着侍女佩玖,晕沉沉地回到二层西厢办公室。
一边揉着太阳穴一边看着中使司递交的上月收支四柱清册和园内报告,月演叹了口气,抬起头来看了看面前的四个幕僚,端起茶杯来啜了一口。
“都说说吧,各位。”双手捧着茶杯,月演淡淡地说道,“老符,你是司正,你先说。”
“殿下,这公主府确实比我们想的要费钱。”担任司正的符义趋双手背在身后说道,“单说这郁州府为秉成宫购置的发电设备就要十一万两,这些按照朝制都要算作州府垫支,将来收了粮钱之后还要交还。”
“更不要说清理周边民人的工作。”司副之一的徐元乡插嘴说,“按照禀山县的汇报是安置费二十又三万两,王用仪说三万两作为县里孝敬就免了,所以今年收上的税款还要扣下二十万。”
“切,这么说我们还应该谢谢他老人家了?”说着,另一个司副吕千原抱着胳膊冷笑着。
捧着茶杯看了看他们三个,月演耷拉着眼睛叹了口气,转而伸着脖子看了看坐在一旁沙发上睡眼惺忪的胡芝榭。
“芝榭,你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听了这话,胡芝榭慢慢悠悠地转过头去,看了看一连无奈的月演,麻木地摇了摇头。
“回殿下……没了……”
“我大清早儿的把大家找过来,不是要听你们说这些的。”月演放下茶杯站起身来,“眼下我有一件超级严肃的事儿要问你们。”
听了这话,四个人面面相觑了一番,谁都不敢说什么。清晨的凉风吹拂着窗帘,茶杯中的烟气渐渐淡了下来。
“谁能告诉我:姐姐的鞋,是你们谁负责买的?”
双手撑着桌子,月演冷冷地看着四个人呆若木鸡的样子,很严肃地说道:“老符,你来说,我们姐儿俩的日需品哪位司副负责?”
“啊……吕千原目前负责府内采买和警备的工作,所以……”听了这话,符义趋转头看着吕千原说道。
“等等,我采买的都是日常小厮奴婢的用度,要说两位主子的需要,还是元乡的监管的内务。”
“不对不对,我的内务又不是做这个的。”听了吕千原的话,徐元乡慌张地摇着头,“按照以前在京城时候的惯例,这类需求都是荷姑娘打发当差去买,回来再找我报账……”
“京城是京城,郁州是郁州。”说着,吕千原整了整领子道,“这穷乡僻壤的,可不是像上京一样方便,随便打发个奴婢去趟店市口儿就得了。凡是购置主子的物什,都要内务专人去正峦县一并卖。徐兄,没把安姑娘当正经主子吧?一双鞋也左省右省的,这成何体统?”
“你放屁!”说着,徐元乡一拍桌子,“姓吕的,你别在这里煽风点火的!就一双鞋的事儿你也要深文周纳一番!我就奇怪了,你一天不针对我就浑身不自在是不是?”
“不是我针对你,是身为老同僚不得不提醒你几句。”吕千原抱着胳膊冷笑着,“我知道你监管内务事事繁杂,但不能因为省钱害得殿下烦心。你瞅瞅,现在人家安姑娘疼的连路都走不了,这么大的罪过,总要有人来担着不是?”
“怎么的,看来吕老弟大早上的还放的是连珠屁,一放就停不下来了。你要教训我,我倒要教训教训你,那天咱们说去正峦购置……”
“都、闭、嘴!”连拍了三下桌子,月演狠狠地说道,“怎么的?吵起来没完了是不是?现在哪个能告诉我,姐姐的鞋,是谁买的?”
清风拂过,杯子里的茶已经渐渐凉透,在窗外若有若无的鸟雀声中,办公室里一片沉默。
“诶呦喂~怎么都不说话了?”攥着双拳咬着牙,月演带着古怪的笑容骂道,“花钱养着你们这帮人,又不是雇你们叫唤的。要真那样儿的话我还不如买挂炮仗,人家炮仗响起来不比你们叫的好听?”
“殿下……”沉默中,坐在沙发上的胡芝榭抱着熊形枕头,慢慢地站起身来。
“怎么了?”月演咬着牙问道。
“荷姑娘……去哪儿了?”
“荷姑娘?啊,我派小荷去请姐姐亲爹的遗骨去了,这你们就甭管了,估计明儿个就回。”
“好……”抱着枕头,胡芝榭慢慢地坐了下来。
“总而言之,日后的工作还有很多,我可没工夫一一解决这些个破事。老符,你这几天先把这些事打理清楚了,别到时候到了年底收税的时候,乱七八糟的再让姓王的给骗了。”
“是。”符义趋点头答道。
“还有,月安姑娘在我家也是个名有姓的千金小姐,给她预备的东西,只许比我好,不许比我差。伺候我有不周之处,顶多罚个把月的例银,要是把她老人家得罪了,你们到时候别怪我不讲情面。”
说着,月演叹了口气,一边转身离开办公室,一边嘴里嘟囔着:“这帮活宝,早晚有一天我得死在你们手里。”
待月演出了办公室的门,徐元乡挠了挠脑袋转身坐在了胡芝榭的身旁,对着吕千原说道:“你说你,说出的话总往人肺管子上戳。现在可倒好,开心了吧?非要让殿下抛出句狠话才罢手。”
“还说我呢,你瞧瞧你,左一句放屁又一句放屁,你还会说点儿什么?”听了这话,吕千原还嘴道:“要不是把差事办砸了,怎么会招得殿下动怒?”
“放屁!要不是你提什么‘安姑娘不是正经主子’这种话……”
“好啦、好啦。”挥了挥手后,符义趋皱着眉头说道,“你们俩都先消停消停,鞋的事情都已经这样了,还是赶快想着弥补吧,下午的时候咱们还要合计分工的事呢。”
“要我说,这殿下也是奇怪。”坐在徐元乡对面的沙发上,吕千原叹了口气说,“放着堂堂刑部尚书、右都御史不去当,非要请旨跑到这穷乡僻壤来就藩。这也就算了,来了郁宫园后,从早到晚把一个远房亲戚当活菩萨似的供着,饮食起居处处留意,也不说明白是哪路的亲戚。”
“怕是殿下觉得,咱们怠慢安姑娘,实际上是怠慢她老人家……”
“不是。”听了徐元乡的话,吕千原摇了摇头。
站起身来后,吕千原走出办公室朝走廊左右看了看,便关上了大门。随即小跑着走回众人旁低声说道:“你们可别说出去了,我听说昨天晚上,殿下亲自用自己的脸盆给安姑娘洗脚来的。”
“真有这样的事?”徐元乡瞪大了眼睛,一副瞠目结舌的样子。
“可不是么!你徐兄也是从平州开始就跟着殿下的老人了。平心而论,又几个人能让殿下这样相待的?除了宣祖皇帝、当今皇太后,怕是找不出其他人了。就连当今圣上,也没有过这样的待遇啊。”
“你们说……”听了这话,胡芝榭慢慢地张开嘴,缓缓地说道。
“什么?”一听胡芝榭有话说,大家都闭住了嘴,严肃地看着他。
“你们说……荷姑娘,去哪儿了……”抱着熊枕头,胡芝榭呆呆地问道。
“芝榭兄,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吕千原拍了拍大腿,“我看这安姑娘绝对不简单,很可能是什么方士,或是身怀绝技的贴身护卫,专门替殿下办什么不便和外人说的事。”
一听这话,徐元乡摇了摇手说:“不会不会,殿下从来不信那些方士之流,要说贴身护卫,有小荷一个人就够了。你听说过没有,她屋里藏了好多令牌法器,里面好多东西都是被朝廷明令禁止的玩意儿。”
“我说,你们到底说够了没有。”站在沙发一侧,符义趋说道,“有时间胡诌乱猜,还不如去置办些合适的鞋袜、绣袍,省得下次再招惹殿下责骂。”
“是……”听了这话,三个人都没精打采的站起身来,晃晃悠悠地回中使司办公去了。跟在所有人的身后,符义趋转过身去,看着摆在桌子上的文件和茶杯,心中叹了口气,摇着头关上了办公室的大门。
自办公室来到了东阁五宗堂,月演照例焚香参拜了圣旨,随后径直下了楼来到一层的储藏室,带着管事依次翻看了账目后,安排将诸宫印及前殷皇帝遗墨宸翰一一造册了登记。忙完之后,便又带着侍女佩玖到且济池西边的琼瑰苑,一边督促工匠修整花圃一边用了上午茶。
“佩玖,怎么今天一上午都没见着姐姐来的。”坐在花园中的高台圆基八方亭里,月演一边从兜里掏出了烟一边问道。
“回千岁,听说用了早膳之后,安姑娘就带着琼英去园子外头了。”
“园子外头?启明园还是长庚园?”
“不是承恩园外,是郁宫外。”
“哦……”点了支烟猛吸了一口,月演点了点头,发了会儿愣,她猛地将头转了过去,两眼直直地瞪着佩玖:“什么?出园去了?”
“是,是去外头县城里了。”
“什……什么?你们怎么让她出去了?”
“之前千岁交代说:‘姐姐想干什么就要她去做,所有人不得阻拦’。”看着月演满脸惊异的神色,佩玖有些迟疑地说道。
“带了多少人?”说着,月演将烟头丢在地上,飞奔着跑出了亭子。
“贴身的三个姑娘,我还派了二十个护卫跟着。”
“知道了,给我把马牵过来,再调五十人分头去找。这个时候到处都是流民草寇,万一被劫去做了压寨夫人就麻烦了。”
带着吕千原等五十人护卫,月演骑着马穿过长天街,自暑门下走马道进了县城后,一行人便沿着街道四下寻找起来。绕过空无一人的井子铺、良子坊,月演勒着马头四下看了看,只见青石板路左右,家家户户大门紧闭,深沉的乌云下,整个街道死一般沉静,唯有身后远远处吕千原朝护卫们发号施令的声音。
猛然间,一个孩子吆喝的声音从悠悠远远处传来,一听这声音,月演猛地想起了之前梦游前听闻的声音。极目远望,只见在青石板路的尽头,一个孩子穿着白凄凄的衣服站在路当中。因为距离太远,也分不出男女,只是孩子手里拿着朵不知名的血红花儿,在陈旧阴暗的良子坊小街上显得格外刺眼。
“去、去。”赶着马往前走去,月演按下怦怦跳的心脏紧紧盯着那孩子,只是不论走了多久,那远处的小白点依旧站在前面,不知不觉间,月演觉得自己已经走出了好远,回头看去,只见来路已经隐埋在了云雾之中,护卫们也都看不到了。见此,月演急忙勒住了马,手上不由得颤抖了起来。幽幽的,前面那孩子欢笑着,又唱诵道:
寄首琼花下,藏尸芭蕉台。清魂破茧去,化蝶伴如来。
似乎看出了月演心中的慌乱似的,唱毕,那孩子用诡异的声音“嘻嘻”地笑出了声来。
“那边的,给我过来!”说着,月演从兜里掏出了枪,直直地对着悠远处缥缈着的小白点。只见那孩子也不害怕,只是转过身去,飘飘悠悠地朝远方走去,转眼间便没了影。渐渐地,月演只感觉身边的薄雾渐渐淡了下去,身下也明亮了起来。
“殿下!”带着护卫,吕千原纵马追了过来,看到月演举枪的样子,便也从腰间抽出了配剑来,“怎么了,有什么情况?”
“千原,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孩子?”举着枪喘着粗气,月演极力克制着颤抖问道。
“孩子?看到了,刚刚好像顺着小道跑了。”
“追!”说着,月演拽着缰绳冲着护卫们喊道,“朝腿开枪!抓住活的给我押过来。”
“是!”高喊了一声,众护卫在吕千原的带领下朝着小路奔驰而去。
跟在吕千原的身边,月演率众护卫穿大街越小巷,眼瞅着一个孩子奔跑在前面,便举枪高喊:“前面的小崽子,姐姐这里有糖!”
那孩子听了,也不回话,只知道死命地往前跑去。见此,月演狠狠地“呸”了一口,朝着孩子的腿肚子开了一枪。只听得“哗啦”一声,街道边的瓷罐子碎了一地,那孩子依旧跑在前面,转而往大街上跑去了。
“这傻小子,今天他是死定了。”说着,月演纵马绕过小街,只见在大街的拐角处,一大帮孩子围坐在牌楼柱子下。见此,月演勒停了马,举枪朝天空放了一枪,随后带着众护卫包围住了石墩子旁的孩子们。
“都不许动,总算是让我逮住你这小鬼儿了。”说着,月演翻身下了马,举着枪朝孩子们走了过来。
“等等!千岁是我们!”只听得混乱的孩子堆当中一声呼喊,琼英从牌楼柱子后面钻了出来。
“琼英?你怎么在这儿?姐姐呢?”见此,月演放下了枪,皱着眉头疑惑道。
“演儿,你这是干什么?”抱着一个年纪很小的孩子,月安也走了出来。
“姐,你怎么躲在这里?让我好找半天。”说着,月演将枪别在腰间,小跑着走了过去。
“我从前经常来这里的悲田院给孩子们看病送吃的,昨天晚上听你说县里流民多,所以过来瞧瞧。”
“护卫们呢?”
“我让他们分头去找人家了,就剩下两个大兄弟站在那边。”月安抱着孩子说道,“话说,你刚才听没听见有枪响?”
“姐姐,你跟我过来。”拽着月安的袖子走到一边,月演小声说道,“我看这帮孩子不是什么正经路数,估计是着了什么魔,姐姐快走,看我把这帮小崽子赶尽杀绝,省得日后节外生枝。”
“演儿,你说什么呢?”扭过头去看了看身后的孩子,月安笑着说道,“都是很普通的孩子们啊。”
“月安姐姐,她就是追我的那个坏蛋!”说着,一个小男孩冲到月安身边,指着月演骂道。
“娘的,我看你是不想活了。”说着,月演抽出了配枪,在男孩的脚边开了一枪,一瞬间,砂石尘土扬起一片。听到枪响,一帮孩子愣了半晌,随即一个接一个地大哭了起来。
“月演,你这是干什么?”一边哄着怀里的孩子,月安一边生气地说。
“姐姐,你还记得记得上次我生病发烧么?就是这个小业障作的祟。”拿枪指着瘫倒在地上的小男孩,月演冷笑着说道,“出门儿之前,阎王爷没嘱咐你绕着丹月演走道儿么。”
“徐月演,你给我把枪放下!”将孩子塞到琼英怀里,月安转身堵在月演的枪口前说道。
冷冷地盯着月安的眼睛,月演“啧”了一下,老老实实地收了枪。
“二十三,别害怕,有姐姐呢。”见月演收了枪,月安转身走到男孩的身边,将他紧紧抱着安慰道。
绕过护卫们的包围圈,月演看了看赶来的其余护卫,挥了挥手叫他们免拜。
杂乱的脚步当中,听着姐姐温柔的安慰声音从身后传来,月演从兜里将烟拿出,让吕千原给自己点了火。在猛吸了一口后,月演憋着气站了一会儿,叹着气在沉沉的乌云下吐出了一个烟圈。
“回府吧。”